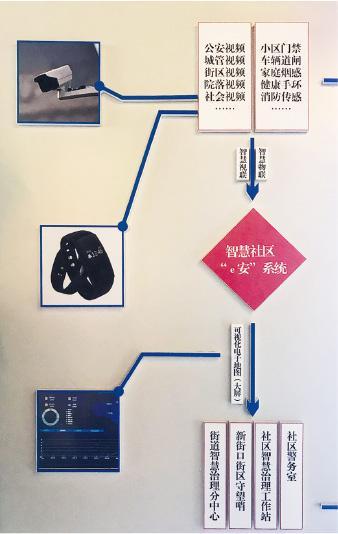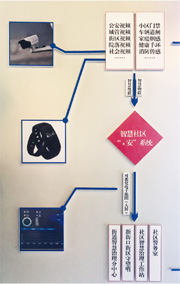【明報專訊】區議會變天後,觀塘區、灣仔區均開會通過叫停被稱為「小白象」的音樂噴泉、社區會堂計劃,但無阻工程繼續進行,香港究竟擁有怎樣的社區規劃政策方針?在去年成都舉行的社區規劃論壇上,參與其中的有中大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伍美琴教授。她回想獲邀時的反應,「他們讓我談香港的社區規劃制度,我說,吓?香港沒有社區規劃,也沒有制度㗎喎,但民間爭取了很多」。很久以前,她聽過在北京工作的學生說,做事還得看政治氣候,「有時可以做,有時不可以做」,現在全球發展多時的社區規劃,轉眼在內地愈趨廣泛,「當然背後深層次是有原因,社區和諧,管治更容易,變相是更高明的維穩方式」。
當台灣是先行者,日本有發展,內地都開始建立社區規劃的制度,香港政府一如其做事作風,慢很多拍。到底成都如何做社區規劃?伍教授先談她在成華區見到的兩個例子:
青龍記憶5811
「那裏原先是一塊爛地,居民以前會用來放狗,見面點點頭便算。」5811是指寶成鐵路通車之日(1958年1月1日),鐵路從陝西寶雞市到四川成都,及後成為中國首條電氣化鐵路,成都青街道社區住了很多鐵路局的老工人,因此佔地3850平方米的「青龍記憶5811」項目以鐵路作主題,裏面包括「鐵路文化微博物館」,收集居民的舊物及舊照展出。伍教授雖留意到草地做工不佳,「但我對整體設計的印象很深刻」,她提到花圃由不同住戶提供的花組成;規劃團隊在研究過程中發現該區沒有喝咖啡的地方,所以增設一角;又設小蛋糕店,售價比外面便宜,亦由居民經營,「有商業活動可自負盈虧」。地方營造有The Power of 10的說法,「如果一個地方有十個原因可以吸引人去,一定vibrant(充滿活力),所以為何旺角、銅鑼灣總是人來人往,就如青龍記憶,可以去坐、去玩、看花、食餅、飲咖啡、睇展覽、談天,就會多人去」。
毛邊書局‧桃蹊書院
桃蹊路街區住了12萬人,原有的社區活動中心既小又偏僻,假日亦不開放。社區規劃團隊對區內居民的文化需求作問卷調查,收回1.5萬份問卷,當中42%投了「讀書」一票,14%對書畫有興趣,於是負責這個項目的規劃團隊找來有21年歷史的古/舊書書店毛邊書局合作,經營一個社區空間,「政府只是給予空間,那裏不只賣書,除了書局之外,還作為社區一個落腳點,鼓勵一家大小入來」,當中有課室可舉辦書法等課程、展覽空間等。在設計階段,團隊5次徵集公眾意見,對方案修改過12次,4名社區規劃設計師之中有一名是當地居民。伍教授經常提及「社會健康(social well-being)」,「社會的健康是住在裏面的人發覺我不是沒用的,原來也可貢獻社會,可以實現自我」。
與香港比較,又是土地問題?曾公開批評「明日大嶼」的伍教授多番力勸政府做好規劃,她說:「土地完全不是問題,所有地都是政府的,要畀人用幾容易?願不願意給出地方只是一念之差,但(政府)想管治好的話,真心希望社區和諧,人生活得開心,唔該你,諗清楚,土地是讓人用的,不是只用來賺錢的。」昔日學生總結北京工作經驗時提到的政治氣候,對於內地的社區規劃有何影響?她坦言,「這方面我不太清楚,這也是為什麼我會如此驚訝(成都的發展),而且他們不是今天才開始做」。
被拒、爭取過程 一一記下
成華區官方出版一本《社區規劃案例集》,記錄十多個計劃如何構思實踐,並附專家意見,內容亦不乏規劃團隊對計劃的反思,例如「青龍記憶5811」的部分,會記下曾被成都市鐵路局拒絕為工程連接水電,多次向當局去信不果,最後由鐵路局的退休職員向局方領導層爭取才可解決問題;另外八里莊社區一個「共享客廳」經營半年,規劃組坦承「運營效果並沒有達到非常理想的狀態,只能進行一個比較低微的循環」;桃蹊書院在建立過程中,亦因規劃組兩名成員參與得不夠積極,經共同評議被開除。伍教授認為「不斷改進很重要,做了會檢討,下次再改善。香港是開了頭覺得ok,便從不檢討,年年照做」,「在21世紀城市發展中這是很需要的,所以出現很多urban lab的概念,要看成是實驗,才會好玩」。
還權予民 社區「自治」
在案例集裏可見政府欲將社區規劃建立成一個制度,每個計劃均列明「社區規劃師」及「眾創組人員」名單,眾創組是什麼?在另一本官方編寫的《成華區社區規劃實務指南》中,列出眾創組成員包括社區兩委成員(即黨支部委員會及居民委員會)、居民領袖、居民自組織、社區工作者、社區居民、社會組織、社會企業、志願者。伍教授提及曾與一名「被稱為成都政府文膽」的女士傾談,「她說要還權給居民」,「當我問成都為何有這樣的發展,他們跟我說,成都人有豁達的思維,因為當地地震連連,他們跟死亡很近,明白有些事不必執著,會豁開去,做事少些框架,當然不代表沒有,肯定有」。
成華區的指南描述近年內地社區規劃的發展,最早是深圳2008年開始研究,上海在2015年隨之推行,上海嘉定區2016年還出版《社區自治工作指導手冊》,社區「自治」在內地是怎樣的概念?翻開成華區指南,裏頭開宗明義,「與由下而上的、通過政府與民間團體合作從而動員居民積極發展的『社區發展』不同,我國的社區建設運動是由上而下以及政府體制改革的一部分,體現了以行政力量推動社會運行的政治傳統」;不過同時確有提出「還權」概念,「成都市自2016年起推進城鄉可持續總體營造,在『還權、賦能、歸位』的基礎上,在居民自發組織過程中,建構社區的主體性,提升社區社會資本……」
伍教授重申內地社區規劃具維穩作用,然而「他們接觸外面的資訊也不會差,這是全世界都在做的,除了香港,台灣也做了很多年,社區規劃師這個制度是由台灣開始變得正式的,日本也有社區營造,亦有規劃師會落區,但如果說到除了政府訓練的規劃師外,還會邀請居民去做自己社區的規劃師,一起去規劃,這個模式可說是台灣所創的」。今天台灣不少地區營造的創意已為人熟悉,如台北將公園開放「認養」的做法,「有組織認養後會與政府部門合作,再設計公園空間,又與學校合作,讓小孩認養一棵樹,幫忙設計小卡片介紹。這是積極讓大家能用到這個空間,在用的過程建立社區關係,令大家身心靈都健康些,做法已很普遍」。
你睇人哋社區規劃幾好玩
社區規劃,在今日香港依然付之闕如,「我一有機會已經講,講了廿年都沒人理睬,這就是香港,令人很frustrated(泄氣),你睇人哋幾好玩,社區規劃就係咁好玩」。我們有的,是觀塘造價5000萬的音樂噴泉。她憶及往日中央政策組曾邀學者給予意見,最後政府卻每區派一億,衍生小白象工程:「我當時已說做這類項目是有趣的,又有就業機會,可讓當區的人參與研究,規劃師或設計師有工作機會,點知講完佢派錢叫人起嘢,眼都大埋。」
2011年伍美琴在港大工作時,曾為中西區區議會做研究,讓學生參與構思整個中西區的發展,設計圖包括連結海濱、建立平民大笪地、大帆船博物館,「但因為香港沒有社區規劃,區議會是諮詢角色,唯有將這些項目斬開,在各種政策範疇去問能不能做。後來當然不行啦,每個範疇早就定好優次,還想各個項目能一起實行,怎麼可能發生?簡直是神蹟才會發生,結果無一成真,或就算成真都做得零碎,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不過她仍寄望區議會可做到更多,「雖然做到這樣(上述成都項目)有少少難度,要有資金,最重要是空間」,「但可以教育當區居民」,everyone is a planner,「不要像奴隸被城市空間駕馭,你每天的生活都被社區空間克制着,不要覺得不關我事,是規劃師的事,這是錯誤的概念。你每天都在用這個城市,你話你係咪專家?點會只有城市規劃師才是專家?規劃師可能在某個範疇冇你咁叻,作為用家,你肯定有權利義務去參與規劃」。另外區議會也可先構思計劃,「到水到渠成時就把它拿出來,這其實是我引用一名公務員的話。我曾為渠務署研究將渠道活化成河流,你想想(要實行)有多困難?但那時署方有官員對我說,唔緊要,我們先做,來日政府有這個政策,我們立即拿出來,不就做到了?」她嘆:「有時政府就是這樣,無端端也有十項紓困措施,講咗咁耐唔得,突然之間又得,你唔知佢幾時得㗎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