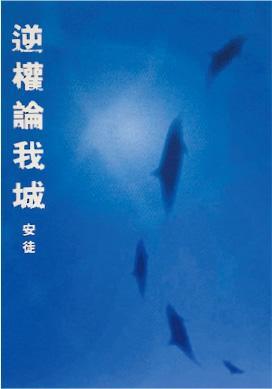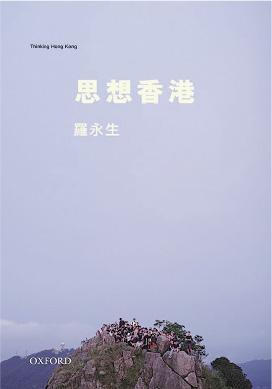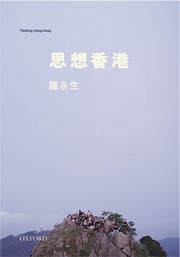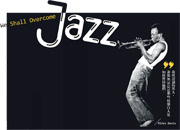【明報專訊】二○一四年,人人尊稱「生哥」的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在本欄接受過阿離專訪,被記下「兩個多小時的訪問,羅永生沒說過一句『愛香港』」。
那年風雨來臨前,他出版文集《殖民家國外》;今天他再度受訪談新書,是日清晨新聞直播,是酒店外突如其來一場國安公署揭牌儀式,香港人當下經歷的,已是隔幾日便捲來一個大浪的日子。急浪還逼得香港人向城市集體表白。
問常談主體性的羅永生對「好撚鍾意香港」直幡的看法,他答:「看到巨大的熱情,但用這種方式表述則相當無奈。」
有得講其他,難道會只想講這句?仍保持冷靜客觀態度的他更說,「某個意義上來說,我唔係好鍾意香港」。
回首香港來時路
這份冷靜貫徹他在「星期日生活」以筆名「安徒」所寫的專欄文章風格,當中很多收在新出版的文集《逆權論我城》。短打以外,他同期又出版《思想香港》,則收錄一篇篇格局宏大的論文,把對黃國鉅劇作《漁港夢百年》的分析評論放在首篇,從盧亭傳說談香港人身分的前世今生,安排一個殘酷又美麗的史詩式開頭。讀下去,沒有神話,也沒有寓言,他總是向直拉一條跨越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的時間線,或向橫切出連接國際大勢的時局,深潛歷史敍述裏不曾被照亮的角落,去撿拾珠海事件、中文運動、文化大革命、六四等每場政治運動在香港未曾被留意的碎片,放進世界發展與思潮裏,為過去至現在的香港重新定位,編織屬於她的故事,「是此城的男男女女持久掙扎,艱苦地尋找自由和確立自己身分的歷史足迹」。
香港故事為何難說?
「香港是一本很難讀懂的書。」曾有中聯辦官員這樣說,這句話大概又可翻譯成也斯的問題,「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簡單問便是何謂香港人。羅永生把講歷史的焦點從六七暴動和保釣運動移開,寫永遠在史書只有一兩句的珠海事件(一九六九年)與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一九六○年代末起),搬開一堆陳腔濫調,顯現香港故事更多輪廓。「中文運動的歷史作用、地位是什麼?我們很受七十年代論述的影響,那個年代論述的架構是,經過六七暴動之後有一段激進化的時期。如果你翻關於香港學運的書,會說中文運動只是一個過渡,高潮在保釣,這很明顯是個中國民族主義的論述。」
「那時遠比我們想像中複雜很多。」時代背景是全球冷戰格局,政治意識形態分為兩大陣營。「珠海事件」中,珠海學院開除十二名批評高壓校政的學生,學生抗議獲大專生及學生組織聲援。十二人之中的吳仲賢後來雖以托派社運人物而為人認識,然而羅永生翻出吳一九六九年所寫〈珠海學生會的展望〉一文,卻發現他援引殷海光等自由主義學者的各種見解。殷海光在台灣因批判蔣介石獨裁受政府打壓,而珠海學院由親國民黨人主持,故吳仲賢的主張當然不為校方所喜。有趣是後來吳有份創辦的《70年代雙週刊》雜誌是中文運動重要推手,親中共左派又因緊跟上頭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路線,容許殖民體制存在,對具反殖精神的中文運動大潑冷水。如此,吳仲賢在「右」邊是異見者,轉「左」路線又不與這些左派一路,把察看歷史的燈光照在他身上,便顯出當時青年如何在受各種政治思潮影響之下,「尋求一種獨立的反對派政治方向」。
從時代流變中梳理香港身分
「看香港如何走過來,不能離開這種錯綜複雜、多元的源流,香港從來都有非常廣泛的跨國聯繫、政治思想及文化資源,這些都在回應何謂香港人,在答『點解我哋咁撚鍾意香港』。」吳仲賢、中文運動,均非歷史沒記載的名字與事件,但羅永生以事件的前因後果為骨幹,搭出一個龐大框架,花盡心力爬梳細節,寫不同事件中時人各種想法如何碰撞糾纏,指出當中的混雜性(hybridity),為香港的身分循時代流變追蹤一條脈絡。當我們視香港為一個主體,她既非殖民者口中的漁港變成國際大都會,也不是中國國族主義之下說的「遊子歸鄉」,切實走過的日子,經歷過的起伏跌宕,都是不斷在追尋「我是誰」的掙扎之中成長,逐步來到今天,「透過書寫、分析,起碼有個說法,而這個說法跟我們現在對自己的說法是講得通的,自我才不會完全被過去壓到透不過氣來」。
離開留下 都是難民
「我們為何會說好鍾意呢度?因為我們有自我,這個自我要健康地生存。」現下我們彷彿看見名為「香港」的共同體,正痛苦地在逼狹空間扭動着。八九之後,因為痛苦,他記得兩三年之間,許多人選擇漸漸遺忘、轉身,「難保香港過去幾年,特別是過去一年的事,到某一個時候,大家會說我們應該放下包袱、遺忘不是什麼壞事」。今次也許不待兩三年,我說,痛苦已然臨頭,這一刻必定有不少人痛得幻想過忘記一切。「香港現在可能從挫敗中變成另一個難民社會。不是離開了才是難民,就算留下來,也可能變成難民社會,人人重回難民心態。你想想,走難落來的人,不就是太痛苦,所以說咩都唔好理,變成一個短視的人,不需要有承擔,不需要對他人有責任?」
說什麼共同體,什麼痛苦與自我,好似太抽象,但歷史的循環反撲,其實好real。羅永生說他的一代人,在去年社會運動爆發以後,很多在問「香港點解搞成咁?」然後又問「我做咗啲咩?」開始感到懊悔。「不知後生一輩是否很多人覺得做多了什麼,但我們這代的具體經驗卻是,有些人現在才覺得少做了很多。」一切懶理,甚至否定過去的自己,羅永生說始終要付代價,「過去幾年就是一種復仇式的反彈,社會累積那種不公正,是會報仇的」,「如果選擇否定自己,否定到幾時先夠?你永遠不會知道。一直否定,會去到一種自我傷害的地步」。
香港人重新認識自己
「香港這本書很難讀,是什麼意思?我想講清楚這個意思,不能全部講清楚,就盡量為難讀的地方給出更多資源去思考。」我說,讀你書寫香港,筆觸總帶點冷靜抽離,會否因為你自感與運動有距離?「哈哈哈哈哈」,這深受學生喜愛的教授,頂着清爽白髮談笑風生,側面看亦風采非凡。「我覺得冇乜好大距離。」他坦言在二○一四年時,「當時我的整理與學理分析,是想為整體運動做一個掃描、報告。而過去一年發生的事太豐富,我不可以說自己很了解裏面的狀况,也在學習、理解,甚至認為我退休之後更沒有利條件去做這件事,只是將這歷程中產生的想法,用我認為合適的方式,如看大家沒空看的書、整理大家沒空梳理的過去,提供給做決定及實踐的人,在當中找到有用的東西」。研究香港,他形容「好似甩唔開咁」,「後殖民研究有很多別的可以做,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也很有興趣,但我總想扯回來回應香港的現實」,他說沒拉開距離,反而一直靠近。
離不開,仲唔係愛?「某個意義上來說,我唔係好鍾意香港。」還不止,他進一步解釋那種「唔鍾意」,「對我來說香港唔係咁,不是因為香港累積了我很珍視的什麼,好鍾意佢、冇咗佢唔得,而是可能好憎香港某些事,但放在這個語境之下發覺原來是寶。或者我曾經以為好垃圾的東西,放遠些去看,其實好正」。什麼讓你唔多鍾意?「譬如香港人的某一種淺薄。但唔係嘅,當你有比較的視野、闊一點的眼光,或者對照中港台,發現唔係喎,香港人就係正喺嗰度,就係嗰度最真誠。正因為香港人咁市井,才對精英大論述有抵抗力。」
香港的「庶民道義」
他在《思想香港》裏論述港人不願遺忘六四時,其中一段說法尤絕:「作為一個難民城市,也作為在冷戰左右派思潮夾縫下成長的地方,香港的文化底蘊就是一種『庶民道義』的直觀,對言詞蠱惑的高度懷疑與敏感,令得她對官方意識形態宣傳具備『天然』的抵抗力……這裏的人根本沒有興趣去區分『社會主義民主』還是『資本主義民主』,使自己迷失於這類意識形態迷宮。這不是因為這裏的人對『普世價值』也可能是被利用的謊言毫無警覺,而是他們不會愚蠢或者冷血到以為,在鮮血與赤裸的暴力面前,還有需要去區分『資本主義屠殺』和『社會主義屠殺』。」
這並非冷眼觀察,來自他往各地交流所見所感。他受訪時解讀,「對照內地,很多讀書人天花龍鳳搞一大輪,大家在同一個圈搞到好複雜,我一看,中國人真係好有思想,但你再問,這些思想有什麼用處?其實到最後都是不同的人用知識來爭寵。在大歷史事件發生之後,一層一層去問,會知道這是香港很獨特的地方,好『我哋』。這些才值得書寫,值得說她為何會如此生存下來。這本書愈來愈難讀啊,原來最市井最讓人看不起的地方,就是韌力所在,於是我愈來愈鍾意香港,哈哈哈哈哈﹗」他笑起來帶着覺得事情很好玩的老頑童神態。
無言語道出的故事
想來他說的不陌生,香港人有時都愛自嘲市儈,但如此角度卻新奇:「這需要不斷拆開,讓香港在歷史累積下來的精神面貌返番嚟,呼召將來或現在的香港人重新認識自己,那種精神面貌很豐富,有很多potential。」從一向被認為負面的特點看出積極意義,他說亦受這一波運動啟發,「大家一路鬧,鬧緊自己、鬧緊身邊的人、鬧緊上一輩,但同樣的東西,另外一面會突然爆發出來」,「之前如何看不起自己,只因沒有語言把它說出來,連自己都不知那另外一面,所以抱很強的self-hatred(自我憎恨),但這一面其實香港人一路都有……」說着,他眼圈驀地紅了,一時說不下去。
揼石仔一般重組香港人尋找自我之路,羅永生心中着緊,着緊這個城市為何不能說出她的故事,「當提及時很快被sideline,或被其他東西壓抑、收編」,他人硬套上的說辭,又統統不合身。想道出香港的本土性,需要另一種語言,需要更多創作,他嘆「未夠,還是很雛形」。
「面對自己」這個課題,正是他自身與這個城市解不開的扣。一九八三年任中大學生會會長的羅永生,信過民主回歸,信過中國改革有前途,六四後,「自己之前的世界觀面對頗大危機,在那個時刻覺得很多事情要重新思考、重新釐清,不只我自己,還有這個時代」。書裏亦收錄關於民主回歸的一章,「那時太樂觀自信,這後來都納入我的歷史反思」,「若有些人覺得我抽離,是因為跌過落去,有警覺拉出距離」。眼見昔日同行者當上人大政協,也曾有人來邀他忘掉過去,「一起搞好香港」,但他始終沒選擇「上船」,講到尾還是「過唔到自己」。一直留在學術界,他退休後仍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見證過運動退潮時人心逆轉之可怕,但今天沒那麼悲觀,「平民百姓會變到好犬儒?我覺得最多去到冷漠,返番去做順民囉,唔出聲、消費娛樂,總之唔好掂政治,做一個『經典』香港人、難民一代的香港人,去找出路,沒出路就順應;以前不唱國歌的,現在唱得大聲過你」。
迷茫失落 不如讀哈維爾
強權高壓進駐,逼停抗爭,他想到昨日捷克。「一次過動員很多人,很理想主義,很熱中那個moment,一盆冷水下來就收晒。」如果迷茫,如果失落,生哥教讀哈維爾,「你或會說那些政治理論已經唔work,那我會說你沒讀懂哈維爾,到最後他說的是如何面對自己,在一個困局中,很多事不由你控制,要在極權底下維持一種力量,不是靠一套怎樣的綱領,而是你點過到自己。他說的是我們如何生存,不是苟活,甚至是一種potential的反抗」。
守住自己的位置
「當時捷克『正常化』的趨勢,人愈來愈放棄問自己這些問題,造成一種風氣,連最後一點都守不住。」要堅持問什麼?「你是否活得忠誠於你自己,活得consistent。所謂身分、自我認同,就是關乎你是否始終如一,對不對得住過去的你。這對我有很大啟發,世界亦然,人們開始出賣自己時,世界就會淪陷。當有很大力量把我們推向另一邊,做不到大事,便守住位置。哈維爾也告訴我們要關心身邊的人,互相支持,當時很多地下文化都是各自圍爐,但圍得來有公共性,不是敏感事全然不談,只關心私人問題,不是幾個朋友聚埋日日打麻將不理世事。勇氣,就見於這些貼身的事情上。」
以後你還敢寫嗎?「哈哈,我唔知㗎」,這位專欄作家笑問:「《明報》可以做到幾耐?『星期日生活』又做到幾耐?」他正色說:「可以做幾多就做幾多,屬於思想或文字的工作,無論世界變成如何,都有我們的位置,只要我們給自己尚能思考的地方,無論地方在哪,都可以做下去。」落筆會否避忌吓?這樣問又被他趁機取笑,「如果你寫完畀我睇吓,可能安心啲啦」。「咁我又唔會。」他聽着高興,朗聲:「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