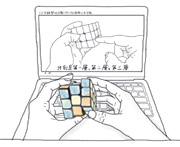【明報專訊】連接大埔墟街市與泮涌村有一道石拱門,拱門底行人如鯽,站在一端,想要拍下一張素淨的靜景幾乎不可能。短短步程未及讓人浸沒在完全的黑暗之中,因為盡處有光。光源正是來自拱門另一端的泮涌村。拱門上是鐵路軌道之所在,當天經過時未逢列車經過,但從前村長羅叔叔口中得知,因為泮涌與軌道相鄰,列車的轟轟聲早已融入村民的生活背景,就如蟲鳴於郊野般自然。「都是聽火車聲大的,以前是兩條臂『程尋程尋』咁推,啲轆大好多,燒煤還是燒柴呢,味道梗係有,猛噴黑煙」。
與鐵道相鄰 火車日夜「程尋程尋」
穿過拱門,即見泮涌村口的士多,前村長羅叔叔就坐在士多路邊的餐桌旁。拱門上的鐵道就在一條小馬路之隔的身旁。鐵道距離民居近得如此不尋常,羅叔叔反問,當年村民不可能就範吧?便告訴我們他從父親口中聽來關於那場關鍵的暴風雨傳說。四百年前,泮涌前方原是汪洋,村與大海之間有一片淺灘,他曾在村公所後來已被丟棄的一些文物上看見「湴涌」二字,推想那應為村的原名,而泥湴(音:辦)亦即濕了的泥。在1898年九廣鐵路建設之時,將水圍與大埔頭割裂開來的軌道鋪展而來,臨到村前這片濕泥地上,卻遇上了一場大風暴,海浪將這一段捲走。平息以後,鐵路公司決定將軌道的位置向村的方向推移,建成於現時所見、泮涌村外僅僅十多呎的位置。而原來被強風摧毀的殘餘路壆與鐵道之間的那片泥灘,後來亦順勢填成農田。
因村前泥湴得名
羅叔叔仍在襁褓的幼年與家人搬離泮涌,後來因為大哥考進伊利沙伯中學,想到這鐵路之便,舉家在重修舊居後的1956年遷回。哥哥於是每天乘搭火車上學,「你知唔知,以前不是叫旺角東站的,叫油麻地火車站!」
羅叔叔指,泮涌最初應由文氏聚居建村,後來遷往泰坑鄉,空置的泮涌遂由其他姓氏的人陸續遷至,包括他十八世紀末才從澳洲乘破爛木船來到的太爺,「你信不信?沒有大洋船,鄭和下西洋都是坐木船」。單身的太爺來港後結婚,生下了羅叔叔的爺爺。爺爺卻沒孫兒幸福,當年到港島皇仁書院上學,因為沒車路沒列車,必須翻山越嶺。「據我所知,太爺要給錢請人擔行李,就從這裏後面山,攀過去荃灣,經鉛礦坳落城門水塘那邊,到荃灣海邊搭船過去港島」。當年的「越洋留學」就是如此,在外寄宿的爺爺每逢暑假才能回家。
井頭曾有娃娃魚
入村參觀,羅叔叔帶我們穿過村屋的脊背,隔着鐵絲網遙望遠方山間的石壆,指說那是此村最大的神明「大王爺」,邀請我明年元宵節再來參觀,看大王爺如何被「請」至燈花會,在我們剛才喝支裝汽水的廣場、從前曬穀的禾塘擺放三天。
下一站,我們步上村中高處看村中「井頭」。小小的井口兩側有錦鯉石雕,內裏錦鯉成群。羅叔叔說都是村民放養的。「1964年香港天旱,大埔墟個個來打水,一日到黑輪住擔,曾經吸到見底!」村民後來裝過鐵板,定時蓋下以保水源。此井頭所以獲同行的彭玉文稱為神井,因為裏面曾養活過娃娃魚。羅叔叔指,當年有人從內地把娃娃魚帶來,本想售賣,開價十萬,想吃的人又怕違法,賣不出而最終只好在此放生。娃娃魚現獲列為國家二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彭玉文指其對環境潔淨與否非常敏感,一丁點的污染都無法生存。相信水井的石縫可以外通,娃娃魚後來也不知所終,為神魚神話留下尾巴。
文、圖˙潘曉彤
…………………………………
掌故:「湴涌」
位於大埔區的泮涌村,屬於本地圍頭村。昔日原名「湴涌」,在1688年的康熙 《新安縣志》便有記載,當時屬於新安縣五都,到了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的《新安縣志》則屬於官富司管屬本地村落。湴字常與泥字一同使用,泥湴即是爛泥的意思,這是由於湴涌位於林村河與大埔河出海交匯處,周圍都是冲積的爛泥,故有此名。在1960年代大埔仍未開發前,泮涌四周田疇遍野,景色秀麗,也有不少候鳥在附近棲息。
泮涌在明朝初年已經開發,當年深圳崗下文氏的文蔭公從陶子峴遷到這裏附近,建立文家莊。到了清朝時期,來自南頭的麥氏鐵象公,在湴涌擇地建成傳統的本地圍村,後來唐、羅、陳氏也先後加入,他們以漁農樵商為業,是大埔區內繁盛的村落。
圍村建築東北朝向,有七排八巷,四周曾建有圍牆,圍底則為神廳。朝北的圍門在重建後仍予保留。在圍東北側的褔德神壇旁,仍見數百年前立圍時所植的巨樟樹頭。在圍西南有著名的龍口井,泉水清澈,據說是大埔區二大名井之一。
在1899年,駱克的接收新界報告中,當時村名仍是湴涌,有本地100人的紀錄。湴字改為泮,有說可能是1958年,村旁籌建泮涌公立學校,為求文雅,故改今名。
泮涌燈會,昔日曾是大埔區內盛事,在每年農曆正月十五的上元節,村民會奉請神廳及村內所有神明,包括井神和門神土地等,捧到圍前蓋搭的燈棚神壇供奉。到了正月十七會進行天姬節的行船儀式,由緣首捧着紙船在鑼聲中繞遍村內,村民將把代表污穢的雞毛、四色豆、黑炭和元寶等放進紙船。集齊穢物後,紙船在村外火化,以示送走。
文˙沈思
…………………………………
生態圈:地方神靈與樹精山鬼
泮涌村圍門左側,有一特別神位。神位不大,稍大於A3紙。我跪下來看,神名被一排紅紙遮蓋,朱谷主也跪下來替我逐張揭起,方便拍照,於是見到運頭角感應大王之神神位、粗石坑感應大王之神神位、大步頭土地福德之神神位。
我第一次知道有神以地方為名,向羅先生請教。原來供奉地方神祇的神壇或社壇,從前遍佈鄉郊路邊空地,神位上不註明地名,因為對地方供奉者來說,該處地名是已知,神位只會以「『本境』感應……之神位」標示。
重置敬諸靈
當鄉村都市化,地方神位在「本境」被挖走、掩埋、碎裂之前或之後,被有心人救起,重新安置在「境外」安全地方供奉,新神位的刻字就要將「本境」改成本來地名,否則便不知是那處的「本境」神祇了。同等職稱在各境由不同神祇擔任,神位必須清楚寫明本鄉,否則神祇便歸錯位。
有些地名在今天已棄用,如粗石坑,很可能就是今日的大埔河,或者在其上游「碗窰河」;也有地名是沿用至今的,如運頭角,風景及土地用途卻已大異。當年碗窰工場瓷器出窰,就地搬上貨艇,沿碗窰河下航到運頭角,再駁上大船出口東南亞。運頭角神壇,很可能建在當時大埔河出海口附近。有成語「頭角」崢嶸、嶄露「頭角」,上禾坑村原名「頭角」;是基礎、始端的意思,「運頭角」地名詞義是「瓷器貨運的始端」。
羅先生曾向官員建議,把諸鄉神位轉到村的另一入口旁闊大空白石碑,但遭當局否決。是認為地方神靈之遺棄是城市化必然過程,因此不敢讓自己開先河?
對於這三位神靈,我沒有多大認識與感應,但對於曾見過原本神壇,曾在未都市化前的運頭角、粗石坑、大步頭渡過童年的鄉親父老,如羅先生而言,為諸神復位,一定有重大意義。俄裔美籍小說家納博科夫,曾用一個短篇把這種意義闡釋清楚,令人深受感動,以下述其概要:
山鬼童年伴
一個陌生人敲門入我家,相貌似曾相識,感情可能很深,卻認不出是誰。他在扶手椅坐下,細訴俄羅斯故鄉樹林風月無邊、青春永駐的風景,追憶童年往事,說自己當時到處鬼混,喜歡開人玩笑,被罵也樂在其中,經常在森林從早玩到晚,猛烈地打呼哨,使勁地拍手,驚嚇路人。有一次我在森林裏的一個昏暗地方迷了路,他不停把林中小路弄得錯綜複雜,讓樹幹亂轉,閃現在枝葉叢間,如此對我惡作劇了一整夜。我雖被戲弄,但依稀記起倆人在森林追逐打鬧,一玩就是好幾天,當年快樂無窮、無可替代,至今常繞心頭。我終於記起他是誰。客人原來是故鄉的木精靈,一個淘氣鬼。話題一轉,客人描述親眼看見極權政府奪權後在樹林一批批槍決反對派,木精靈被嚇怕,從故鄉逃亡至此(美國),是無家可歸的孤魂,不久就要死去,請我說愛他,坐近點,把手給他摸。蠟燭閃了幾下熄滅了,熟悉的憂鬱笑聲如鐘震響然後消失。我開燈,扶手椅上並沒有人,只有一股淡淡的樺樹濕苔香氣飄蕩在屋子裏。
冷待歿鄉情
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陳雲,從外祖父及村民口中得知本地山鬼,也曾描述戲弄大人小孩方法,情節一如俄羅斯木精靈,可見兩者也是淘氣鬼,職級相同。而納博科夫用小說體表達,其間人性鄉情與政治覺醒,令讀者印象深刻。
運頭角感應大王之神、粗石坑感應大王之神、大步頭福德之神,當然比木精靈或山鬼高級、莊重,是為鄉民解決困難、實現願望的善神,與戲弄之事不搭邊。一個為納博科夫帶來麻煩的淘氣鬼,也得到他如此深情之愛,遑論有恩於鄉親父老的地方神靈,祂們應該得到更大的回報。羅先生重置諸地方神祇的心思,與納博科夫一脈相承,關乎原鄉濃情,土地之愛,傳統文化薰陶,對棲居地方真摯感恩,對神秘力量謙卑敬畏。這些高階情志與價值觀,官方一時理解不來,等待解讀再慢慢消化,看來三位地方神靈,要繼續屈就一段日子。
文˙彭玉文
Ways of Ruralist Seeing(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