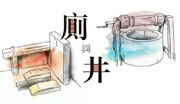【明報專訊】我很後悔。後悔幾日前收到編輯黎佩芬的邀稿短訊時,我答應了她。
那刻我正在西九龍裁判法院的記者室裏,聽辯方大狀馬維騉公讀一份保釋條件的草擬文字。聽過幾堂他打的官司,故此感覺熟悉,熟悉感有助安慰心靈。我一如以往低頭奮筆疾書、字體潦草,一心二用。在短暫的空檔裏滑一滑手機,看到黎的短訊,有點猶豫,心想連日來已寫了很多字,不肯定到了星期日還有沒有題材。但隨即又進入第45被告王百羽的保釋陳辭,我心急想拿起筆桿抄寫,就先答應了她。
誰料當四日四夜的提堂聆訊完結後,我實在下筆無語。庭上控辯的陳辭因受法例限制而不予報道,故我不能只當個忠誠的廢物,把筆記簿上潦草難辨的字體翻譯。庭外前來支持的市民,綿延白晝和黑夜,精神面貌堅定而觸動,但我寫不出煽情的文字,因為整件事最後籠罩我的不是溫暖的熱度。我第一次去完法庭而深深失語,五臟六腑被津液撐滿,而春天的天氣灰白潮濕,我懷疑自己餘生都要如此負重前行。
超過40小時的提堂經歷,我一直或坐或站在法院一樓的記者室裏。這兒有如災難現場,三十幾個座位但擠了七十餘人,房間混雜了一日三餐的飯餸氣味,一直沒散。大家直勾勾望住前方的電視畫面,追蹤比指甲還小的被告臉容。我們彷彿毒氣室的管理員,透過閉路電視觀察眾生痛苦的掙扎,每當我拿出紙巾抹去眼淚時,常常不經意的把圍巾拉緊,想遮住後頸,因為感覺自己正身處另一個更大的毒氣室中受到監視。隔了一重又一重玻璃,只有上面才知道,我們這些人當中,又有誰因為說多了話寫多了字,以致名字已經被盯上了。
提堂第一天(3月1日):
這是一個我不曾見過的西九龍裁判法院。
黑衣市民鬧哄哄的圍住法院大樓,由正門所在的通州街,轉入東京街西,再轉入英華街。進入法庭旁聽的票早已派完,但前來的市民依然絡繹不絕。我用半跑之態,也花了六分半鐘,才勉強把一條壯大的人龍巡禮一回。
陽光灑在眾人的臉上,大家額角都在冒汗。調派過來的藍衣警員人數增加,但怎也及不上流水式市民填補的速度。這千人意志不減,拿住書讀、播住歌聽(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接受記者訪問。偶爾有人嗌一句「香港人」,眾人回應「加油」,還有更多曾經佈滿街頭的口號,春風吹又生起來。接連幾條街都擠擁得寸步難行,但人人互相禮讓,這兒有一種2019年6月的氣氛,讓人得到瞬間溫暖的throwback。
法庭則不斷將提堂時間押後,2庭、18庭、陪審員房、記者室四個地方,直播庭上情况,實時收音清晰。被告欄的咪由於開着,因此大家甚至乎聽到他們輕鬆的對話,記者室屢屢傳出笑聲。「出面好嘈喎,示威咁喎!」、「見字飲水呀!」、「So I say I love you」(唱出來)、「大家不要懷憂喪志!」、「呢到收到?老婆我愛你!」記者按聲尋人,每有被告說話,大家就鬥快估說者是誰,「哇哈,阿藍唱姜濤呀!」、「呢個林卓廷啦!」若眼前出現高點,往往預視之後將滑落的低谷,果然,這也是香港人跟47名被告最後一次人性化的接觸。在這一刻之後,他們便已身不由己。
聆訊最後在凌晨2:45結束,第10被告楊雪盈啪一聲在被告欄暈倒,庭內一片慌亂,庭外一片憂戚。這不是熟悉的香港法院情節,沒有人知道擺在前面會是什麼命運的筵席。
提堂第二天(3月2日):
四日中只有第一天出現太陽,這日天色慘澹,霧鎖愁城。一眾被告失去了前一天的活潑,他們於退庭後,一直等到清晨5點才分批乘囚車離開法院,再於上午8點幾返回法庭應訊。被告人精神委靡,家屬、律師團隊,記者和公眾也疲於奔命,這天警方的佈防更加嚴密,屢次驅趕守候市民,前一日大樓門外的浩瀚情景不再。情緒被硬生生的壓抑,黑衣市民退到相隔一條馬路的對街,徘徊多時,對庭內的人無聲地支持,對庭外的暴政無聲地抗議。
這一整天是被告的保釋陳辭,因控方的突然提告,令很多人都措手不及。不少辯方大狀皆一人代表幾個被告出庭,僅第16被告劉偉聰選擇自辯。進入保釋陳情階段,法庭又換上另一種氣氛,席間說出了每個被告自己的人生故事,很多人縱使你叫不出他的名字,但他的過去跟你和我相去不遠。他們是連登巴打、是前空姐、是社工、是前記者、是大學生、是博士生、是文員、是律師、是營銷員、是醫生、是飛機師、是區議員、是立法會議員、是大學教授,是大學講師,但某朝一個細密的網撒了下來,他們成為「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被告。
這個罪名很恐怖,這種馬拉松式的提堂很荒誕,這一切一切都超出香港人的認知。但我們不能把當中的一言一詞報道出來,記者室開始變得很靜,只有手指飛快敲在鍵盤的聲音,和筆尖摩擦紙張的氣息。既然不能報為什麼還要寫?因為這成為我對庭上被宣讀的故事表示尊重的唯一方式,這麼遠,那麼近。
提堂第三天(3月3日):
47被告連日來沒機會洗澡、沒外衣內褲可換的窘境被報道出來,是作為執政者依然高舉人權旗幟的恥辱。而馬拉松的聆訊依然未完,這天先有第35被告楊岳橋、第30被告郭家麒、第20被告譚文豪以及第46被告李予信表示不再聘用大狀梁家傑作代表陳辭,接着再有更多人包括第10被告楊雪盈、第33被告何桂藍、第38被告林卓廷等表示辭退大狀,選擇自辯。
突然發現,以往我不感興趣的人物,他們的故事原來這麼動聽。他是醫生,原來大學未畢業便已經成立社會組織,之後多年在公立醫院行醫,再晉身議會。某一天突然被拘捕,他錯失了很多已承諾的手術。他是一個爸爸,上星期日進入警署報到時,深深抱了一下女兒道別,可她卻睡着了。於是爸爸產生了莫名的恐懼,生怕女兒有一天懂事時,會怪責自己當日為何沉沉睡去。
我責問自己,過去為何沒有用心做好人物訪問,一直覺得眼前這些臉孔都是理所當然,沒想過這天他們講的每一句話、承諾的一切保釋條件,都有如訣別。法庭向來是極度壓抑情緒的地方,措詞冷靜看似文明,然而這個傍晚,說的人摒棄了法律詞語放下了by default的面容,傳來哭聲傳來飲泣;我一邊拿紙巾抹去眼淚,一邊覺得香港整個公民社會可以承受的重量,可能只剩下最後一根稻草了。
這天晚上8點半退庭,走出記者室,我看見精神奕奕的吳靄儀。她穿著桃紅色的絨褸,跟我們沮喪的眼神相遇,有記者問:「庭上的陳辭不能寫,那我們還坐在這裏有什麼意義?」她瞪大眼睛回話:「物質是不滅的!你聽到的內容不因為不能報道而消失,你受到影響,你會再影響其他人。你坐在這裏,我坐在這裏;你見到有我,我見到有你,這一刻我們需要知道,大家都一同在這裏。」
先有記者向Margaret討一個擁抱,然後我們幾個人排隊,逐一緊緊摟住她。其他公眾看見了,也紛紛上前,怯怯的問:「Margaret,我也可以抱一抱你嗎?」
離開法院大樓後,我看見手機的燈光照亮了街道。我踱步想看清楚每一個前來市民的臉孔,做了一些訪問,聽到很多故事。兩小時後囚車駛出,眾人追住車奔走大喊:「頂住呀,我哋喺到呀!」直到11點15分,送別了最後一輛囚車,這些香港人才依依不捨離開。
提堂第四天(3月4日):
去到下午5點,所有保釋陳辭終於完結,而裁判官也否決了放寬報道的限制,法庭表示傍晚7點將有眾被告的保釋申請結果。忘了是哪個家屬說,當聆訊進行時,仍可欺騙自己保存希望,最痛苦的時刻,會是發落之後。
法院外今日來了送大衣的人、送熱食的人、拉小提琴的人,各人都用自己的方法,向彼此展示自己的存在。傍晚7點15分,法庭未有動靜,但位於一樓的記者室,卻聽到街上傳來震天的口號聲。我按捺不住跑落樓下察看,只見風雨下亮起了上百點手機的光,形成一條發光的街道,群眾情緒激昂,如潮水席捲唱出闊別太久了的《我願榮光歸香港》。這個畫面持續了大概20分鐘,在場警員就舉起紫旗,驅散前來聲援的市民。
隨即開庭,裁判官宣布15名被告獲准保釋,並逐個跟進報到安排。但這個短暫得享自由的消息頒下未及15分鐘,主控就表示律政司提出覆核,裁判官繼用他不曾改變的聲線宣布全部47人繼續還押。
「吓!」除了這個字,記者室再沒餘力發出其他聲音。法庭從來是個外人不能詰問的聖地,今後尤甚。我望望表,8點15分,一眾被告最後透過法庭直播傳來的說話,是「政治犯無罪 香港人不死」、「政治檢控可恥」、「多謝各位律師」、「對唔住」、「大家撐住」。
我推門離開記者室,在巨大的沉默中,傳來一把女聲的嚎哭嘶叫。是第40被告呂智恆的養母抵不住情緒爆發,在法院地下奔跑哭喊跪倒,我呆着感覺雙腿難移。另一邊我看見第20被告譚文豪的一對孩子,女兒梳着黃色的蝴蝶結,側頭看着大人愁苦的臉。然後一個戴住黑色口罩剛剛暈倒的女人,給抬上了擔架牀送上白車。現場巿民力竭大叫:「加油呀!保重呀﹗你要撐住!」
同一時間,三個女士在咪前發話,她們是梁國雄的新婚太太陳寶瑩、岑敖暉的新婚太太余思朗,還有朱凱廸的太太區佩芬。我站在她們前面,卻沒聽到三人說了什麼,只聽到旁邊有人說:「為什麼我看到了709律師太太的身影……」
3月5日:
律政司突然表示撤銷覆核被告楊雪盈、劉偉聰、呂智恆和林景楠的保釋。4人前晚離開法院,需遵守嚴苛的保釋條件。
3月6日:
其餘11人的保釋覆核,再被押後至3月11日及13日裁決。另,全部47名被告的控罪聆訊,暫定於5月31日開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