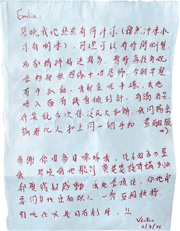【明報專訊】47人案,令我自己陷入前所未有的沮喪:我真的不覺得再有什麼希望。然而在保釋審訊期間,唯一令我可以笑一笑的,是何桂藍(阿藍)在庭上唱了姜濤《蒙著嘴說愛你》的一小段:「So I say I love you,只有愛恆久不枯。」在這個如此荒謬悲憤的時刻,抗爭資源竟然是一首小情歌。這種「違和感」,反而產生了某種不可思議的力量。友人在網上寫道,這是「以幽默(或曰『癲』)揭示了整場審訊的虛偽與荒誕(笑)」。寫得很準確,但我又覺得除幽默之外,還有更多。
早前周永康share了月巴氏所寫關於Edan(呂爵安)的一段小文,留言者非常踴躍(包括本人)。Alex和阿藍半開玩笑說期待我在《星期日生活》寫關於Mirror。我從未研究流行文化,當然不敢寫什麼分析(要寫應該都由阿果寫呀)。所以本文只是寫我個人投進Mirror世界的一點經歷,無什麼理論可言。大家當小品文章讀讀就好。
首先我是如何認識Mirror的呢?我比較out,很少「跟進」香港的樂壇發展,也很少看香港的電視。所以我當然無看過《全民造星》I、II和III(《造星III》決賽時,我見facebook和IG很多人討論CY,方才知道原來香港有名的CY,不一定是那個令人憤恨的CY)。但我比某些人跟得上潮流,起碼我還是知道有個人叫姜濤。乃至年頭的叱咤頒獎禮,Mirror奪獎頻頻,姜濤成為「我最喜愛的男歌手」,引來熱議。然後一些朋友也在WhatsApp group討論,我方才知道有另一個歌手叫Jer(柳應廷)。朋友大力推薦我去聽《迴光物語》,聽了幾次後,便成為某種形式的「鏡粉」了。過了不久,Edan推出首隻solo《E先生連環不幸事件》,頗為轟動,至今在YouTube有超過170萬view(連周永康也有注意呀),亦令我更加注視這隊12人的男團。(不要以為看Mirror的都是迷妹。介紹我聽Mirror和看《男排女將》的,全是男士。)
同代人的凡星
鏡頭回到大審訊。47人提堂那天,樂隊One Promise和Jer推出《明年見》的duet version。《明年見》其實是上年年尾推出的歌,但這是我第一次聽。上星期內,我loop了這首歌超過20次。其中一段令我好感觸:「也許 靜靜地等待 花都不會開 / 茫茫然一生 千里障礙賽 / 讓我破喉吶喊 世界當然未改 / 卻至少有一刻變精彩」。這段歌詞,給了我一點慰藉。我在反思為何會這樣。這首歌絕對講不上是什麼熱血歌(例如「難得夢一場革命不老」那一類),也無法帶來什麼希望。畢竟一刻變精彩,其實即是世界完全無變。然後我得出的結論是:慰藉來自共感。
什麼共感?當現實環境已經非常惡劣,黑暗籠罩大地,還去講什麼拋頭顱灑熱血,反而無法觸動人,因為知道那是false hope、「講大咗」。但《明年見》的幽幽傷感與無奈,聽的時候就好像和歌者一同悲傷。對,世界就是如此殘酷,我們都是凡人,但起碼我們共同在一起。所以當阿藍哼出「So I say I love you」的時候,除了是幽默外,也是在極度荒謬中顯露平凡。庭內庭外都是有血有肉的凡人。政治犯都會追星。在絕對的國家暴力面前,保持平凡已經好艱難。一些老生常談(愛是恆久)、青春顏色,在猙獰的面孔前,散發出微弱的光線。就好像風中的燭光,似乎即將熄滅,卻又確實未熄滅。
或許Mirror的力量,都是來自某種平凡。「平凡」不是「平庸」。說他們平凡,是指他們就好像是會在街上「撞到」的人,好像跟我們這些非樂壇的凡人差不多的(Edan的《膠戰》表現,更加強了這種印象)。他們不像四大天王般只能遠觀,而是跟我們一樣在地上工作、生活。我們所經歷過的(例如2019年),他們也應該經歷過、苦惱過。特別對我這一代人而言,Mirror的成員基本上是同齡的人,所以代入感更強。當然,這種代入或多或少都只是粉絲的想像,未必有什麼根據。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代入感是真實的。
另一點,當然是ViuTV疑似比較「黃」的作風,令某些粉絲希望(甚至相信)Mirror應該起碼是淺黃的。其實電視台是商業機構,不可能真的黃。但與「紅黑紅紅黑」的TVB比較,加上某種虛擬的開明作風,令我們感情上(不是理性上)願意相信ViuTV以至Mirror當中有黃的人(或起碼不藍吧)。林家謙和Serrini肯定是黃的,也在ViuTV現身,算是某種「證據」吧。
這種半真半假、疑幻似真的親切、在地與「暗黃」,令人更能對他們的作品或他們本身做各種詮釋(甚或「超譯」、「作者已死」)。例如《迴光物語》一句「那地厚 與這天高 / 仰首一笑不知道」(詞:小克),引發無限聯想;阿藍可以在Anson Lo(盧瀚霆)的「一世的戰事 一世的意義」、「誰要去領軍 諸位也可能」(詞:梁栢堅)和勁舞中,看到「時代投落每一個人身上的責任,只有自身能夠承載,而總有那麼一秒間,自己的抉擇,會成為改變一切的關鍵,哪怕改變的只是自己的人生」, 以及「人立身於亙古俱寂的天地之中,打破靜止與凝滯的恆常的能量 —— 把自己的生命,活成一種怒放的意象」;而我也能聲稱Ian(陳卓賢)的《鯨落》懷有某種基督宗教精神(其實是因為一位神父share這首歌,令我這想像根深柢固)。
他們也在掙扎
當然,這種想像,很容易就會戳破。在北方資本帝國的強大壓力下,以及電視台的商業計算中,Mirror可以保持這種身段多久,無人知道。畢竟娛樂事業在政治與資本壓力面前,從來都不堪一擊(近來在讀《盛會不歇》這本書,又是感觸良多)。Mirror很難成為何韻詩、黃耀明、王宗堯,粉絲卻應該極不願見他們變成周柏豪、楊千嬅。在兩端不斷急速壓縮的空間內,Mirror可以游走多久?再一次,這些年輕人的處境,和不少「普通」香港人的掙扎,何其相似。
3年前,Mirror經理人花姐接受《立場新聞》訪問,記者問到有些藝人到大陸發展後,被質疑背棄本土。花姐如此回應:「大家諗清楚點解他們去內地發展?因為香港人已經唔鍾意佢哋,已經唔睇佢哋,已經唔再買佢哋嘅嘢。佢哋都要搵食,都有夢想要發展,都有自己的聲音,既然呢度容納唔到,咪去內地發展去賺錢。」繼而再說:「如果唔想佢哋去內地發展,就應該改變我們的思想,聽吓香港的音樂係咪好先,唔好未聽就話唔好囉!」
這段陳述,未必完全準確,但可能都講出我們香港人僅餘可以活得有尊嚴的方法。
在沒有巨星的年代,我們想支持「凡間」的歌手和藝人,也希望他們不要忘記香港;正如在沒有英雄的時代,我們唯有靠自己做好一點、做多一點、退少一點,互相扶持。你鼓勵我,我支持你,相濡以沫。這不會帶來什麼希望,不會石破天驚,未來只會愈來愈黑暗,但也許能否定徹底的屈辱。「即使輸都不算醜 / 同場流汗更加爽快地流 / 被你推進過 非單打獨鬥。」No, there’s no hope. But at least,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話說,阿藍,你在facebook問我究竟是雜食定係「柳炒」定「爵屎」。
好吧,我誠實回答:其實我是柳炒和「Hellosss」(編按:Ian 粉絲的別號)之一,暫時最喜歡的歌是《迴光物語》和《鯨落》。然後上星期我的減壓方式,竟然是看《Mirror 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