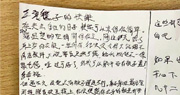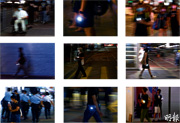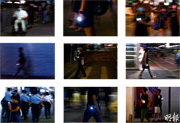【明報專訊】自80年代起,香港的公共財政體制有一個獨特的設計,名為「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現時按香港法例第2A章運作,規定所有地價收入要撥進基金,用於收購土地和建設公共工程及基建。然而,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不能用於興建公屋,因那是屬於房委會承擔的開支;但其實連興建安老設施、竹篙灣檢疫中心的成本都是來自獎券基金,而非基本工程儲備基金。近年不少涉及土地不公義的討論視這基金為造就大白象工程的機制,本土研究社曾稱其為以賣地養基建的「資本旋轉門」,造成今日香港被基建圍城的景象。雖然在早幾年土地大辯論期間,有前高官解釋此基金的運作,試圖為高地價政策開脫,但他們都無法解釋基金的由來。儘管他們或不願揭穿真相,不過更有可能是連他們也不知道基金設立的來龍去脈。關於香港公共財政的研究雖多,但都未曾解釋過這樣的公共財政機制是在何種脈絡下制定。表面上,此基金是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遺留的產物,但其他英國管治過的殖民地都不曾存在這樣將土地收入和基建開支掛鈎的規定,令人猜想這條法律到底從何而來?
經過分析涉及中英談判的香港政府檔案、英國外交部檔案、中國及相關機構的檔案、官員和政治人物的回憶錄和訪談紀錄,筆者發表在《都市歷史期刊》和《華人社會變遷》的研究發現:雖然麥理浩領導的港英政府在1982年因要撥備資金以開發天水圍新市鎮和多項工程項目而設立此基金,但當時制度設計的初衷與今日賣地養基建的規定背道而馳。偏離初衷的契機是中方透過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三作出的要求,港英政府被迫配合這份「歷史文件」而從根本上改變公共財政的設計,對香港的土地規劃和城市發展影響深遠至今。
這個故事說來話長,本篇先由香港的地契問題及與之關係密切的天水圍新市鎮說起,之後再逐步理解港英政府設立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初衷,再剖析中方要求的修改。
「香港未來」—天水圍發展
7、80年代香港前景不明朗。外交官出身的麥理浩1971年就任港督後,一直以城市基建發展為手段來實現其政治任務,解決迫在眉睫的新界地契97年到期問題。呂大樂、Alan Smart、葉健民及李彭廣等多位學者研究過麥理浩與倫敦之間的通訊檔案,揭示麥理浩的政治任務是要改造香港,拉遠香港和中國發展上的差距,使香港能提升為一個先進到當時的中國無能力管治,而只有英國才能繼續管治的模範城市。考慮到二戰後殖民地相繼自決及冷戰等地緣政治因素,倫敦意識到有必要透過香港來維持在遠東地區的長遠利益。經過六七暴動後,倫敦也意識到如果中國決定以軍事形式攻進香港,香港是守不住的;若在97年僅交還新界的治權而退守界限街以南,亦不是現實的地理考慮。故此,倫敦的盤算是爭取以某種特殊安排來繼續管治整個香港。
於是,麥理浩規劃了對現代生活方式事關重要的城市基建,例如興建新市鎮、公屋、教育、交通網絡、地鐵、內部規劃新機場選址於大嶼山,甚至劃定郊野公園等。但隨時間推移,兩個主要問題困擾港英政府:一方面,公共財政體制要為基建投資作長遠準備;另一方面地契問題造成的信心危機已成燃眉之急。即使政府已在1977年與商界的管治伙伴一起組成土地供應特別委員會,物色適合發展的新界地點,但是當時發展商擔心地契無法續期的後果,而銀行家亦不懂怎能在1982年起再批出15年期的按揭,這令倫敦和麥理浩不得不試探北京的態度,華資商人亦渴望試探中英雙方的取態。幾方互相試探地契問題的取態,卻陰差陽錯地造成了天水圍新市鎮規劃發展的結果。
在英國檔案中,與天水圍有關的文件歸檔於外交部以「香港未來」為名的檔案,而非與其他涉及城市發展的文件放在一起,足見天水圍新市鎮在香港歷史中的重要性。
藉地契問題解決97危機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始,麥理浩透過新華社社長王匡向北京提出地契問題,但當時中央政府內部因「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原則,決定先作研討,暫不回應。但藉這機會,北京領導邀請麥理浩訪京,以尋求香港支持中國經濟改革。倫敦和麥理浩都認為這是當面向北京領導人討論地契問題的時機。時任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在1994年出版的回憶錄憶述,雖然當時他對會談不感樂觀,但麥理浩卻相反地以為中國對經濟改革的考慮優先於民族考慮。英國殖民地管治系統傳統上信賴當地官員的判斷,故麥理浩的觀點亦成了倫敦考慮的框架,在後來的中英談判初期,主張用滿清和英國簽訂的條約來堅持香港和九龍半島已永久割讓予英國,只要整個香港包括新界繼續由英國管治,日後經濟上終能裨益中國。
1979年3月29日,鄧小平和麥理浩在北京會面,還未待麥理浩提出地契問題,鄧小平已率先開口,希望英方不要過早提出此問題,中國根本未有考慮任何政策,但不論香港在97年後維持現狀還是由中國收回(值得一提的是,不論中方人士的回憶錄抑或英國檔案,都沒有提及鄧小平堅持收回香港,反而不約而同地記述鄧小平提及過存在的可能性),屆時都會有特別政策,叫麥理浩回去叫投資者放心。事實上,根據魯平、許家屯、黃文放等多名中方人士的回憶,北京直至1982年才開始有治港政策的雛型。但麥理浩馬上回應說,主權誰屬是中英兩國長遠處理的問題,刻不容緩的新界地契問題不能靠一句叫人放心來解決。麥理浩提議把新界地契上的97年限期更改為「只要仍是英國管治新界」的字眼,以不明確地標明限期的地契來解決香港確實存在的法律技術問題。鄧小平不置可否,只是他看起來認同這做法不需中方作任何動作,也似乎沒有違背中方立場。麥理浩再向黃華和廖承志等其他幹部提出同樣建議,態度同樣模棱。當時麥理浩向倫敦報告說,鄧小平等人顯然無法明白當中涉及的普通法概念。今日回望當時,這情况亦不難理解,若當時的北京領導人能明白這些概念,就不用在過後數年歡迎包括陳子鈞、梁振英等人到內地講授土地、法律及其他專業知識。
雖然麥理浩就此打道回府,但他卻依然樂觀地以為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終會令北京採取合作態度,而倫敦也依然有信心能依靠與滿清簽訂的條約來延續管治香港。雖然鍾士元的回憶錄強調麥理浩在事過境遷後,曾向他述及訪京期間鄧小平對收回香港有強硬態度,但這版本並不符合麥理浩後來採取的行動,而且麥理浩有不向兩局議員透露政治敏感信息的守密習慣,故不能排除麥理浩沒有向鍾士元和盤托出事實。
1979年11月,麥理浩再與王匡接觸,表明香港樂意貢獻中國現代化發展,具體措施包括在港規劃專供中國航運業使用的貨運設施,麥理浩席間藉機再提及地契問題。麥理浩從這個對話中接收到的信息是,英方宜再多等一會,等到中國(尤其是廣東)的政治和經濟更穩定才說,而在中港雙邊各有多些投資對此會有幫助。麥理浩問王匡其口中的投資是否包括房地產,王匡答說包括房地產,以及包括新界和香港。麥理浩希望保密這對話,不要讓兩局議員知道。隨後12月,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習仲勳(即習近平父親)訪港,當時港督政治顧問衛奕信(即後來的港督)向倫敦報告時指,習仲勛論及地契問題時,與王匡思路一致。中國研究文獻指出,中國內部政治情勢複雜,地方官員的說話不一定能代表上級的想法,尤其在經濟開放初期地方官員拼盡方法要爭取表現的時候。然而,麥理浩看似接受了這些是中方的信息,令他在1980年初接到在投資比例上以華潤為首的財團提出的天水圍新市鎮發展計劃時,誤以為這是中方刻意的動作,故他積極配合以望實現其政治任務。
中英試探間 華資得手業權
70年代後期,正當英方在試探中方就地契問題的取態之際,香港的華資地產商亦想試探雙方的取態。前述的土地供應特別委員會1977年發表報告,在新界物色了11個適合發展的地區;其中表明政府已在元朗地區的流浮山鳳降村進行規劃研究,以作為元朗新市鎮的一部分,這意味政府可能已計劃在該處投資基建設施。李嘉誠的長江實業似乎也從中接收了有利信息,看中鄰近地區的發展潛力,自1978年起開始收購不在該報告考慮之列的天水圍。天水圍當時仍是濕地,並未完全是可供發展的土地,但有數項吸引長實的有利條件:地勢平坦,鄰近政府擬開發的地區,並非原居民土地,故不受祖堂地轉讓發展或傳統權益的限制,加上逾500公頃的地權由單一承租人趙氏家族的聯德公司持有,而非散碎的業權分佈。78年的長實年報刊載集團規劃在天水圍進行住宅、商業及工業的發展。長實和當時已由華資主導的會德豐在78年各自透過收購聯德公司股份取得天水圍土地的業權,長實當時取得逾半股份,會德豐亦購入少量,胡應濱創立的大寶地產亦有參與其中。
這些華商在取得天水圍多數業權後,在1979年邀請中國共產黨30年代在港創立的國企華潤集團共組巍城公司(Mightycity),華潤是大股東,佔51%股權,公司其後歸屬中國外貿部;早前華商擁有的聯德股份亦轉至巍城名下。因香港實行土地批租制度,天水圍土地在法律上涉及港英政府與聯德之間的業主租客關係,但因聯德公司的組成改變,天水圍土地實際上涉及了港英政府與中資企業之間的業主租客關係。
巍城創立後,胡應濱出面在79年底向新界政務司鍾逸傑摸底,又透過傳媒向公眾透露發展計劃,提議發展一個人口達30萬的新市鎮,其後在80年初正式請求港英政府批准發展計劃,與政府舉行過多次會面。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華潤是巍城的大股東,但從未出面交涉,當時巍城負責與港英政府交涉的是以胡應濱為代表的華商。
當時港英政府的考慮之一,是香港的公共財政與日益加重的基建開支壓力,因政府已拍板興建將軍澳和馬鞍山等新市鎮,同時密鑼緊鼓地規劃大嶼山的新機場,故政府預計到80年代中期,公共財政面臨重大壓力,而天水圍發展申請牽涉的基建配套無疑將加重這方面的壓力。不過,麥理浩這時已有想法,他對中資財團參與其中深感興趣,他或認為這與早前從其他中方官員接收到的政治信息有關,故視配合巍城為實現其政治任務的機會。麥理浩反過來問巍城打算怎樣應對地契問題,因按發展計劃由落成至97年期間只有大約10年時間賣樓。巍城表明還未準備好答案,但麥理浩政府認為財團未有答案,便不影響政府考慮批出發展許可,而且私人發展商的投資亦有助解決土地供應不足的問題。港督會同行政局在5月決定開展配合巍城的前期規劃研究,以盡快決定批准天水圍發展與否。
與此同時,儘管巍城至1980年透過收購聯德公司取得天水圍土地93%業權,但尚餘7%業權不知所終,故向最高法院申請公開拍賣,以取得全部業權。同年9月21日,最高法院下令仲量行舉行拍賣,由梁振英主持,華潤總經理俞敦華、李嘉誠和胡應濱出席。拍賣過程由出價至結束僅半分鐘,梁振英叫出底價港幣6億元後,只有俞敦華舉手,梁振英再次叫出底價後準備即將結束拍賣時,俞敦華因不熟悉拍賣程序竟想再舉手出價,被鄰座的李嘉誠出手制止,梁振英第3次叫出底價並落槌,天水圍地皮自此全歸巍城,後者亦因而成為天水圍的唯一承租者。
這一連串事件引起了倫敦的注意,麥理浩的政治顧問衛奕信向倫敦報告時形容此拍賣只是一個法律技術的過程,但該財團確實是一個強大的集團。衛奕信指出,天水圍是新界裏最大片由單一承租者擁有業權的可開發土地,港英政府對華潤參與其中的背後原因知之甚少;然而,作為一位中國通,衛奕信亦強調,他掌握的證據傾向表明華潤純粹想賺錢,華潤甚至可能沒有考慮過這有什麼政治含意。
衛奕信的初步分析其後得到證實,麥理浩亦顯然對自己的策略過分樂觀,中國也根本未深入計劃怎樣處理97問題,而中英雙方都可說是被華資發展商擺了一道。
胡應濱是巍城和政府之間的唯一聯繫人,他自稱代表華潤和其他股東來與政府交涉。
胡應濱在1980年中向政府提出了兩個建議:首先,巍城向政府支付改劃天水圍土地涉及的補地價金額攤開20年繳付,這意味繳款期將超越97年;其次,不要在土地契約裏寫上到期日的條款。麥理浩和衛奕信覺得這兩個建議很「有趣」(interesting),是他們的意料之外,衛奕信隨即向倫敦匯報,要求倫敦研判這些建議的含意。不過,雖然胡應濱自稱代表華潤,衛奕信亦向倫敦表明不能完全相信他能代表華潤作決定,更重要的是,衛奕信也無從查證華潤是否代表更高的權威(即北京領導人)。倫敦表明,補地價及更改土地用途之事由港英政府自行決定,但地契問題必須與倫敦磋商。時任外交部亞洲及遠東事務副次官尤德(即後來的港督)則再次提醒,因82年是處理地契問題的關鍵年份,麥理浩應該用諸如天水圍等具體個案來建立一個能讓地契超越97年的安排。
在這段時間,正值1979年深圳經濟特區成立,80年有些香港華商突然提議在中國境內興建香港的新機場,儘管當時港英政府內部已決定新機場選址在大嶼山,但麥理浩又以為這是北京的信息,在9月向倫敦匯報;倫敦認為,似乎中國有意推行某種透過工業發展和「華潤擁有的天水圍新市鎮」等項目來與香港實現經濟共生的政策,要求麥理浩試圖與中央聯絡之前,必須先與之討論。倫敦又在10月要求衛奕信準備一份涉及香港中資的項目清單,嘗試從投資分布模式一窺北京的想法,可是衛奕信花了5個月才在81年3月完成並交去倫敦,因港英政府發現很難追蹤中資在香港的投資活動,中資透過多間公司進行各種買賣,他們只能透過讀報紙來判斷哪些經濟活動與中資有關,最後列出的清單完全看不出任何具政治含意的投資。這裏還有一段小插曲,由於英國外相卡靈頓計劃於81年3月訪問北京,麥理浩在4個月前認為那是與北京直接討論天水圍地契問題的良機,故向外交部表明行政局將在那之前完成審批天水圍發展申請。
然而,在這清單完成和外相訪華之前,麥理浩和倫敦在1981年1月獲悉一個驚人消息,發現一年多以來的紙上談兵都是想得太多。
超越97期限 中英經濟共生?
在1979年麥理浩訪京後,倫敦未曾直接與北京領導人就地契問題交涉,麥理浩政府也未曾就天水圍計劃接觸過華潤。在中英關係裏號稱「信鴿」的香港油蔴地小輪有限公司總經理劉定中與廖承志素有交情,他80年12月到北京一遊,出發前未有與麥理浩溝通過,只是與廖承志閒談間提起香港華潤公司發展天水圍一事。廖承志感到錯愕和煩擾,因為華潤從未將投資決定知會北京,他請劉定中向麥理浩傳話,希望他們不要因此批出超越97年的地契。劉定中回港後馬上通知麥理浩,衛奕信隨即在81年1月約見新華社副社長李菊生,一探究竟。這是港英政府首次就天水圍發展與中方官員接觸。李菊生明言,華潤根本沒有權力要求批予特殊地契,也未曾作出過這樣的要求。就是這句話,打破了英方一年多以來打算透過天水圍發展來處理香港前途問題的如意算盤。英國外交部官員在衛奕信就此會面提交的報告一角,手寫了一句評語:「這是令人失望的(this is discouraging)」。
或更令英方感驚訝的,是李菊生對華潤的參與和角色的解釋。華潤決定投資發展天水圍,因為他們發現與華資合作的話,開發天水圍的成本比投資其他地區便宜。李菊生亦澄清了華潤的雙重角色,一方面它是中國國企,但它也是香港的公司,故會遵守香港法規。李菊生指出,雖然中國不承認不平等條約,但這些條約是當時香港的現實,既然華潤無異於一般香港的公司,其運作也理所當然會尊重和遵守不平等條約下的法律框架。李菊生又提到,天水圍只是小問題,港英政府按正常做法處理便可,而當時未到討論大問題的時機,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嘗試以小問題來解決大問題。更有趣的是,李菊生在席間批評有第三者歪曲華潤角色,似乎意指自稱為華潤代表的一眾華資。諷刺地,胡應濱隨即跑去北京,但廖承志拒絕接見,只派秘書接見並送客。衛奕信認為胡應濱對中方的反應有過分樂觀的解讀,英國外交部內部討論更形容那些自詡中間人的華資的行動,反映了華資一廂情願和豐富的想像力。
魯平在回憶錄中,也說北京領導人對華潤參與其中一事感憤怒,「把華潤公司批了一頓」,因基於立場問題,再便宜的土地也不能要。據華潤公司的內部檔案,華潤副總經理姬江會在1980年12月下旬才初次向北京報告他們投資了天水圍,受到幾名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質疑。也許出於這個原因,華潤在81年1月主動約見港英政府,強調天水圍只是一個投資項目,從沒考慮過地契問題,又澄清他們希望按照政府的既定政策來開發天水圍。
其實說得再白一點,當時中國的私有產權概念未成熟,亦未有房地產市場,北京根本不甚了解香港的地契問題到底是什麼問題,為何英方如此着急。但這些與英方的接觸,亦讓北京內部開始思考怎樣處理香港問題。在香港的麥理浩則繼續樂觀相信,只要香港能發展成為現代城市,同時繼續帶給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好處,便可令中國願意在97後維持現狀,故此他繼續發展基建,也渴望與巍城合作開發天水圍。可是這對公共財政制度造成的壓力,催生出港英政府版本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基建圍城系列三之一,下周續)
本系列因篇幅所限只能扼要地分析考證過的事實,已發表的兩篇學術論文載有參考資料的詳細列表,還望讀者見諒。
延伸閱讀:
Yip, M. (2020). New town planning as diplomatic planning: Scalar politics, British–Chinese relations, and Hong Kong.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Yip, M. (2020). Hong Kong as a property jurisdic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