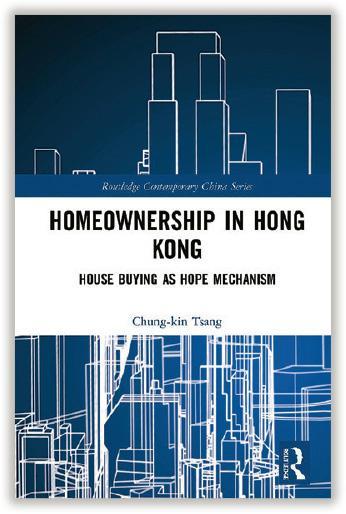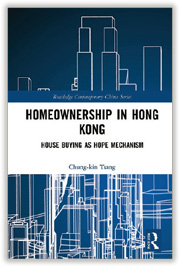【明報專訊】這個城市的怪象,總是源源送上。地產商想出一條絕世好橋,抽樓谷針,每日報名打針者立即多成倍,有人話,響應愈熱烈,愈顯得香港人悲哀,反映的是買樓夢遙不可及。
曾仲堅剛出版成書的博士研究:Home Ownership in Hong Kong: House Buying as Hope Mechanism,說香港人的買樓故事,他說表面研究買樓文化,其實研究希望才是主菜。內地興起「躺平說」,不買樓,不結婚生仔,維持低欲望生活;傳到香港,不少人都有幾分共鳴,問這學者怎麼看?他笑回,「我都想躺平」。
買樓的希望機制,他以一個畫面形容,在騾仔跟前綁一根蘿蔔,牠一直追一直追,好想吃好想吃,同時有人趕牠走,前面引、後面逼,騾仔於是前行。「社會運作上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機制,才可推動人行,如果個個都躺平唔行,社會經濟冇得發展,而以政府的角度就是關心經濟發展,會想如何推動人做事,或聽政府的方向去做。以前是用恐懼統治,公開示眾、懲罰,讓所有人都驚而去做;但到現代社會就有新的方向,階級可以流動,每個人覺得有機會可以向上,便推動人更努力工作。」
躺平的相反,似乎是郁,點令人郁,資本主義世界有「秘技」,「西方世界二次大戰後經濟發展,在1970、80年代停滯,他們認為只靠希望是不夠,歐美政府出現bureaucracy(科層制),很多人進入科層制被視為不思進取、懶、唔郁,於是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在不同的制度增加競爭元素,引入市場式的競爭,令人們會工作」。希望以外又引入另一種恐懼,「令你驚不工作會被炒,會在競爭中失敗,就如攪動水池來令裏面的魚郁」。
買樓「真理」 70、80年代成形
阿媽常跟他說,哎呀最衰當年沙士冇買到淘大,又羨慕隔籬屋師奶幾層樓揸手,追溯香港買樓故事,他發現買樓就是「真理」的想法不是自古以來自有永有。「1950、60年代人們覺得香港好多機會,遍地黃金,有可透過自身努力和聰明向上流動的希望」,他爬梳各年代的政策、紀錄片,甚至文學作品等資料,分析這個想法的背景來自難民經驗及當時政府提供福利不多,不過直至1970年代早期之前,買樓並不是人人追求的蘿蔔,直至中產生活方式開始出現,私人屋苑發展;至1980年代中,公屋、居屋、私樓市場的置業階梯鋪設成形,買樓逐漸成為一種人人信奉的「真理」。
希望是怎麼一回事?曾仲堅引魯迅:「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幾咁勵志?但他說這句話延續下去,「那條路束縛了人的方向,個個覺得安全、穩陣,就好似陳奕迅《任我行》說的,明明可以雨傘外行、赤地上行,表面上有無限選擇,但大家仍會選行那條路」。
期望危機 樓價可大跌
結果呢,這條買樓路大排長龍,等了又等,但排隊的人仍覺得終有一日會等到,等咩?他從訪問知道,大家在等另一個危機,像沙士那樣會令樓價大跌的機會。受訪者認為買樓如儲蓄穩陣,甚至當作是解決人生困局的魔法。「買樓在1990年代象徵着希望,買到樓就做到中產,有好的生活;到2000年之後,政治、社會、文化環境停滯,人們在無乜希望的環境之下,以買樓作為寄託,視為拯救個人生活的方式。」
在金融化的社會,政府解決社會問題也用金融化的方法。「政府提供社會福利不是給你公屋、綜援,而是畀個機會你買樓,因此有公屋的自置計劃,各式各樣的置業階梯。解決香港人的貧窮問題,就是透過鼓勵人們購買資產,當資產升值便可解決問題。又如早前政府援助失業人士,就想到借貸。」
希望如何維持社會秩序?澳洲人類學家Ghassan Hage用巴士站等車的比喻去理解。「當排隊排很久,條隊永遠唔郁,你會如何反應?大家會竊竊私語,互相溝通,然後開始有人發起行動,致電巴士公司投訴或研究其他出路,這是馬克思所說的class in itself,自成的階級,簡單來說就是大家形成一個團體去爭取一些東西。而Ghassan Hage的研究是指澳洲似乎沒有這回事,每個人變成零碎個體,覺得乖乖地忍耐才是文明人,隨便投訴、發聲的是野人。」這個故事在香港,就是買樓的故事,「雨傘運動之後至2018年,大家都在等下一個浪,覺得集體行動未必有用,於是用個人行動去處理『將來唔知點好』的方式,就是透過買樓,而其間對現况停滯的不滿仍不斷累積,在2019年爆發」。
後來,曾仲堅的博士論文完成了,香港人的買樓故事未完,真的等來了下一個浪,一場社會運動、一條新的法律、一場疫症,一波又一波,可是樓價大跌的預想沒有成真。
買樓夢碎 希望轉移炒股移民
「現在連這個希望都沒有了,關於希望的話題已經完結。」他說:「最後我是覺得泄氣,不知大家是否都有這個感覺?我感覺是身邊的人不再講買樓,轉而講炒美股、移民,往別的事情上尋找希望。」
回想起來,將希望寄託在下一個危機,盼樓價跌而得救,豈不戇居?他在論文裏也寫了自己的經歷。現在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的曾仲堅,在2012年至2018年間,是游走各間大學教書的漂流講師,那段經歷就像登台,「做兼職講師時就是上堂跟大家說,各位鄉親父老叔伯兄弟,今日小弟初到貴境,同大家唱一支曲,就準備一支曲周圍去唱」。沉靜的他說話自帶親切平民腔,沒很重的學者講解tone。「那4、5年的經驗也令我覺得好不安、不穩定,雖沒在學生面前表達出來,但感覺渾渾噩噩。」他當時租住的私人屋邨盛傳將成為地產巨頭的重建計劃一部分,收入又不符住公屋資格,與家人面對流離失所的威脅,唯有想像讀完博士做個中產,儲更多錢。
聽他說寫論文的尾聲,可謂在玩命。承受着論文不知能否通過的壓力,最後48小時,怕熱食招眼瞓,他買幾個蘋果充飢,奮力修改最後版本,「看着窗邊日轉夜,夜轉日,好似卡通片畫面咁」。出關第一餐,還得小心慢慢吃,免得腸胃受不住。
不過最後論文順利通過,他得到人工更高的工作,還是負擔不起在香港買樓,而如今,樓價跌的希望也幻滅了,世界沒有最差只有更差。「𠵱家真係好灰喎。」
他的興趣在流行文化,也會在劇集裏睇樓,「《壹號皇庭》的陳秀雯住跑馬地比雅道,2003年時比雅道樓價低到呢……我當然買不起啦,但有個幻想在裏面嘛」。為2003年沒買淘大可惜,他不覺得戇居,反而想了解對買樓的未來想像如何影響這個社會裏的人,「關於文化或社會的研究,很多講過去的輝煌故事,但決定我們這一刻如何生活的,也有對未來的想像,現况會被想像束縛,如果我們明天就死,會做的事就很不一樣,而這些想像會塑造我們所行的路」。
希望與恐懼都未能推動 於是躺平
他把希望放在active、passive hope的框架去看,「兩者之分是主動爭取還是被動接收,被動是社會上設定很多目標,如買層樓、生仔、考科舉、考公開試,都是外在的,讓你覺得得到的話就會有好的生活,通常得到又覺得空虛,不是你預想的。主動的希望可以是如學一種樂器,想像將來彈得更高超,會享受其中」。買樓是哪一種?「在1970至90年代是兩種扣在一起。你會覺得買到樓是自己有進步的一個物質象徵,但到2000年之後就是一個追極都追不到的夢,passive多過active。」
買樓的Passive hope是否無用?「想像不是虛無的,是有真實的效果,令你keep moving,keep motivated。欲望的客體不是絕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行落去,唔好停,這不等於要回應資本主義的訴求。」在他的研究提及,受訪者想像樓價大瀉,卻選擇性地忽視如果危機出現,亦會伴隨失業等問題,日子其實都不會好過,「不過我不覺得這種selective narrative(選擇性的說法)戇居,想像有各種功能,可以是維持社會現狀,用左翼角度看這是壞事,但還有另一個好處,會令人keep住做嘢,不會死氣沉沉,不會被打敗」。
向上流的路堵住了,買樓講來都嘥氣,在一個社會生活看不到希望,於是躺平。「每次不斷做各種事,結果都徒勞無功,有一刻覺得都無希望,不如就算啦,與其繼續被剝削,不如我咩都唔好做,其實是希望破滅,在這機制內不論希望與恐懼都沒辦法引人向前行,咪躺平囉。那當然是對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反抗,你叫我做嘢咩,我唔去做,叫我去讀書我唔讀,每一日過最低欲望的生活。」
在他眼中,其實躺平不是真的躺着不動,始終有郁,而只要有郁,「郁這件事本身是有它的意義,可能從中發掘到些什麼,逐少逐少行到自己的路」。在香港,除了炒股、移民,大家興致勃勃地討論的,還有MIRROR、ERROR,「大家咁集中睇他們,有時不是看表演本身,是看當中還有向前行的可能,繼續找方向的可能」。
令人存活下去的微小能量
「買到樓」的現實與想像距離愈來愈遠,在今天甚至遠到已經割裂,但在變得很壞的社會裏,「諗吓都開心」,可以提供一種讓人存活下去的微小能量,「黃子華在《末世財神》都有講,每次買六合彩,返到屋企就會開始幻想中了要做什麼,會買豪宅,會追番個女仔。第二日當然冇中,又要返工」。打針抽樓的怪象,在根本買不到樓的情景下,想像一下自己就是那個幸運兒,雖然不會有樓,但那刻擁有的滿足感確也存在過。
抽樓打針狂熱突顯香港人好悲哀?「我沒想過要這樣高高在上地點評,我也有普通人的心態,當大環境很差,我無法批判普通人追求自己的快樂,鍾意ERROR咪鍾意囉,鍾意幻想買樓也可以,小市民有時好卑微,如每日都要湊仔,又或工作每日回家都很累,真係唔想日日睇大道理,想睇娛樂,如果總是篤爆,要說低俗或愚蠢,為乜呢?」
這份希望是好是壞?他不去斷言,那可以成為一種機制,也不過為存活(survival),「社會機制上有希望引你郁,恐懼逼你郁,我們知道這份虛假,仍可在每一步、每一個行動中找到自己的意義,將那件事變成是自己的,就像被人用到爛的西西弗斯寓言,將推石頭轉化做屬於你自己的事,而不是別人強加的」。
也許阿Q,但反而因他對人性沒太苛求的視角,聽到三姑六婆煩氣說「梗係要買樓啦」,竟選擇研究去揭開這些觀念背後不是老生常談,而是從社會、經濟、政治背景演化出的香港買樓文化。「說他們愚民呀、被騙呀很容易,但好肯定大家不是完全被騙,儘管知道是虛幻,但產生的開心可令你survive,既然社會現實暫時改變不到,唯有在自己的空間過得好啲。」
「好難㗎」,他搖搖頭,既說自身也說香港人,悲觀地積極去活,將感受進步的希望轉移去做瑜伽、打機、洗碗抹地乜都好,得閒無聊幻想自己住千呎豪宅都好,「survive到已好難,survive到,心裏面尚有一點火,咪就係咁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