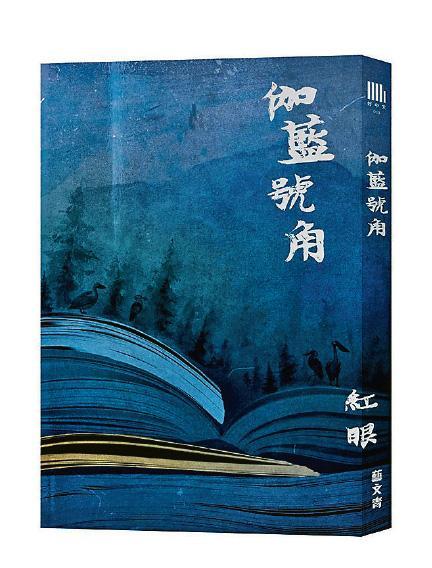【明報專訊】時代人生潮起潮落,世事倏忽變化,人在其中或不得不抓緊什麼,如作家紅眼所說,寫小說於他,恍如船錨,是自小陪伴自己的習慣,從船上拋擲,一起一落,安定自己的心。印象中的紅眼,百足咁多爪,寫小說創作之餘,近年亦多見他在不同平台上寫影評、寫流行文化、寫電視劇集……評論文字、訪談文字、創作文字,多得追趕不上,行有餘力更身兼藝文刊物的編輯、主編,總是走在時代前端,緊貼時代。近日得知他將要出版新作《伽藍號角》,收錄短篇小說十三則,讀他介紹新作的文字,最記得裏頭他寫:「寫小說仍然是我寫作生活裏最快樂的事情。」
由十二年前初出版處女作《紙烏鴉》起,紅眼一直希望以雀鳥命名書作,十二年間也出版過一些類型小說、創作集,曾中斷此命名習慣,這次則回到原初,那少年時代對文學的想像——「十六七歲時寫小說給我好自由的感覺」,如鳥。
書集以伽藍鳥(鵜鶘,俗稱塘鵝)命名,紅眼解釋,「日本人覺得伽藍鳥有靈性,牠們會在寺外聚居,似有佛性,聽得明佛偈」;日本傳說如此有靈的鳥,在中國《詩經》當中,則帶點對現實譏諷的意味,有說體型較大的牠毋須沾濕翅膀,只要伸出脖子便能吃魚,這「似在諷刺離地的中產或官員」。雖然後來讀中文系的他嚴謹地補充,這只是「解讀之一,學術分析上存有爭議」,但無疑這說法吸引着他——「可能《詩經》唔止關於情愛?放在今日,寫情歌好似方皓玟咁都唔止關於情愛」。把伽藍鳥的隱喻,放到香港近年紛擾的大環境,使他這兩年間不斷思考,作為一個作家、作者,寫作還有什麼意義?
近年社會變化速度極快,文學如此不合時宜的藝術,如何回應時代,或是不少文學創作者正思索的事情。紅眼笑言,「寫『藍絲廢老』其實幾有趣,現實中你未必認同他,但你不認同,更需要去寫他」,寫這種故事,代入那些角色人物,於他而言更能具體地書寫一個時代。文學固然非關政治立場,不囿於、更不從屬政治,在如此世代,紅眼關心的是,如何交出一部視點獨特、而又能觀照社會現實的小說?在他成長時期的香港文學,他認為一直缺少母題,「大家在說的總是城市冷漠、孤單、無主體」,但身處此時代,「你便有了主體──一個匱乏的主體,而這匱乏的主體,就是你不能言說、永遠的一個創傷」。要如何勾勒這個主體,是紅眼認為現時更值得思考的事。
寫元朗故事
新的作品集《伽藍號角》,不乏近年的社會運動甚至是疫症等描寫,其中一篇篇幅較長的小說〈擊壤路之春〉,寫及背景設置在社運與疫情交集下,圍繞一段路上所發生的故事,當中寫到的包括粉麵店老闆、中年貨車司機、南亞裔便利店員及他土生土長的南亞朋友、炒散的獨立劇團成員、喬裝警察打劫的四人組,以及中學生等,黑色幽默的筆觸底下,更多許是居於該區近三十年的作者,長久經驗累積下來、寫來不至「心虛」的元朗。筆者在採訪當天早上才發現我們將要到的元朗小店,正位處擊壤路附近。談及這段路,紅眼想起年前採訪當時剛出版《北京零公里》的陳冠中一句讓他深刻的說話──回應紅眼「你終於為北京寫小說」的感言,陳冠中說:「對啊,終於住到一個階段覺得自己寫這個地方不會心虛了!」
平日工作雖游走本地不同地區,卻只有生活了近三十年的元朗,讓紅眼感覺寫來「不心虛」,如「在心中有個藍圖」一樣,他說,尤其元朗聚集了不同人群,「政治光譜很闊,年齡落差很大」,例如聚居其中的有「新移民、老人、南亞人、原居民、年輕人等」,這地方除了讓他感到很特別,也有深刻體會,致使他反覆書寫。除了元朗,在他心目中另一個寫來不會心虛的地方,是數年前赴台念書時居住了三年的台北小社區。他明言對這兩個地方,特別情有獨鍾。
回望首個獲獎小說,紅眼憶述當初也在書寫元朗,當時錦上路鐵路站即將興建,他便以小說〈錦上路的牛〉記載村民遭遇拆遷的不同反應。印象中紅眼寫文章很快,對潮流時尚有敏銳觸覺,且在媒體生態瞬息萬變下工作及生存,總予人向前直奔的輕快形象,但言談間卻發現他常回首過去:談十六七歲時憧憬創作的初心、首個獲文學獎的小說,再然後是,兩個經常重現的小說人物——陳天偉、高海俊。
筆下人物重現不同小說
原來自中學時代為校園電視台創作廣播劇起,這兩個人物便一直陪伴他至今。其他人物如許雅婷、何湘琪、何美芝等,讀過他小說的讀者該會留意到,他們老是輪迴般在不同位置、不同時空,以不同形態再生重現。曾任其編輯的筆者,讀小說稿時總是頭暈目眩,到某刻很想知道那些小說人物設定是否連貫,紅眼答說,「那些小說人物或有原型,但不是固定的」,他再以科學角度解說,「在量子力學的世界裏,他們有時可能是同一個人,有時可能完全不同」,看我依然糊里糊塗,他說,人物或許是作者的投射、分身、不同面向的自己、不同時段的經歷,或是別人的遭遇。後來他細思再說,關於角色設定的狀態,「可能跟現實生活有關,正如你相隔數年後再見一個人,你可能會覺得他(她)面目模糊,甚至變成另一個人」,所以有時是我們對那些角色的「一廂情願」。
這種塑造人物的想法,難免與紅眼對身分轉換的着迷,以至他個人在現實生活中游走各個場域的置換特質作對照。無論小說內外,他對被定型皆有所抗拒,就如他說「不知自己是記者、編輯、影評人,或其他什麼」,更故意讓寫小說的他,與其他身分區隔。他以一個精神分析學裏借用莫比斯環的概念,詮釋這種身分位置的轉換,「驟眼看像一前一後」的兩點,但它們其實皆在同一環上,是「一體兩面」,互為影響。
重寫舊作 與十來歲的自己對話
在新作《伽藍號角》裏,不少小說也有face-off(換臉)暗示,一些人物的臉並不固定,譬如說〈東方燈塔〉、〈造雨人〉,讀至尾段你會發現,某些角色以不同形式換臉。而原來這種設定,也可追溯至紅眼在少年時代,最初創造高海俊和陳天偉這兩個人物時,一個關於face-off的故事。以現在的說法看來,紅眼無忘初衷,常與過去的自己打照面,而這次更在一篇頗血腥暴烈的小說〈海明威的貓〉中,嘗試與十來歲的自己對話。初版在十多歲時寫,把小說擱下十多年後,這次雖說剝皮拆骨地重寫又重寫,但當年被放在抽屜底的故事,最終是這次「最花心力」創作的小說。「這十年八年,我一直在跟別人講一個故事:有個女仔呢,佢唔肯剝自己對襪,有個男仔就懷疑佢係咪有六隻腳趾……」在昏黃燈光底下,再重新聽一遍這個故事的初段時,感覺恍若它仍有魔力,隨時間再度變遷。這個紅眼中學時開始構思的故事,在走至雙倍年紀的今天,他七除八扣地改寫,放進現時的故事框架內,「感覺就像在跟十五六歲的自己對話」,小說中的兩個女主角亦已不止是兩個女主角,「也像是兩個我,許雅婷是十來歲寫的,關於初戀;何湘琪那前往台灣路上的外遇經歷,則是後來寫的」。
談到血腥和恐怖,或是類型小說的操作,自覺因理科出身,是半途出家不正統的文學作者,紅眼說,在另一角度看,「文學小說」或也是類型之一,尤其在文學比賽裏,寫何種角色、題材,牽涉什麼元素會得獎等,「其實自有它的操作運算」,在這層面上,他認為與類型小說相似。紅眼再舉例說譬如Stephen King,「大家認為他寫恐怖小說,但其實不然,他本身不喜歡寫恐怖小說,只是賣得好便一直寫下去」,也譬如是東野圭吾,他們好些作品──例如《月黑高飛》(The Shawshank Redemption)和《人魚沉睡之家》,有類型小說的情節或操作在內,但紅眼想反問的是,「是否就代表沒有文學性呢?」反而有時他認為,在類型創作上的突破,以及內裏那文學性的探挖,甚至比傳統文學作品更為深遠。
以動物作隱喻 古今皆有
回到文首伽藍鳥的隱喻,小說創作如何在當今社會現實下不離地、不置身事外,紅眼似乎在小說集裏提出了其中一種逃逸路線。《伽藍號角》一些短篇小說皆以動物為題,例如〈鼠疫〉、〈殤豬〉、〈殺雞〉等,紅眼回溯並笑說,「可能我細個被母親強迫背誦成語啦」,「啃食」整本成語字典的經驗,讓他往後能輕易羅列一串與動物相關的成語,繼而發現,原來除了《動物農莊》是部政治隱喻小說,「其實中國大部分與動物有關的四字成語,也有類似典故」,而且數量之多,「明顯是由於過去無論任何朝代,也有威權,無辦法暢所欲言時,便以動物作隱喻」。他自言自己其實「很中國、很傳統」,雖然念中文系時「無心向學」,但他特別喜歡讀《山海經》。而《山海經》裏總是有七頭八腳的妖怪,他問為何會如此?當時系內一位教授曾啟發他,「今天我們可以講狼心狗肺,但當時可能未有這詞彙,那麼你怎樣形容人很兇惡呢,可能是他有四個狗頭狼頭」。即是說,動物在那年代已是個喻體。他接着再以「黃帝大戰蚩尤」等為例,說明當時人們如何以動物或怪獸的描寫,承載對社會政治現實的批判。紅眼再說:「今日你做文學創作,其實可以重回那思維,當你無法寫某些文字時,可以問,什麼是最根本的喻體?」
進入自由褪色、言論受箝制的時代,問紅眼如何看待未來的文學出版,他比預期中更抱有希望地回應──觀乎你從哪角度去想,「從社會現實的話,一定更艱難,因為審查和政治憂慮」,客觀因素上必然是障礙重重的,但從另一角度想,他說,「你要寫得更聰明更好」,意思不止說要擺脫那紅線,而是在這時代,「反而有更多事情,更值得、更需要用小說去描繪」。以往紅眼經常思考小說的功用或價值所在,直至近一兩年他發現,「當其他領域的聲音被減弱時,小說其實是個讓子彈飛、暗渡陳倉的形式」,「當我們在想如何在小說形式上有突破時,其實小說被需要這件事,現在正正於香港發生,你用這個想法的話,現在其實是寫小說的大好年華」,即是說,現在是小說更被大眾需要的時代。
也寫影評的他,再以電影作為例子──拍主旋律的導演,「其實也有暗渡陳倉」。近年被一些人唾棄的王晶,是紅眼經常講的一個例子,「他在這個年代拍《賊王》(《追龍II:賊王》)、今年四月《金錢帝國2》(金錢帝國:追虎擒龍),講六七十年代香港貪污,有四大探長、警黑勾結」,他接着說:「竟然可以在二○二一年四月上一部關於警黑勾結、收賄,然後無法無天的香港!」所以他說,政治與創作,從來應該分割去看,「每個時代的創作也有一個轉身空間,另一種被解讀的可能性」。
採訪快要結束時,紅眼收到編輯傳來的信息追他下午交影評稿。維持一段很長時間每天交一篇(甚至更多)稿的紅眼說,工作去到某個臨界點時,「其實我很需要寫小說,它給我轉身的空間,像是尋回一種節奏的形式」。「但永遠匿埋寫小說又沉不住氣」,要寫其他文章的紅眼說,在其他流水作業式的工作之間,也在社會現狀、媒體生態與自身生活轉變速度太快之時,寫小說予他的已非少年時代的自由感,現時它更像是船錨,讓他沉澱下來,安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