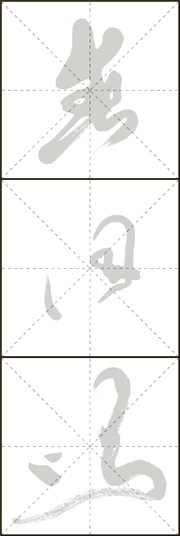【明報專訊】只要有多過一個人,就會有孤獨。聞說古希臘時代,公民投票判決某人有罪時,其中一種懲罰方法就是把那人放逐到遠離國土的邊緣地區,目的是要那人經歷難以承受的孤獨生活。這樣說來,孤獨原是一種懲罰。雖然如此,從古羅馬詩人奧維特(Ovide,43 BC-17 AD)到今時今日,孤獨一直是,而且應該還會繼續是作家創作的主題和靈感。
話說筆者月前跟朋友開讀書會,偶然看到兩篇以當代人的孤獨狀態為主題的作品,它們分別是希臘作家瑪洛.維姆沃納基(Maro Vamvounaki,1948-)的《電話獨幕劇》(One-act play for a Phone Call)和法國作家讓.卡格納爾(Jean Cagnard,1955-)的《那人、那人、那人和那人》(L'homme, l'homme, l'homme et l'homme)。筆者感興趣的是,孤獨至少已被不同的人寫了二千多年,那麼在當代的作品中,作家會用什麼方法去書寫這個歷史悠久的主題呢?而基於篇幅所限,筆者只能在此篇文章討論技巧較為特別,也較少香港讀者認識的希臘作品《電話獨幕劇》。
《電話獨幕劇》的作者瑪洛‧維姆沃納基大學時主修法律和心理學,畢業後以律師的身分工作十一年,一九七八年出版第一部文學作品。可能是因為她曾修讀心理學的關係,她的作品尤其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強調人物的心理狀態和行為動機,突出他們的恐懼和不安,以及他們潛藏於內心深處的需求等。《電話獨幕劇》的劇情是一個女人在房間打電話,滔滔不絕地說話,從她說話的內容,我們大概可猜測到電話的另一端是她的男朋友,但這個男朋友一直沒有說話。甚至她好像跟男朋友吵起架時,後者都沒有說過一句話。最後,婦人很憤怒地說:「你(按:男朋友)是個不存在的人……只在我的想像中存在過。我製造了你,我粉碎了你[……]我再明確地說:你不存在,你聽明白了嗎?三年來我對着一部壞電話講話……你不相信嗎?讓我做給你看!(拽聽筒上的連線,是一條切斷的線)這部電話多年來被切斷,同外面沒有任何聯繫。除了我,從來就不存在外部的世界,只有我存在,孤獨一人。」然後這場三年來扮講電話的獨幕劇就完結了。
以荒謬對抗荒謬
驟眼看來,《電話獨幕劇》的情節轉折位有點像《幻愛》,都是由主角揭露一切都是虛構,都是自己的幻想。不過《電話獨幕劇》的主角不是一個精神病患者,所以,她為什麼三年來都扮講電話,並在講電話的過程中虛構出一個男朋友的存在呢?而且,讀者看這個獨幕劇時(至少我是這樣的情况),一直都以為電話的另一端真的有一個人跟她聊天(雖然這個人一直都沒有說話)。因此,為什麼在另一個角色一直不說話的情况下,讀者仍一直願意相信敘事者,即這個婦人的敘述呢?換言之,敘事者透過什麼方式成功地營造出她在和男朋友講電話的印象,以致於她自己最後揭穿電話其實好多年都沒有插上線,一下子推翻了之前的敘述時,讓人覺得佈局如此巧妙。
首先說說婦人為什麼三年來扮講電話。答案很明顯,因為她的生活很沒趣,而她有很多話想說。婦人開始講電話不久,她便向不存在的男朋友投訴自己的工作:有很多訂單,她必須一一過目,工作缺乏任何創造性,而她做這份枯燥無味的工作十一年了。她在辦公室坐的位置也不甚理想,她原本的位置沒有窗戶,白天也需要開着燈工作。她搬了對着窗戶的位置後,對着的也是其他建築物的外牆。換言之,離開了一堵牆後又遇上另一堵牆。下班後,她好像也沒什麼有趣的事去做,她說「覺得時間這麼長,太空虛,還不如整天待在開燈的辦公室」。婦人描述的生活,其實就是卡繆(Albert Camus)在《薛西弗斯的神話》(The Myth of Sisyphus)中描述的現代生活:「起牀、電車、四小時辦公室或工廠的工作、吃飯、電車、四小時的工作、吃飯、睡覺;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大部分的日子一天接一天按照同樣的節奏周而復始地流逝。」面對這樣的生活,這個婦人沒有轉向哲學的世界去問為什麼,去問存在的意義。面對這種機械的生活時,她的方法很直接,就是創造一個不存在的男朋友,定時打電話跟這個伴侶聊天。她在劇本中說:「我結識了你,把你當做玩偶來利用。[……]對我自己而言,一切為了自己,因為至少我還有需要。我必須戰勝家裏這種令人作嘔的孤獨。就這樣,我製造了你。」劇情發展至差不多最後三分一時,她甚至說自己懷了孕。如果按她自己最後的說辭──即三年來都是跟一個不存在的人聊天的情况來看,這個小孩應該也是虛構的。那她為什麼又虛構一個小孩呢?其實不存在的小孩跟不存在的男朋友功用相似,就是為了拯救這個婦人的孤獨。當婦人從不存在的男朋友身上再也得不到滿足時,她就轉而虛構一個小孩,用另外一種想像的關係來拯救自己。簡單來說,婦人面對荒謬的現代生活的方法,就是以更荒謬的虛構來對抗它。
敘述可靠性
除了以荒謬對抗荒謬這點外,筆者還對此劇的敘述技巧感興趣。為什麼在另一個角色一直不說話的情况下,我仍願意相信婦人的敘述,覺得她一直是在跟男朋友聊天呢?試想想,於現實生活中,如果兩個人電話聊天,其中一方一直不說話,我們也會覺得很奇怪,覺得可能是斷了線或有其他問題。如果是在文學作品,閱讀經驗較豐富的讀者可能會猜測是作者刻意安排只有一個人物說話,所有情節的發展,以及其他人物的形象,都只靠一個人物帶出,所以只有一個人物說話。而《電話獨幕劇》精妙的地方在於,不到敘述者自己最後揭破真相的一刻,我都不知道原來男朋友是不存在的。這裏涉及的其實是敘述可靠性的問題。
美國學者W. C.布斯(Wayne C. Booth)是早期討論敘述可靠性的學者,他在《小說修辭學》一書中區分可靠敘述與不可靠敘述,他說:「當敘述者為作品的思想規範辯護或接近這一準則行動時,我把這樣的敘述者稱之為可信的,反之,我稱之為不可信的。」作品的思想規範是指隱含作者於整個文本中所建立的思想規範和價值取向,敘述者說的話要接近前者才算是可靠的敘述。布斯的說法較為複雜,也引起不少爭辯,或許以色列學者里蒙-凱南(S.Rimmon-Kenan)的說法更適合《電話獨幕劇》的討論。凱南認為「可靠的敘述者的標誌是,他對故事所做的描述評論總是被讀者視為對虛構的真實所做的權威描寫。不可靠的敘述者的標誌則與此相反,是他對故事所做的描述和/或評論使讀者有理由懷疑。」換言之,可靠敘述是敘述者透過不同的方法令讀者相信,他所作的描述符合讀者眼中的虛構的真實,而不可靠的敘述就是敘述者泄露了一些蛛絲馬迹,令讀者覺得他前言不對後語,邏輯不一致,而他又沒有很好的理由去解釋自己的邏輯不一致(有些作品會有較好的理由去解釋敘述者的前後不一致,例如敘述者是小孩或一個智力障礙的人)。這個情况就跟我們平時向情人逼供一樣:「你為什麼前晚十二點不回我的電話?」「我跟我阿媽去了飲早茶。」「晚上十二點」和「早茶」就讓我們有合理的理由去懷疑情人的敘述可靠性了。
回到《電話獨幕劇》中,敘述者用了什麼方式令讀者一直相信那個全程沒說話的男朋友是存在的呢?她用了至少三種方式。第一種是劇本一開始的現實主義式的場景描述。如同大部分戲劇的開場介紹一樣,此劇的場景描寫非常仔細:「這是一間老式住宅的客廳。家具陳舊,有的已經腐朽。深處設有一個酒台,覆蓋酒台的刺繡已經年久發黃。酒台角上有一個精緻細刻的獅頭[……]一個婦人緩步走入室內。」細緻的場景描寫令讀者很快地在腦海中勾勒出一個與他們生活對應的場景,而場景描述愈仔細,愈與讀者於現實生活中看到的場景相似時,讀者就愈願意相信於現實生活中或許也有這麼一個人生活在如此的場景中──即使這個人物是虛構的。換言之,此劇一開始細緻的場景描述,令讀者很快地就沉浸在一個獨居婦人的生活空間中。
第二種令讀者相信這個婦人的敘述的方法,是於劇本早期便塑造出婦人很喜歡說話,很快地說話的性格。例如婦人一開始講電話時問候對方(對方沒有回應),然後投訴自己的工作。按正常的聊天程序,這個時候應該是輪到對方說話了。而婦人的反應是:「還不如整天待在開燈的辦公室(按:婦人剛投訴完她的工作)……現在給我談談你的情况……你怎麼樣?今天是怎樣過的?已經做完些什麼?[……]我喜歡打聽你在做什麼?在什麼地方?過得好嗎?[……]你就是強迫我講,我也高興。(流露出抱怨)你並不詢問很多……你會說根本來不及考慮對哪些感興趣,因為我嘴太快都講了。是的,我不管有什麼事,總想痛痛快快地說出來。[……]我幾次也想不聲不響,但堅持不了多久,又開始嘮叨,而且更加喋喋不休。」從這短短的引文,我們看出婦人也不是一個完全沒有自覺的聊天者,她知道要在適當的時機讓對方說話,所以她一連六個問題拋向對方。但當然,對方是一個問題也沒有回答的。那婦人如何解釋這個情况呢?她就說自己是一個嘴太快,不管什麼事都痛痛快快先說出來的人。她也試過不聲不響,但堅持不了太久,又開始喋喋不休了。由此,我們可以暫時相信,電話另一端的人沒有回應任何問題,是因為婦人太喜歡說話了,明明自己拋了好幾個問題出來,但對方都來不及回答就被她自己霸佔着說話時間,繼續說下去。由是初步解釋了對方的沉默不語。
然而,隨着婦人一直說下去,讀者還是會升起同樣的疑惑:為什麼電話另一端的人一直不說話呢?所以就來到第三種令讀者壓下自己的疑惑、繼續相信婦人的敘述的方法。那個方法就是婦人不斷地解釋為什麼對方不作聲,為對方奇特的行為提供動機。法國文學研究者Gérard Genette於〈仿真與動機〉(Vraisemblance et motivation)一文中指出,如果我們要描述一個很出乎意料的行動,在沒有其他條件加持下,這個行動往往讓人覺得很不真實,好像是不可能的。因此,為了令這個行動變得可信,我們要令它帶有動機(motivé)。舉例來說:有一個人一直在我面前做一些奇怪的行為,但有人跟我說他可能暗戀我,那「可能暗戀我」的動機就令他所有奇怪的行為變得彷彿可以被解釋了。其實對方是否真的暗戀我不是重點,重點是,當我有了這個猜想後,對方一切看起來完全不合理的行為就會變得合理。同樣的情况發生在《電話獨幕劇》中,婦人一直解釋男朋友的反應,例如:「我知道你們男人一般不太喜歡打電話」、「希望你能開口。一言不發更使我尷尬。你的沉默使我哭笑不得,變得歇斯底里」、「你以為我沒有察覺到你有意迴避我嗎?你懶得同我說話,你以為我還不明白?」這些句子是情人吵架時常見的句子,它們嘗試解釋了為什麼對方不開口:可能是男人不喜歡講電話,或感情淡了,不想說話。與此同時,男朋友的反應彷彿也透過婦人的說話呈現出來,例如婦人說自己懷了孕那個情節:「我懷孕了。怎麼知道的?做過檢查。一個月前我就知道了。肯定無疑……什麼時候?你還需要問什麼時候?難道你忘了?[……]我從來沒有想過打胎。為什麼?因為我想要這個孩子。(苦笑)」由這個片段可見,男朋友的反應全靠婦人的說話表達出來,讓我們有個感覺,就是對方一直在給反應,不是完全沒有存在感的人。而他的存在感較弱,是因為敘述者是一個喜歡表達自己的人,男朋友是一個較沉默的人,也可能是男朋友覺得感情淡了,不太想說話。這些原因,或方法,加起來就令讀者一直懸擱着自己的不信任,繼續沉浸在婦人的敘述當中,繼續相信她。
推翻自己的一切
去到劇本最後幾行,不存在的男朋友彷彿仍然給着反應:「你說我不懂?沒有什麼需要我弄懂。我可以告訴你一切……讓你了解最糟糕的事:你根本就不存在……」然後婦人就揭破了真相,推翻自己一直以來的敘述。原來三年來,她都是對着空氣講電話,男朋友是不存在的,懷着的嬰兒也是不存在的。在文學研究來說,這種敘述者推翻自己之前的敘述之行為,我們稱之為「後設敘述」(meta-narrative),其目的是要突顯敘述的虛構性,或在寫作中以寫作行為為研究和描述的對象。但正如讀書會其中一位書友所說,《電話獨幕劇》比較好的地方在於,它不是為了後設而後設,即它不是為了炫耀文學技巧,或探討較為文學內部的寫作行為問題而用這個後設敘述的方法。敘述者(婦人)的自我推翻,正好突顯了她的孤獨。即是說,此劇的形式與它的主題高度配合。
面對這個沒趣的世界,婦人構想出「正常人」會有的關係(即伴侶和小孩),然後又揭破自己的自欺。這樣一個清醒的人,她在這個世界應該是孤獨的。她的行為也呼應了劇本的標題,「電話獨幕劇」,她一個人三年來都做着一齣講電話的獨幕劇,只有她自己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