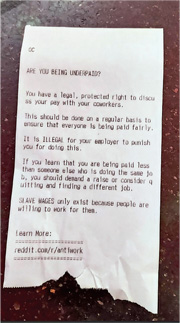【明報專訊】今年獲得金馬獎最佳導演的羅卓瑤,其新作《花果飄零》在極低成本條件製作下,將觀眾帶回到2014年之後,2019年之前的香港時空,這部還未在香港上映的電影,與近年香港和台灣電影中強調本土身分,一頭栽進本土意識裏的走向相反,顯然並不討好,並不能為現時政治環境下的觀眾提供任何情緒宣洩,但將觀眾拉後遠去回看的距離感,審視自身處境與不安是自此一家的,這會否是她得到評審團肯定的最大原因?
電影的特殊之處也因此絕非它出現在此時此刻,談及任何一場政治運動。要將《花果飄零》納入近年香港獨立電影中常常出現,非常直白地表達政治問題的處理方式去理解,確實會造成限制,羅卓瑤的局外人視野,並沒有離地到漠視近年香港社會人心的變化。
但必須指出,影片具有一定爭議,由提及廣州起義、借由音樂家談到俄國十月革命、戲中導演的哥哥在「一二.三」暴動中失蹤、電影中重要的主線也關係到雨傘運動後人與人之間關係摩擦,甚至在影片的尾聲中,暗示其中有角色參與過六四事件,多場政治運動背後受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左右,將它們簡單並排,甚至將事件片面地歸為「爭取自由」、「反對殖民控制」,把左派暴動與2014年雨傘運動劃上等號,或只視之為不同世代華人仍未忘理想追求,都富爭議。在現時政治環境下,拍虛構故事本身也可能是對當事人的一種冒犯,羅卓瑤和編劇方令正選擇的敘事方式,將這些改寫了人際網絡甚至整座城市的命運的政治運動串聯起來,將政治運動作為背景加諸角色,似乎只為令角色添加一份沉重感,背後卻沒有深究其起因以及當中人們的掙扎和選擇。前作如《遇上1967的女神》、《如夢》,羅卓瑤和方令正發展出他們的非線性敘事,借鑑德國小說家 W.G.Sebald的手法,引用他者的轉述,照片,景觀,導演自述等,突顯羅卓瑤和方令正關心的不僅是「說什麼」,更是「怎樣說」的藝術,所有生命經驗的碎片共同拼接成一份關於漂泊的處境,就像她在《秋月》和《浮生》所做的一樣。
《花果飄零》以導演第一身講述開始,展現了兩條平行發展的敘事線,一邊是導演扮演的「我」回到澳門探尋失蹤了的哥哥,導演並沒有出鏡,只親身以旁白講述,一直在追問失蹤哥哥下落,那仿若遊魂般遊走於雙城之中的鬼魂,吟唱着辛漢創作的《中國男兒》,詠嘆失去了的人事。導演不停在電影中叫着「哥哥、哥哥」卻始終得不到回應。另一邊是從英國回港的音樂系留學生Jeff在街頭遇上聲稱有陰陽眼的女生,眼看她家庭因政見不同衝突,以及他個人面對香港社會找不到出路的格格不入。
論者都提及他們2人的創作離不開漂泊這兩個字,不只是在空間意義上被政權驅逐,也有自我流放。被迫離家的人們,此前信任的一整套生存經驗:家庭、關係、教育、習慣、甚至語言,都被暴力事件,社會所剝奪與傷害,《花果飄零》中的角色,都是被主流環境驅逐出來的人們,鋼琴主角、不受重視的音樂家老師,以至戲中的導演自身都是如此。要如何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阻斷,喚醒記憶與感受,在自我與他者之間建立聯繫,羅卓瑤和方令正探索這近乎不可能的嘗試,亦為我們做出了典範,懷着耐心和洞察力,記錄着事物中糾纏蔓生情緒,懷疑與不安、轉述和回到消失了的人曾經到過的現場,並且以虛構去建構,讓他者成為我們之間自己的回憶。《花果飄零》召喚了隱身在家庭與國族歷史裏的意識,牽連出一條跨越時空的對話。不過低成本,非職業演員演出,亦令到羅卓瑤無法有最好發揮,現實與虛構交錯並不突兀,甚至由羅卓瑤口中提及她哥哥的事,非常真實,更顯得劇情部分演出生硬,讀起對白時亦略嫌造作。但這些問題並沒有限制了作品拓展的表達空間、甚至有時候可以將不利條件抽象化成優勢。
澳門和香港都是導演過去生活過的城市,如今電影人將各種自己和他人的記憶告訴觀眾,但她處身在什麼位置,是回不了家?是發現屬於自己的家已經不存在,只能擁抱已經失去了的時地人?想起電影開場不久,男主角坐在一片荒漠,大片沙漠場景與後來的城市畫面顯得格格不入,分不清地理位置,沒有歷史,沒有過去,也好像沒有未來。
電影完結時有如下一句題詞——「哀歌 那記憶中的城市、二零二零。」哀悼的不只是2014年雨傘運動後的香港,更是導演出生地澳門,那裏夾雜着她與失蹤哥哥嬉戲玩樂,聽到大哥哥們高唱的回憶,這位已長居澳洲的華人,對我們已經失去了的東西拍出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