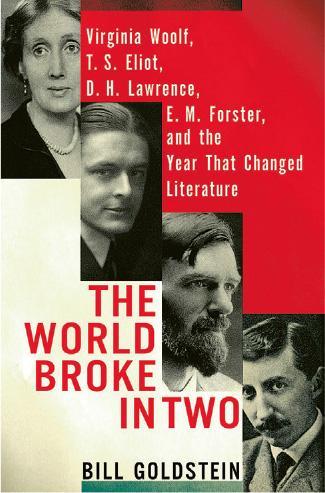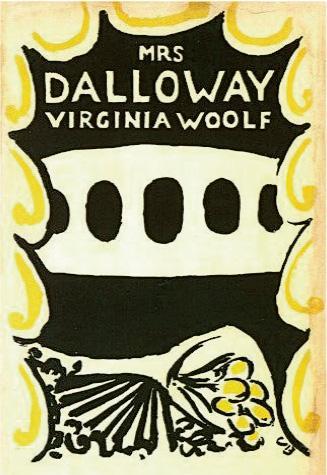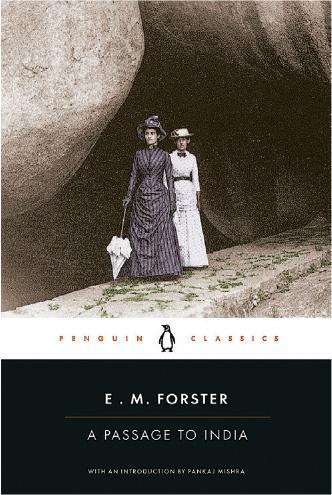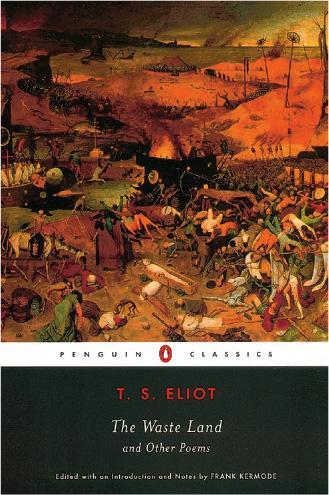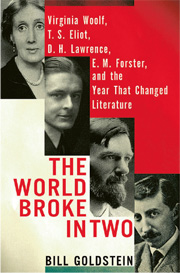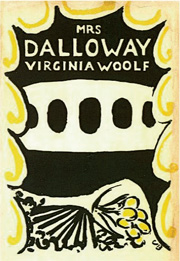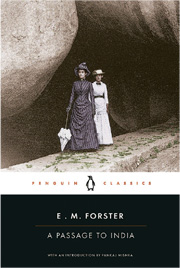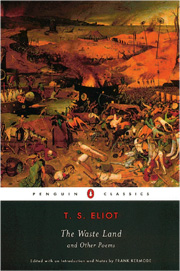【明報專訊】我們帶着沉重的步伐,走到2022年。
回望100年前的1922年,英語文壇風起雲湧,1922年2月2日,喬伊斯(James Joyce)的現代主義長篇小說《尤利西斯》(Ulysses)單行本,由巴黎的莎士比亞書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出版,面世當天正好是喬伊斯40歲生日。1922年10月15日,詩人T.S.艾略特(T. S. Eliot)名作《荒原》(The Waste Land)在《標準》(The Criterion)雜誌面世,迅即驚動文壇。這兩件文學界大事,肯定了1922年對於世界文學,是十分重要的一年。
一個事實,可以從不同角度和方向觀察。2017年,書評人比爾高士甸(Bill Goldstein)推出著作《世界一分為二:胡爾芙、艾略特、勞倫斯、福斯特,以及改變文學的一年》(The World Broke in Two: Virginia Woolf, T. S. Eliot, D. H. Lawrence, E. M. Forster and the Year That Changed Literature),書中用了4位英語文學家的生平和創作為切入點,細論1922年如何成為現代文學的分水嶺。
《世界一分為二》的前言開宗明義說:「有些年份被認為是歷史上的關鍵點——1492、1776、1865、1914、1945、1968。1922年是文學史上的分水嶺。」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並發表;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奴隸制廢除(愛爾蘭詩人葉芝W. B. Yeats在這一年出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68年是全球各地政治運動此起彼落的一年。
1922年的文學故事有許多,高士甸以胡爾芙、艾略特、勞倫斯、福斯特4位文學家為焦點,他們在這一年發揮了不一般的創作力,而高士甸的着眼點不是出版,而是寫作。他們4人在1922年年初都處於極度沮喪之中,感到不知所措。但突然之間,他們都有所改變,胡爾芙開始寫作《達洛維夫人》(Mrs. Dalloway),而福斯特就重拾舊稿,寫作《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高士甸說他們二人閱讀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第一卷,激發了他們的靈感,自1922年起一直持續。至於勞倫斯就開展長途旅程,在逗留澳洲期間,寫作帶自傳色彩的小說《袋鼠》(Kangaroo)。艾略特當然是與身處巴黎的龐德(Ezra Pound),大手筆修改《荒原》了。
高士甸翻閱大量文學歷史材料,回望4位文學家在1922年的轉折,他道出這4位文學家「創作上的掙扎和勝利,以及私人的戲劇性事件——神經衰弱、慢性疾病、極度孤獨、離群索居和抑鬱,更不用說愛情與婚姻的難關,以及法律和財務問題——背後隱藏着一個共同的幽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災難,到1922年,也就是停戰將近4年後,他們每個人都終於能夠創造性地應對了」。
我也不妨引述書內書外的相關資料,看看4位文學家如何走出個人的重重困境。
意識流與新視點:胡爾芙《達洛維夫人》
1922年,胡爾芙40歲了,與政治理論家倫納德(Leonard Woolf)結婚10年,夫婦二人創辦的賀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恰恰5周年。好事多磨,踏入新一年,胡爾芙就為感冒所折磨,臥牀不起,甚至被死亡的思緒分散了注意力。
1922年,胡爾芙動筆寫作《達洛維夫人》,1925年出版單行本。她用了新的意識流手法創作,小說的主結構是克拉麗莎.達洛維(Clarissa Dalloway)的一天,在這一天,達洛維夫人準備在家中舉行晚會,而透過達洛維夫人的意識流動,我們了解到她的過去與人生,包括拒絕了與彼得結婚。而另一方面,胡爾芙刻劃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役軍人塞普蒂默斯,他由於戰爭的創傷而有幻覺,在精神失常下自殺。
胡爾芙受了普魯斯特的影響,但走出了她自己的文學道路,在10月14日的日記中,胡爾芙寫道:「《達洛維夫人》已構思成了一本書,在這本書裏我要進行精神異常和自殺的研究,並同時通過健康者和精神病患者的眼睛來看待這一世界——類似這樣的內容。」
繼續寫下去:福斯特《印度之行》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最漫長的旅程》(The Longest Journey)、《看得見風景的房間》(A Room with a View)和《霍華德莊園》(Howards End)4部長篇小說出版後,福斯特有10多年未見新的長篇小說面世。此期間世事天翻地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福斯特是良心拒服兵役者,在埃及亞歷山大港的英國紅十字會工作。
1921年,福斯特第二次造訪印度,擔任印度德瓦斯的摩訶羅闍(Maharaja,大君)杜科吉拉奧三世(Tukojirao III)的秘書,1922年,福斯特回到英國。此時福斯特一蹶不振,難怪胡爾芙在3月12日的日記說:「我們認為他情緒低落,幾乎到了委靡衰弱的地步。我想,43歲回到韋布里奇(Weybridge),回到離車站一英里遠簡陋的家,回到愛挑剔而嚴厲的母親身邊,失去了印度王公所享受的尊敬,沒有小說並且失去了創作小說的力量——確實令人垂頭喪氣。人到中年讓人不能不感到恐懼。」
《世界一分為二》中提到兩件事情,呈現出福斯特的狀態,一是詩人沙遜(Siegfried Sassoon)請求羅倫斯(T. E. Lawrence)的允許,與福斯特分享尚未公開出版的羅倫斯自傳《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羅倫斯同意,因為他回想到自己對《霍華德莊園》的欣賞,但羅倫斯又有些懷疑:「作者不是早就死了嗎?」彷彿,福斯特過着死後的生活。
另一件事是,3月25日,福斯特寫信給胡爾芙的丈夫倫納德,要求見面:「我想和你談談我的情况。我不太願意諮詢其他人,我知道如果可以的話,你會幫助我的。……禮拜五你會在城裏嗎,如果可以,我們可以一起吃午飯嗎?」倫納德記錄了他在3月31日禮拜五的活動:「早上工作,與福斯特午餐,福斯特談論他的寫作。」倫納德給福斯特兩個建議:放棄新聞業的工作,並通讀他自己的印度散稿,繼續寫下去。這些印度散稿,後來成為了福斯特最出色的小說《印度之行》。
《印度之行》的故事是這樣的:穆爾夫人(Mrs. Moore)和阿德拉.奎斯蒂德(Adela Quested)一起來到英屬印度的城市昌德拉普爾(虛構的地方),探望擔任殖民地官員的穆爾夫人兒子朗尼(Ronny Heaslop),阿德拉要看真正的印度,也考慮要不要和朗尼結婚。她們與一位年輕的印度穆斯林醫生阿齊茲(Dr. Aziz)成為朋友,阿齊茲邀請她們一起去遊覽馬拉巴山洞(Marabar Caves)。在幻覺之中,阿德拉感覺受到阿齊茲的侮辱,阿齊茲被拘捕,由此引發了審訊,英國殖民統治者與印度人之間的矛盾白熱化。當地的公立學校校長菲爾丁(Cyril Fielding)是阿齊茲的朋友,他相信阿齊茲清白無辜,而終於認清了事實真相的阿德拉也向法官撤銷了指控,阿齊茲的冤案告終。可是,阿齊茲認為菲爾丁與自己的仇人阿德拉關係深厚,對菲爾丁產生了芥蒂,菲爾丁也回到英國。小說的最後,菲爾丁和阿齊茲難得在印度茂城同遊,他們談到政治問題,阿齊茲相信印度要脫離英國,成為獨立的國家,到那時候,他們才成為朋友。
《印度之行》在1924年出版,令福斯特獲得重要的詹士泰特布萊克紀念獎(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福斯特取得成功,走出了創作的瓶頸。60年後,英國導演大衛連(David Lean)拍成電影,這是大衛連最後的作品。
漫長旅程:勞倫斯《袋鼠》
勞倫斯一直憤世嫉俗,他更喜歡自然世界。他第五部小說《戀愛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是《虹》(The Rainbow)的續集,1920年11月,在美國先推出,同月,勞倫斯致出版人塞爾策(Thomas Seltzer)的信中說「這是我最好的一本書」。可是,當1921年6月,《戀愛中的女人》在英國上市,隨即劣評如潮,銷量也不濟。
1921年底,勞倫斯收到美寶道奇(Mabel Dodge)的信,信中邀請勞倫斯到美國新墨西哥的陶斯(Taos, New Mexico)一住。美寶道奇是個闊太太,她讀到勞倫斯的遊記《海與薩丁尼亞》(Sea and Sardinia),而想到找他到陶斯,寫一寫當地。她的提議正合勞倫斯之意,在回覆美寶道奇的信中,勞倫斯說1月或2月起行,他要離開歐洲,他要踏出下一步,而且他喜歡Taos的名稱。
美寶道奇給勞倫斯的那封書信文獻已佚失。但從勞倫斯給朋友卡斯韋爾(Donald Carswell)的信中,可略知內容:「從新墨西哥的陶斯給我們來了信。她說,假如我們願意,我們在那兒可以住上一幢家具齊備的磚砌房子,還可以得到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陶斯似乎在一座山上——海拔7000英尺——離開鐵路23英里——在那兒有一個600人的自由的印第安人部落。她告訴我們那些印第安人很有意思,他們崇拜太陽、求雨,還沒有受到現代文明的侵蝕。」
從高士甸的《世界一分為二》以至勞倫斯的書信,可以知道勞倫斯舉棋不定,他的朋友布魯斯特(Earl Brewster)邀請勞倫斯去錫蘭(斯里蘭卡)小住,那麼他要往東方去,還是往西方去呢?他更想去錫蘭尋求平靜,於是,陶斯之行變成下一步了。
由1921年聖誕節起,勞倫斯就患了流感,未能在1月隨船起航,結果2月才起行。船上的旅程愉快,他抵達錫蘭,又覺得氣候和環境不合適,6個禮拜後,勞倫斯轉到澳洲,在當地重投小說的世界,快手寫完《袋鼠》。終於,勞倫斯在9月抵達新墨西哥。他給福斯特寫信,說「我感到這地方非常陌生,但也漸漸習慣了這種陌生感」。
1922年,勞倫斯展開了漫長的旅程,不斷探索,他似乎沒有寫下十分驚人的小說作品,但也快將完成了個人尤其重要的詩集《鳥、獸、花》(Birds, Beasts and Flowers)。對他個人來說,美國之旅解決了他的窮困,因為《戀愛中的女人》在美國的銷情很好。
憂鬱的自傳:艾略特《荒原》
1888年,艾略特生於美國密蘇里州的聖路易斯,他在哈佛大學獲得學士與碩士學位後,一度在巴黎的索邦大學參加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哲學講座,其後他回到哈佛,順理成章攻讀博士學位,1914年是重要的一年,艾略特到牛津大學墨頓學院研究哲學,又與龐德首度見面。1915年,艾略特與舞蹈家維維安.海活(Vivienne Haigh-Wood)結婚,這段婚姻沒有帶來幸福快樂,但是帶來了詩,當然,就是《荒原》。
1916年,艾略特的博士論文寫好了,但他無意回到美國,口試不了了之。艾略特在勞埃德銀行(Lloyds Bank)工作,1921年10月,艾略特因為神經衰弱,向銀行請了3個月假,他途經巴黎,探望龐德,再到瑞士洛桑治療,1922年,艾略特折返巴黎,工作依舊,就是與龐德修改《荒原》。
6月23日,胡爾芙在日記中,記下艾略特朗誦《荒原》一事。胡爾芙欣賞詩作,也寫了一起聆聽的朋友瑪麗赫捷臣(Mary Hutchinson)的話:「這是艾略特的自傳,憂鬱的。」艾略特同意,他將自己的人生投入到詩中,詩中引經據典,不易理解,而同時詩中有對當時社會、精神領域、男女關係等等的看法。
艾略特將《荒原》發表在自己主編的《標準》雜誌創刊號,取得注目與成功。
高士甸的《世界一分為二》以艾略特《小吉丁》(Little Gidding)的兩行詩作結,《小吉丁》是《四首四重奏》(Four Quartets)的最後一首,寫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以時間、宗教啓示和救贖為主題。我引錄原作與張子清翻譯如下,對我們有一定意義。
For last year's words belong to last year's language
And next year's words await another vo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