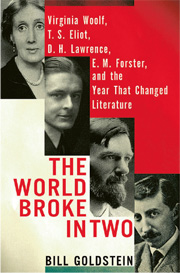【明報專訊】文化博物館正門的李小龍像,新亞書院的唐君毅像、中山紀念公園的孫中山像……這些巨匠名人的身影和精神面貌,都由雕塑家朱達誠刻鑄留存。雕像的矗立與倒下,他親歷不少。一九六五年於湖北美術學院雕塑系畢業的他本要留校任教,但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被派到山區學習改造,一年後回到校園,只見大衛像、維納斯像等「封資修」物品全在操場被砸爛,老師已被批鬥一輪,同學在喊口號,文革正拉開帷幕。活到耄耋之年,他見過、雕過許多作品,最拜服還是米高安哲羅和羅丹,「在歐洲、羅浮宮看到大師作品,感動到不得了」。時間證明雕像的精神不會過時,現在內地多間美術院校,仍倬立着維納斯、大衛像或「沉思者」。
熱愛每個親手造的像
朱達誠說,雕像不同其他藝術媒介,着重與人的互動交流,讓觀者感受其事迹和對該地方的貢獻,「難得有個公眾場合,如果造得不似,就不應白佔位置」。新亞書院的唐君毅像迎風昂首,立於行人道旁邊的草地,面朝他生平最關心的莘莘學子。眉頭和嘴角緊鎖,有風雲感會的氣派。「唐先生的弟子提供了他望向大海的相片,我便以此為依據。」銅像於二○○九年奠立,勞思光也有出席,當時學生已說將來想為勞先生造像,請朱達誠多看兩眼,並拍下數幀照片。朱達誠記憶中的勞思光溫文儒雅,於是他提議在未圓湖畔的樹蔭下設置坐像,合手翹腳,面帶微笑。本來中大已不再在校園立人像,唯獨這次破例。「兩位大師性格不同,但學生見到雕像時,都會覺得他們就在面前。自己親手造的雕像,我都有好熱愛的感情。」
每次塑像前,他會視察環境,決定銅像和底座高度,確保配合安放的地點,兩者諧協。內地早前有座接近六十米高的關公像,他說「完全離晒譜」。為慕光英文書院造的杜學魁夫婦像、英華書院的馬禮遜牧師像,他都刻劃得平易近人,讓師生倍感親切;中山紀念公園的孫中山雕像則背海面山,聳峙莊嚴。香港童軍中心大堂有座昂首闊步的童軍像,是他一九八四年來港後首個雕鑄的人像。朋友引介他與當時的童軍領袖見面:「他穿了制服和親自做童軍動作,一見就覺得幾有特色,可以做。做了他生動帶領兩個幼童軍邁進的模樣。」與作品交流的不僅是觀者,他每次離開工作室,也會跟雕像說再見;雕刻一個人物的時日久了,會不期然跟它聊天。
為不同時期的孫中山造像
朱達誠大部分作品和文獻都已捐給家鄉的湖北美術館,放在工作室的多是心頭好,如孫中山的相片和模型。其中有幅是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後回港下船的留影,位置是第一代中山紀念公園附近的三角碼頭。他向學者章開沅請教孫中山事迹時得到這張相片的複本,以此作為紀念公園雕像的原型。後來,孫中山紀念館又邀他造一個十七歲、在香港求學時期的孫中山像,「當時是清朝,這個好特別,全世界的孫中山像沒一個打長辮的」。雕像頭戴瓜皮帽,挾着線裝書和英文字典,帶出孫中山學貫中西,這細節為人擊賞。最讓朱達誠鼓舞的是,台上揭幕嘉賓讚許香港也有雕塑人才,「因為以前都是找外國人來造的」。他亦估計自己是首個為外國人雕銅像的香港人,現在遮打大廈中遮打爵士的半身像即出自他手。及後,夏威夷孫中山基金會成員到訪香港,也請他雕一個年輕孫中山像放到夏威夷的紀念公園;孫中山母校伊奧拉尼學校則請他雕了十三歲模樣的孫中山銅像,置於校園。他認為這證明了世界華人對孫中山的緬懷,「辛亥革命改變了幾千年的帝制,改朝換代的一個人,是我在香港最受感動的一個像」。
造像重現李小龍經典動作
三座年輕的孫中山像姿態有別,但都挺胸邁步,下襬揚起,寄喻他風塵僕僕,為國奔波的情狀。然而,這些都不及朱達誠為文化博物館所雕的李小龍像生動。彼時尖沙嘴已有一個李小龍像,「覺得有壓力,別人的已經擺出來了,我又要做一個經典、樣子不同的」。他花一個月把李小龍電影看一遍,經常合眼想像功夫巨星的神韻:除了尖沙嘴那種防守姿態,還應主動出擊,速戰速決。他發現許多電影中都有踢腿,就請教認識李小龍的武師和徒弟,得他們認同這的確是經典動作。但雕像表現動態向來不易,現在更只能一隻腳着地,「所有李小龍像都是兩腳站地,好穩當。我知道這難度高,應該沒人做過」。他先完成草圖和小模型,再處理1:1原大的頭部,刻劃那疾惡如仇的神態,得館方同意後,始到工場製作全身。
經他手的人像,他都由衷欣賞其成就和社會意義,「我都是懷着激情來做」。SARS時,他想為殉職醫護造像,希望將他們的容貌留下,給香港人紀念。他輾轉得到區議員幫忙,取得六位醫護的生活照,包括謝婉雯醫生的結婚照,得以參照她的側面和背面來刻鑿。完成後,他請各醫護的家人來看。有一對子女為母親的人像爭拗,他便給那兒子遞上泥,讓兒子修改,「他真的拿起泥在揑,說:『我媽咪的顴骨高啲。』我在後面看着他親手造母親的頭像,眼淚都流出來」。雕像都捐給政府,現在放於香港公園。
港缺雕塑人才 嘆年輕人無機會
朱達誠說雕像甚少搬移,李小龍像是個特例。它最初放在博物館展廳,之後場地續租,惟雕像被搬到門外,風吹雨打下已變色剝蝕,要定期修繕。「這個用玻璃纖維造,當年是為放室內的。現在連李小龍紀念館都搞不成。」他說香港不乏值得鑄像的人物,如今屆奧運的冠軍選手、光纖之父高錕,也有不少可安置雕塑的公共場所、公園、迴旋處或大堂,但當代藝術的勢頭太大,M+裏連一個寫實人像也沒有,「有的是諷刺、引人一笑或不齒的,當代藝術好多都這樣。沒有令人站在前面,看完有交流感動的。現在不強調這種作品,雖然寫實人像沒過時,而且好需要,但政府沒這個要求」。他不否定當代藝術,但問道:「你強調當代藝術、沾沾自喜時,有沒有地方放值得深思、紀念、對香港有貢獻的英雄人物呢?」
內地畢業生幫忙造中山像
現在委約他的多是私人機構,鮮見公共項目。他為今天默默無聞的年輕人抱不平,因以前尚有公開比賽,徵集大家提交的設計方案。像他在香港的第二件作品,是參加九龍公園雕塑比賽獲選的《天地之舞》。他相信即使做陶瓷或繪畫的,也有潛質設計雕塑,但現在的行規是由建築師包攬或介紹熟人來做:「因不流行做人物,講當代藝術,建築又多數直、橫線,只要來個流線型就可以。」大學課程重觀念多於寫實,沒有專門的雕塑系。他雕孫中山像時,還得在內地找美術學院的雕塑系畢業生幫忙。
人像總被捲入浪潮
銅像的象徵意義隨時代而轉變,也是人們不造人像的原因。光是去年已有民主女神像事件;台灣蔣中正銅像、孫中山銅像引起紛爭;邱吉爾、哥倫布、傑佛遜等英美歷史人物的銅像被針對甚至拆除,人像總是捲入浪潮中。朱達誠說藝術品本應永恆,政治動盪、群眾和政客的變化不應決定它的生命。「如要拆下來,可能的話,我會留起銅像的頭,另外收藏,因畢竟是藝術品,是藝術家的心血,一般來說都應尊重。」他記得俄羅斯公園堆滿了拆下來的斯大林和列寧銅像,如同垃圾,但其實雕塑家的手工精湛,殊為可惜。「被政治家左右的事,只能說是遺憾。所以雕塑家只能完成自己的責任,最後人像命運如何,不由雕塑家決定了。」
他清楚記得在香港掙到的第一筆錢是一千六百元,他用一千二百元買下「發夢都想要的相機」,只留四百元給太太。那是因為學雕塑時經常做泥塑習作,做完後就拆掉,「一個影都無,不像學繪畫的可以把畫紙收藏」。他許多泥塑作品都只有相片記錄。現在藝術家不碰人像,轉向裝置、抽象藝術、多媒體,連他自己也實驗草書書法雕塑。媒材講環保、輕盈,「不用太原始的材料,銅啊石啊」。但他還是堅持造銅像,覺得材料要與內容一樣,抵得住時代洗禮。
八十年代來港 受盡冷眼
一九八四年來香港時,他只為與家人團聚,「沒想太多,但覺得自己學雕塑多年,應該有機會」。他師承錢紹武和張祖武,後者與劉開渠、徐悲鴻一脈相傳,「他們教我的方法,都是歐洲的方法」。操普通話的他在香港受人冷眼,雖然在昔日主題公園「宋城」蠟像館謀得維修蠟像的工作,但某天蠟像的塑膠首飾不翼而飛,他又遭嫌疑、警察查問,至今說起仍悒鬱不忿。做不滿三個月,就轉到一家石膏雕塑設計公司,「總算跟雕塑有些關係」。由宋朝跳到童話世界,設計了很多巫婆、小鹿、耶穌等他笑說「古靈精怪」的玩偶,那些石膏手辦他仍留着,部分已斷裂,「因為是香港第二份工,很有紀念價值。老闆對我非常好」。他一邊上班,一邊參加雕塑比賽,也兼任雜誌《美術家》編輯。一九九六年回歸前,老闆結業移民,留下一筆獎金給他成立工作室。
淺白教學法源自下鄉經歷
來香港一、兩年後,他獲香港視覺藝術中心邀請教成人雕塑班,後來報名的學生多得要抽籤。他用速寫助學生理解雕塑,學生說沒遇過老師如此清晰講解,手把手地教他們修改作品。有年暑假,兩個台灣學生來上課,回台灣前給他寫信致謝,說台灣沒有這樣的老師,朱達誠便認定自己的教法正確。這種教法來自文革時期,他沒法教書,就在農村教農民用泥揑雕塑,把五年的大學課程簡化為短期班。他把這套淺白易明的教法帶到香港,用在香港藝術館和大學進修學院的雕塑班也奏效。
雕塑不能坐着造,人要高低走位,遠近觀察,他開始自覺體力有限。今年八十歲的他,每早九時回工作室,六時回家,星期天休息,按部就班工作,「不能迫得太緊,做不出好作品」。他的工作室有面可以移動的大鏡,這是他自己摸索的方法:「我教的學生個個都有面鏡。」他解釋人有視覺差,尤其是看立體事物。雕塑家長期定眼看着雕像,會眼睛疲勞,原以為對稱的雕像眼睛和嘴角,反映到鏡子裏就看到高低不一。人貴在自省自知:「鏡子反過來提醒我。像老師看學生作品一樣。」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