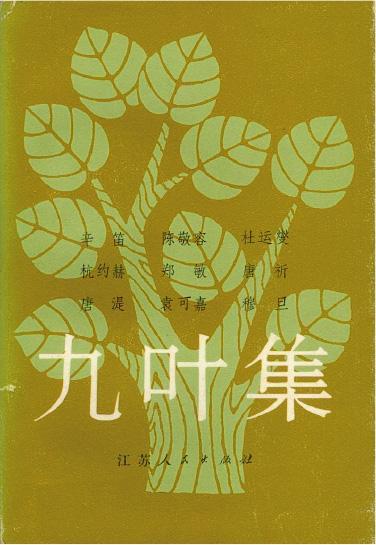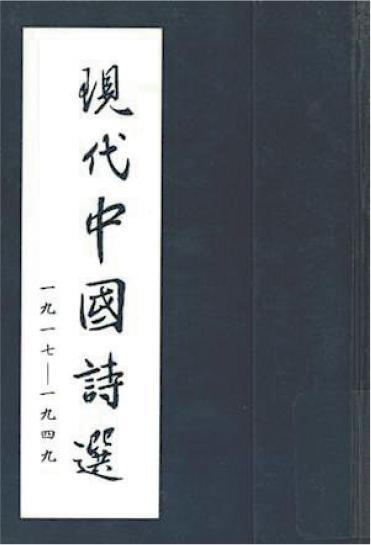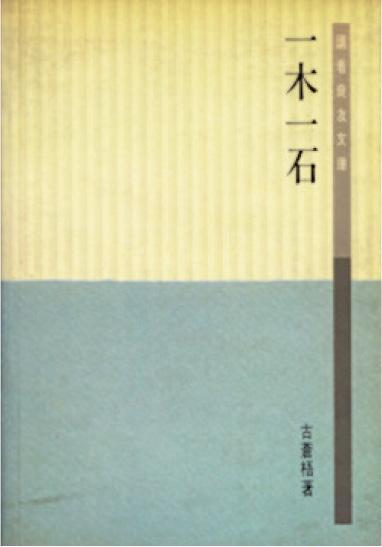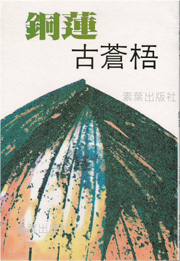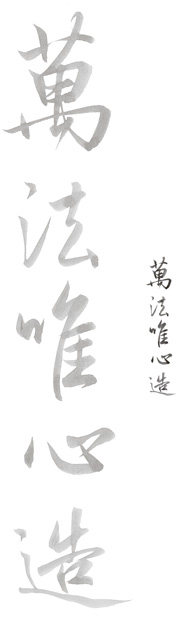【明報專訊】新一年來到,華文詩壇卻帶來兩個不幸的消息:九葉詩人鄭敏在一月三號去世,享年一百零二歲;香港詩人古蒼梧(原名古兆申)在同月十一號去世,享年七十七歲。
一九六七年,古蒼梧與友人創辦《盤古》,也開始合編《現代中國詩選》,合編者是張曼儀、黃繼持、黃俊東、古兆申、余丹、文世昌、李浩昌、吳振明,一書兩冊在一九七四年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現代中國詩選》中,收錄鄭敏詩作十首,數量不少。以下就由鄭敏的生平和早年詩作說起。
鄭敏的生平
鄭敏一九二○年生於北京,一九三九年考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後改修哲學系。在西南聯大期間,鄭敏跟隨馮至等老師學習,也開始詩歌創作。鄭敏一九四○年代的詩作發表於《大公報.星期文藝》和《中國新詩》,收於一九四九年出版的《詩集:一九四二-一九四七》。可是一九四八至一九七九年,鄭敏休止詩歌創作三十年。
鄭敏一九四八年赴美國羅德島的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留學,修讀英國文學碩士學位,論文研究鄧約翰(John Donne)的愛情詩,一九五二年完成。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五年等待回國,一九五五年回到中國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從事英國文學研究。一九六○年調往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教授英美文學。
文革後,鄭敏重新投入研究、教學和寫作。一九八一年與穆旦、王辛笛、曹辛之、唐祈、唐湜、陳敬容、杜運燮、袁可嘉合出詩集《九葉集》。一九八七年出版《美國當代詩選》。鄭敏的論文集有《英美詩歌戲劇研究》(一九八二)、《結構—解構視角:語言.文化.評論》(一九九八)、《詩歌與哲學是近鄰——結構—解構詩論》(一九九九)、《思維.文化.詩學》(二○○四)。
歌德與馮至的影響
鄭敏視馮至為恩師,在口述自傳〈跨越世紀的詩哲人生〉中,鄭敏提到在西南聯大期間,聽了馮友蘭、鄭昕、湯用彤、馮文潛、聞一多、沈從文等大師的課,其中還有馮至的關於「歌德」的課。鄭敏回憶說:「我大學三年級時,一次在德文課後,我將一本窄窄的抄有我的詩作的紙本在教室外遞上,請馮先生指教。第二天德文課後先生囑我在室外等他,片刻後先生站在微風中,衣襟飄飄,一手扶着手杖,一手將我的詩稿小冊遞還給我,用先生特有的和藹而真誠的聲音說:『這裏面有詩,可以寫下去,但這卻是一條充滿坎坷的道路。』我聽了以後,久久不能平靜,直到先生走遠了,我仍木然地站在原地,大概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我和詩歌的不解之緣。」
翻閱《現代中國詩選》或《詩集:一九四二—一九四七》,從第一首入集的詩〈晚會〉,就可見鄭敏有頗高的起點,詩人的內斂性格分明,小船的意象(人在等,船也在等)也用得自然。然後詩作轉入室內的「你」的角度,全詩的收結實在點到即止:
我不願舉手敲門,
我怕那聲音太不溫和,
有一隻回來的小船,
不擊槳,
只等海上晚風,
如若你坐在燈下,
聽見門外寧靜的呼吸,
覺得有人輕輕挨近……
扔了紙煙,
無聲推開大門,
你找見我。等在你的門邊。
《現代中國詩選》及《詩集:一九四二—一九四七》中收錄了鄭敏詩作〈讀Selige Sehnsucht後〉,從這首詩就可見鄭敏如何透過恩師馮至,接觸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詩。
Selige Sehnsucht是歌德的後期詩作〈幸運的渴望〉(Ecstatic Longing,一八一四),馮至在〈歌德的《西東合集》〉中談到這首詩,這篇論文在一九四七年寫於北平,但相關觀點和體會,馮至在多年來不斷重提,早在《十四行集》的創作期間(西南聯大期間),已有所了解。馮至說「這是詩人對於生命的最深的領悟。他用東方詩人常常提到的飛蛾撲火的圖像來比喻人是怎樣從陰暗的官感的生活裏渴望着與光明的結合」。一九八二年,馮至在〈讀歌德詩的幾點體會〉中又說歌德「用飛蛾撲火焚身比喻人嚮往光明,追求更高的生存,不免於犧牲,由此而說出『死和變』的深奧的意義」。
以下是〈幸運的渴望〉的最後兩節,由馮至翻譯:
沒有遠方你感到艱難,
你飛來了,一往情深,
飛蛾,你追求着光明,
最後,你在火焰裏殉身。
只要你還不曾有過
這個經驗:死和變!
你只是個憂鬱的旅客
在這陰暗的塵寰。
馮至的《十四行集》第十三首,相當重要,這首詩就是關於歌德:
你生長在平凡的市民的家庭,
你為過許多良家的女孩流淚,
在一代雄主的面前你也敬畏;
你八十年的歲月是那樣平靜。
好像宇宙在那兒寂寞地運行,
但是不曾有一分一秒的停息,
隨時隨處都演化出新的生機,
不管風風雨雨,或是日朗天晴。
從沉重的病中換來新的健康,
從絕望的愛裏換來新的發展,
你懂得飛蛾為什麼投向火焰,
蛇為什麼脫去舊皮才能生長;
萬物都在享用你的那句名言,
它道破一切生的意義:「死和變。」
鄭敏詩作〈讀Selige Sehnsucht後〉就是把握到馮至所傳授關於歌德「死和變」的哲學,如第一節所寫:
從同一株老樹上發出新的嫩芽,
從同一顆心靈裏湧出新的智慧,
從同一扇窗前捉到新的感情
假如死和變是至寶貴的,因為
他們繫於那不斷的「同一」。
一切皆「同一」,生命是一個力量的不斷連續。還有詩的結尾所寫的哲理,現在與過去也是連續,不可分割,不必向外在前進,而應注意生命的本質:
那讚美飛蛾的他可曾經
想過:從現在裏抽去過去
生命和他勇猛的前進都將
同於落日的潮汐,無聲的
退回海的最寂寞的深處。
一九四九年後,鄭敏等九葉詩人再沒有寬鬆的詩歌創作空間,但三四十年代中國新詩的傳統,透過馬朗、葉維廉、也斯(梁秉鈞)、古蒼梧等香港或居港有年的詩人,以創作、評論、研究、編選、重刊種種不同方法,將新詩傳統繼承和轉化了。
我第一部接觸的古蒼梧作品,應該是一九九五年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備忘錄》,窄窄的書度,加上詩文雜置,令我留下印象。後來才陸陸續續買到素葉版的《銅蓮》、三聯版的《一木一石》以及牛津版的《書想戲夢》。
關於古蒼梧的生平經歷,盧瑋鑾、熊志琴合著的《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1963-2003(古兆申訪談錄)》已有十分詳盡的回顧,我的簡單回顧集中於以下三個要點:古蒼梧的詩、詩評,以及古蒼梧在愛荷華的轉變。
古蒼梧在一九四五年生於廣東高州(茂名),六十年代中開始在《中國學生周報》和《大學生活》撰寫影評、劇評、藝評、詩評和詩作,也參與文社活動,一九六七年與友人創辦《盤古》,也開始合編《現代中國詩選》。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與戴天一起主持創建實驗學院「詩作坊」。
古蒼梧的不斷探索
平心而論,古蒼梧的詩作在質量和數量都不算十分驕人,卞之琳的評文〈蓮出於火——讀古蒼梧詩集《銅蓮》〉也是有讚有彈,但古蒼梧勝在不斷探索,帶來詩作的風格轉變。
古蒼梧的詩集《銅蓮》並沒有選錄六十年代發表的早年詩作,所以當我編輯《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五○—一九六九:新詩卷二》時,就要翻閱文學刊物,尋找詩作;終於在《中國學生周報》第八百六十九期(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四日)找到中英對照的「古蒼梧近作四首:三重憶、秋日、話後、節日」,四首中文詩俱收錄書中。而這四首詩就如林年同〈意境的繼承與空間的拓展——序古蒼梧的《銅蓮》〉所說:「吸收了王辛笛、卞之琳等詩人早期作品那種古典主義的含蓄細緻的寫法。」這種「辛笛風」或「卞之琳風」,帶有古典美,如今看來或許不算獨樹一格,但當時現代主義詩歌如日中天,古蒼梧回歸到民國以至古典主義,也算是別出心裁。
古蒼梧的詩作歷程,經歷了古典主義和批判寫實主義兩個階段,又從直白的批判走出來,我個人尤其欣賞一九八○年發表的散文詩〈冬晨〉(刊於《素葉文學》第一期,收於《銅蓮》),詩中展現出更多慎思明辨,也是相當沉鬱的作品。
詩評:現代詩走入象牙塔
古蒼梧的詩評比詩作更出色,以下選談兩篇。
一九六七年,張默、洛夫、瘂弦合編的《七十年代詩選》出版。一九六八年,古蒼梧就寫了〈請走出文字的迷宮——評《七十年代詩選》〉(刊於《盤古》第十一期,收於《一木一石》),宣告現代詩走入窮巷,詩人玩弄文字的魔術,抨擊葉維廉與洛夫的詩,並肯定三四十年代詩人何其芳、辛笛、羅大岡的詩作。古蒼梧這篇書評論點尖銳,比台灣在一九七二年開展的現代詩論戰(又稱關唐事件、唐文標事件),更早反思到港台現代主義詩歌走入文字象牙塔的問題,確有先見之明。
一九七○年,古蒼梧赴美參加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的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留美一年。一九七一年,他寄柬回香港,在《中國學生周報》第九百七十五期發表了書信形式的文章〈新詩的出路〉,古蒼梧提倡「要寫出大多數人所感所受,在表現的手法上,要誠實,不要玩文字魔術」,而且把詩恢復為表演藝術,恢復詩的音樂效果,又引入「電視詩」(television poetry)、「詩表演」(poetry performance)等新概念。
〈新詩的出路〉引來持續了幾個月的迴響,如溫健騮提倡政治上的覺醒比「詩表演」重要,但更多回應者(如關夢南、李家昇、藍笛、路雅)關注詩、表演與推廣的問題。
古蒼梧的詩評文章不少,較早期的詩評如〈阿瑟韋理和中國詩〉、〈再看意象派〉、〈文明古國中的革命詩人——彥尼斯里索斯簡介〉、〈詩可以不怨——讀西西詩作的一點感想〉、〈論鷗外鷗〉、〈大地的聲音——讀中國新一代詩作有感〉,收於《一木一石》。其中一九八四年發表的〈文明古國中的革命詩人——彥尼斯里索斯簡介〉(刊於《文藝》第十一期),介紹希臘革命詩人里索斯(Yiannis Ritsos),就打開了讀者的視野,古蒼梧更附上詩作選譯,其中〈那不可少的〉的最後兩句令人再三沉吟:「如果死亡常常是第二個來,/自由便常常是第一個。」
一九七○年,古蒼梧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是繼戴天和溫健騮之後,第三位香港代表赴美。一九七一年,古蒼梧在《中國學生周報》第九百七十六期發表的詩作〈二十五歲見雪〉、〈別〉、〈雪月吟〉,還是走新古典的路線。
從愛荷華回來了
在愛荷華,古蒼梧經歷了思想上的轉變,他參加北美學者和留學生發起的「保衛釣魚台運動」,隨着同在愛荷華大學的香港詩人溫健騮提倡「批判的寫實主義」,古蒼梧也向左轉了。
溫健騮因癌症英年早逝,終年僅三十二歲。古蒼梧與黃繼持合編《溫健騮卷》(一九八七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書中附錄了古蒼梧文章〈你去了,還有我們——悼健騮〉的節錄本,古蒼梧在文中憶述:「我們回來了,因為我們都受到了保衛釣魚台運動的衝擊,都看清楚了歷史的方向,我們都覺得,香港有許多工作在等待着我們去做。」
他們都回來了,一九七一年底從美國回港後,古蒼梧任教於西貢公立學校,繼續編輯《盤古》,又與友人創辦《文學與藝術》雙月刊、《文美月刊》、《八方文藝叢刊》等等。
到九十年代,古蒼梧擔任台北《漢聲雜誌》主編、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節目部學術總監,出版國際寫作計劃創辦人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詩集《美國孩子》(American Child),以及瑪格麗.杜哈絲(Marguerite Duras)《中國北方來的情人》(The North China Lover)的中譯本,香港回歸前一度擔任《明報月刊》總編輯。古蒼梧又大力推動崑劇,持續多年。
古蒼梧的一生不斷推動文化藝術,努力不懈,成績當然有目共睹。至於鄭敏,在詩歌創作、翻譯和評論,都有豐富成果。我未能向前輩多加請益,悔之已晚,在此謹向古蒼梧和鄭敏兩位先生深深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