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近日傳出香港電影金像獎已經完成諮詢及討論,即將設立「最佳紀錄片獎」。自從 2009年《音樂人生》成為第一部(亦是暫時為止唯一一部)入圍最佳電影獎的紀錄片後,紀錄片在金像獎的地位一度引起討論。2018年,紀錄片導演楊紫燁又向特首林鄭月娥發公開信,希望金像獎設紀錄片獎,並以更多渠道支援本地紀錄片發展。金像獎董事局主席爾冬陞早前接受《明報》專訪,談到香港金像獎正研究設「最佳紀錄片獎」。
文章談及導演張經緯去年底接到爾冬陞的電話,希望推動成立金像獎紀錄片獎,並聯絡香港紀錄片工作者為之舉行研討會並撰寫報告。爾冬陞導演在專訪中指,金像獎對紀錄片獎的研討會中,有「九成紀錄片界裏的人」都支持設獎,認為有利融資、知名度及發行。
但即使在爾冬陞的訪問中,紀錄片獎的出現都有一個重要前設:「該年上畫紀錄片達一定數目」。問題是,怎樣才算是這「一定數目」?回望近年在香港正式在商業院線上畫的紀錄長片,連同有限放映的場次在內,都寥寥可數。這似乎變成了一個「雞先蛋先」的問題:設紀錄片獎目的是刺激紀錄片的業界發展,但如果香港紀錄片未發展到有穩定作品產出,獎項的基本條件也無法達標。畢竟,沒有作品,又如何頒獎?
那麼,要在香港發展紀錄片行業,做到爾冬陞所講的「百花齊放」,令這個獎項最少可以年年頒發,可以怎樣?從外地經驗看,除了電影獎項之外,還需要各式配套,去刺激紀錄片的製作:影展、融資平台、來自政府或企業的贊助,以至紀錄片影院,不一而足。而這些配套需要建立在怎樣的基礎之上?
未曾誕生的本地紀錄片工作者屬會
倘若香港電影金像獎設紀錄片獎,參與了現有兩場研討會的約四十名紀錄片工作者,會不會在未來成為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在金像獎的「屬會」代表?紀錄片工作者聯合組成職工會或協會,統合行業權益以至共同推進紀錄片發展,也確實是香港現在闕如的。
1982年,國際紀錄片協會(IDF)在有電影行業公會傳統的美國成立。除了互助及出版之外,IDF亦積極參與奧斯卡等美國大型電影獎項的紀錄片環節,同時亦自行籌辦了IDA紀錄片獎。而在政策上,IDF還推動紀錄片工作者可以作為扣稅捐款對象,方便不同個人以及團體為紀錄片拍攝出資贊助。
至於華語地區,台灣自從解嚴以來,紀錄片發展開始多元,金馬獎的最佳紀錄片獎亦由初期的黨國獻禮片主導,開始向不同的民間、甚或政治議題發展。到千禧年初出現了幾部賣座紀錄片,振奮了當時低迷的台灣本地電影市場。至2006年,一群台灣紀錄片導演有感業界無勞工保障,於是聯署成立台灣紀錄片從業員職業工會,除了爭取勞工權益,亦為同工租借器材、提供影展補助資訊、以至成立基金拍攝特定題材紀錄片。紀工會不但組織業界,還有不少出版項目,推動紀錄片教育。
回到香港的環境,要問的是出席諮詢的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在同工當中又有多大代表性?而下一個需要解答的問題是:當「屬會」真的成事,他們需要如何配合《國安法》的實施?會不會有香港的紀錄片工作者將要因為《國安法》相關要求而沒有資格加入?當已加入屬會的會員因紀錄片製作,而被指涉嫌干犯《國安法》或其他法律,屆時「屬會」又是否可以提供相應法律支援?一切都是未知之數。
沒有紀錄片位置的「電影發展」
倘若根本不夠上畫的香港紀錄片,即使設獎亦無用武之地。要令更多紀錄片能夠上畫,最直接的方法當然是從不同渠道增加對紀錄片的投資,令創作者可以有資源拍攝紀錄片。
香港電影金像獎並未直接與本地的電影融資平台有關,其協會專門籌辦頒獎禮本身。對於香港的紀錄片工作者而言,要集資以至建立市場連結,不外以下渠道:法定機構,如電影發展局及電影發展基金、香港藝術發展局的項目資助、以至大專院校的資助;第二是由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籌辦的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HAF);以及私人贊助。
雖然不至於苦無渠道,但是仍然難稱完善。例如電影發展基金整體方針,仍然是以鼓勵工業主流的劇情片作品為主,近年推出的「首部劇情片計劃」、「劇本孵化計劃」等等,以至於直屬的「電影製作融資計劃」,都沒有將紀錄片的製作放入局方的考慮視角:申請的計劃不但要「商業上可行」,並須為擬在港放映的「劇情片或動畫片電影」。
局方對於紀錄片界別的支援,更為間接,主要在「其他電影相關計劃」中資助民間的紀錄片機構處理,而且須以「非牟利性質」。殊不知部分紀錄片發達的地區,院線放映紀錄片已經蔚然成風,自成一個可以賣座盈利的市場。明乎此,難怪楊紫燁在2018年的公開信其中一個訴求是電影發展基金將紀錄片包括在製作資助範圍。
紀錄片拍攝對於投資者而言風險甚大,製作過程難以估計長度及走向,而上畫的商業回報亦難以預計。一些世界知名的紀錄片影展都有提供相應的提案平台,讓來自五湖四海的創作者與投資者有機會互相認識、進而展開合作。而無論是提案階段、還是正在進行製作、甚至是完成製作有待發行的紀錄片,都有相應的宣傳提案平台。
例如荷蘭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IDFA)與韓國DMZ國際紀錄片影展等,都會按不同階段提供資助、並為紀錄片創作者提供向不同投資者、製作公司以至國際媒體亮相的機會:起始發展階段可以與各地監製配對;正在製作階段、後期處理的項目則可以介紹及宣傳作品,吸引投資者;而達到初剪(rough-cut)、完成階段的影片,則可向潛在發行商展示作品。
紀錄片觀影文化從何而來?
楊紫燁幾年前的公開信還提供,希望設立恆常而固定的場地播放紀錄片、並且推動紀錄片教育,想必都是為了培養香港的紀錄片觀影文化。即使是今日紀錄片發行成熟、有固定觀眾的地方,也並非一蹴而就。
例如台灣,既有由政府資助、專業策展團隊掌舵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以志工計劃、各項宣傳平台以及活動去推廣紀錄片文化;在地方上,又有以紀錄片作主題放映的場地「府中15」,舉行不同的放映活動。而到近年,更有本地串流平台Giloo問世,以世界各地影展作品以及選映的台灣紀錄片,拓展觀眾群。
另一個推動紀錄片製作及播放的推手,就是公私營電視台。在今年初戲院因為疫情關閉之前,引起討論的日本紀錄片《三島由紀夫:最後思辯》是日本TBS電視台的出品;台灣的公共電視亦有放映本地及海外紀錄片的「紀錄觀點」時段,給予民眾戲院以外的選擇。
回望香港,本地紀錄片要在院線放映相當不容易,通常僅有的亮相的機會就是在各大電影節、又或在商業院線以外更能讓製作者負擔的空間展映。如《爭氣》、《好好拍電影》一類能得到本地片商發行、繼而在旗下電影院排片上映的例子,仍然比較少。而電視台主催的本地紀錄片製作及播映,更是遙遠。
不言而喻的死結
不過,其實香港真的缺乏紀錄片作品嗎?又真的沒有紀錄片的觀眾嗎?
爾冬陞在訪問中談及電影一向有審查,又指紀錄片談政治之外,還有「社會性題材」。審查電影的確實並非金像獎、而金像獎只接受合法上映的紀錄片也非不合理。然而這些年來,有觀眾、有關注的紀錄片,有的被收回放映許可、有的根本不可能通過香港電影審查。即使有了最佳紀錄片獎,這些發出當下香港難以磨滅的呼聲的作品,但卻注定在可見將來缺席。
最近,創辦采風電影、並舉辦紀錄片影展,致力於紀錄片創作、推廣及教育的導演張虹宣布離開香港,采風與影展都「告一段落」。她在離港前的訪問說,紀錄片「要講真實的說話,但真話不是人人鍾意聽」。在今日的香港說政府不喜歡聽的說話,後果可以大得不成比例:看香港電台最近兩年的電視紀實片製作組,或被停播、或被換血,紀錄片工作者甚至還墮入新時代法網。
這樣的世道之下的「最佳紀錄片獎」,我們又可以期望看到怎樣的得獎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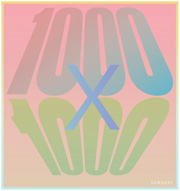
![「1000[想法]×1000[星期日]」 alt=](https://fs.mingpao.com/ldy/20220320/s00014/61ade738a12e74b27f97288f3646dc7d.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