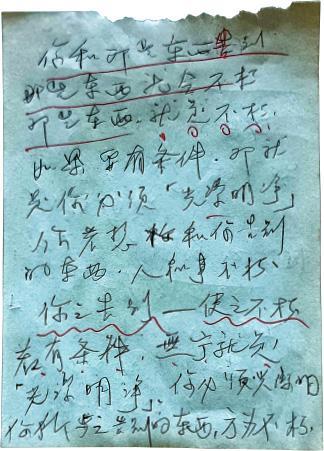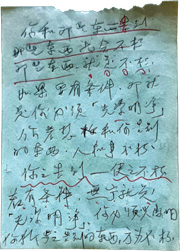【明報專訊】社會情緒低迷,不論是疫症還是經濟都重重困着己身,俗務和責任逼人成熟理智,我會勸喻,不妨看看飲江的詩作,或許會「笑出聲」,甚至得到一些啟示。飲江在一九七○年代已開始發表詩作,半百載筆耕不斷,大家都會尊稱他為「飲江叔叔」,是公認的詩界大前輩。但既沒有前輩架子,天生還自帶幽默感的飲江叔叔,寫詩隨心而富有童趣,不拘一格。
就連詩集名稱,飲江都是因為「貪玩、貪得意」而起。第一本詩集《於是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是取自詩集裏名字最長的一首詩,而第二本詩集沿襲首本詩集名,並加入其中一首詩題「搬石」,演變成《於是搬石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這次的新詩集再將前者延長,名為《於是搬石伏匿匿躲貓貓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飲江認為詩集名字無限加長的概念有趣,便開了一個玩笑:「假如詩集的題目由封面一路繞繞繞到封底,係咪好得意呢?」
十年傾一書 今年再和你打交道
飲江出版詩集,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出版的過程特別長,十年起計。他回想出版第一本詩集花了十三年時間,第二本則要十二年。這次的詩集得力於編輯羅樂敏而變得「更有效率」,由二○二一年年中構思,並將於今年七月面世,當中只花了一年多的時間,飲江更打趣道:「如果呢本書唔係樂敏來幫忙,可能要再傾耐一啲!」出版新詩集的背後故事也是非常窩心,飲江分享有一位讀者好友整合並校對好過往曾發表過的作品,對於這份恩情,飲江甚為感動,並希望透過出版新詩集回饋這班讀者。
出版詩集除了是滿足一班詩迷,飲江指更重要的是「讓書與人結緣」。他從一個故事裏深受啟悟:一位大師帶着一班小和尚到市鎮做法事,並每個和尚分派了一個銅板,可以買任何東西,旁人不免疑惑大師的舉措,大師解釋給予銅板能讓和尚們與人結緣。飲江聽後,發現原來這種簡單的購買也能結成緣分,不禁聯想:「我們好像好久都沒有坐下來黏黏貼貼、圈寫或是指認一些東西,現在可以借這個機會,跟這本書打交道。亦都想這本書帶着一樣東西,和出面的讀者、遇到的世界結緣。」手工做書成本不菲,飲江每一本詩集都有手工的成分,每本都可說是獨一無二,他指手工書的好玩之處,在於裝幀時將意念植入其中。
三本詩集,飲江都請了好友兼設計師袁先生幫忙設計,二人合作近三十載。飲江和袁先生因為住處相近,所以可以常常會面傾談詩集的設計:「我們會見面啦,傾計啦,耐唔中有時會拋低(詩集),然後十幾年先有眉目,先有成形。」飲江十分享受和袁先生討論一本詩集如何誕生,「點樣將一本詩集變成一本書,其實喺過程入面,有時候係生一個機會畀我哋傾計。」飲江補充袁先生常常拋出新奇的意念,自己需要時間消化、思考。在上一本詩集裏,袁先生在其中一頁加入「Poetry」的盲人點字,他認為一個擁有視力的人看點字時會感困惑,和讀者進入詩世界的狀態相似,有時候需要有共同的語言、世界,才能真正閱讀詩人真正的所指。羅編輯指這次的製作團隊都是十分喜歡猜謎,希望讀者可以在新書裏尋找設計師和詩人精心設計的謎題,並將之當作閱讀的樂趣。
隨意寫詩派
詩人廖偉棠曾這樣形容飲江的詩句:「有弔詭、是非邏輯的、貌似西方哲學的詭辯,但又像東方禪宗的無理頓悟」,寫飲江的評論十分難,難在他的詩句「捉唔到路」,但又耐人尋味。他創作時也常常處於一個隨機、即興的狀態,可以因為別人的一句說話、看過的一本書、剛剛經歷的遭遇、經過的一道風景而詩興大發。飲江分享自己有次向女兒說:「惜惜爸爸。」但女兒不願意,即使飲江重複問女兒,也被她三番四次拒絕。因為向女兒求吻不成,飲江便自己惜自己。或許是這個「孩趣」的畫面觸動了飲江,他因此寫了〈我有面頰〉:
我有面頰
但求一吻
我有嘴唇
但求可吻
飲江形容自己是個很隨意的人,寫詩如是,有時會被眼前的景致勾畫幾句詩,他說:「其實不一定要完成整首詩,可以寫一段、一句……」他坦言自己甚少一氣呵成地完成一首詩,詩作都需要一定時間經營,有的更會花上幾年,好像是〈行為藝術(給媚)〉一詩,飲江一九九八年從《明報》上看到一則〈丹麥美人魚尋回失頭〉的報道,覺得非常有趣,便寫下這開首兩句:「丹麥美人魚尋回失頭/又是我們郁手的時候」。他解釋:「我很少很完整地思考一件事,我會先想第一句,然後第二句,接着的句子會慢慢浮現。作品什麼時候結束,我自己也是未知的。而這是一種習慣,是一個我很想改變的習慣,不一定要改變,但也想嘗試改變。」到目前為止,飲江都認為「寫長詩」是自己的挑戰,因為寫長詩涉及創作的章法、編排,也需要對生活和學養的積累,他說:「我在某種情况裏,是比較機智的,但這種機智會否應付到長的片段,還需要其他的東西。」
天生自帶幽默感
飲江的詩常帶有一種哲理味道,以另一種角度去看世事,由此產生了一種充滿玩味的幽默感,他本人在《字花》的作者簡介更是:「顛顛蠢蠢…阿媽真係咁話。」站在作者堆裏,可說是非常「出眾」的自我介紹。說起幽默感,飲江又開了個玩笑,指自己比較「悶」,說話不好笑,在朋友間並不受歡迎,更稱讚自己「善良又腼腆」,說完這句話的飲江,不禁笑着補說一句:「隨着年紀大,愈來愈放肆。」
飲江認為自己的幽默感是源自上帝的幽默,並分享了普雷維爾的一首詩〈無題〉:「上帝/驚動了亞當和夏娃/他跟他們說/請繼續吧/別受我的阻礙/就當我不在這裏。」他閱後便覺得這首詩「好妙」,是一種神的啟示,「其中最妙的是上帝的幽默,這不是神聖所能夠形容的,是送給我們世俗人的禮物。」飲江崇尚那些自然湧現而來的幽默,認為幽默感並不是刻意經營而來,「可能寫的那個人都不覺幽默,要讀的那個人才知道。而每一個人笑的點,幽默的地方都不盡相同」。
將廣東話融入創作
初學寫詩,不少人都會將生澀難明的字詞加入。但反觀飲江的詩作,不時出現廣東話口語、俚語。他在〈聞教宗說不信主的人可以上天堂之隨街跳〉便引用了粵語「有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呀」,將常人的俗語加入詩歌,作為港人讀上去更添親切感。飲江自言本來就「做隨俗嘢」,沒有接受過正規的語文訓練,只靠平日閱讀的文字、生活的對話來創作,正正因為這個平凡的出身,飲江對創作一事十分寬容,不排拒以口語俗話入詩,漸漸走出這種不拘一格。
飲江認為廣東話是一種變動、發展中的語言,使用的人們會為它疊加、稀釋、凝結意義,甚至加入一些情緒和變調,具有特殊的生命力。飲江和身邊朋友討論起廣東話,有些人認為廣東話是讀出來時才有魅力,也有人認為是寫出來才能彰顯,他卻認為廣東話的吸引之處在於其能令其他語種更有魅力,增益其他語言。在〈感君一回顧〉一詩中:「感君一回顧/風雪夜歸人/驚情四百年/係都咬一啖/反咬又一啖/諗吓都疏肝」,飲江指「感君一回顧」及「風雪夜歸人」都是千年名句,自身的魅力不容置疑,但是這些名句的魅力被「固化」,如何活化它們才是重點。而「驚情四百年」是出自一部吸血鬼電影,為接續的「咬一啖」作背景,亦為首兩句作了補充,更添層次。
飲江的詩作裏也不乏對話,他指自己常常如人格分裂般對話,也是他的思考方式。以對話入詩可以擔當補充、提醒自己、表現分歧和質疑。其中一首詩〈鄧寄塵時間之咁都得與又係噃〉:「家嫂/咁你都信?/佢係/咁都嚟㗎/點解唔信?/咁都得?/佢哋係咁都嚟㗎/點解唔得?」飲江這首詩都是以對話完成,「因為有對話的緣故,一些消散的語言,會有人接着話題,令話題生發出有意思或沒有意思的東西」。在飲江的筆下有兩位經常出現的角色——蝦球與亞娣,他們是出自黃谷柳的長篇小說《蝦球傳》,飲江借助他們兩小無猜的關係展開對話,為自己戴上他們的面具去寫詩。
上帝不會介意開玩笑
飲江在詩裏安排上帝和他對話,原來是擔心得罪人,人會介意,他反指「上帝或者會唔開心,但一定唔會介意」,所以才能在詩歌裏和上帝開玩笑。他更指自己從前是個「無神論者」,但現在並不是,形容自己「無條件去成為信徒」,他引用母親的話:「你唔信好啦,但你唔好謗神謗鬼。」
飲江詩裏的基督宗教符號也是常被討論的,他指自己在創作上常接觸有關宗教意味的題材,但是在他的人生裏,宗教成了一個「不敢嚴肅地想像」的禁區,他擔心自己「一進去就返唔到出嚟」,對於投身一個宗教還是有所保留。雖然飲江並無信仰任何宗教,但他對於宗教亦有一番思考,不時閱讀神學的書籍。在他十二歲時參加了一個有關宗教的日營,並從中學會了一首《謝飯歌》。即使事隔多年,飲江都能大致哼出這首歌的歌詞和旋律,其中一句「同胞汗血」——詩歌大多都是感謝上帝的恩賜,這首歌刻意提及糧食由人類種植,令他思考起聖靈敘事的風格。飲江說起劉小楓所寫的《聖靈降臨的敘事》,「為什麼聖靈降臨需要敘事?原來打開《聖經》,福音有四本,即是有四個敘事,不單單是四個敘事角度,還有不同的語調、不同的啟示」。他因此亦寫下詩作〈聖靈降臨的敘事〉,表達對宗教的聯想和批判。
飲江的詩語言質樸,但蘊含對世界、情理的一番思考,複雜的俗事都可依靠通達的言語解決,精警不失幽默。新詩集其中有八個字頗令人在意,那是「光潔明淨,告別不朽」,在詩集不同地方也有出現。被問及這八個字的意義時,飲江新寫了一首詩去作回應,文末和大家一起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