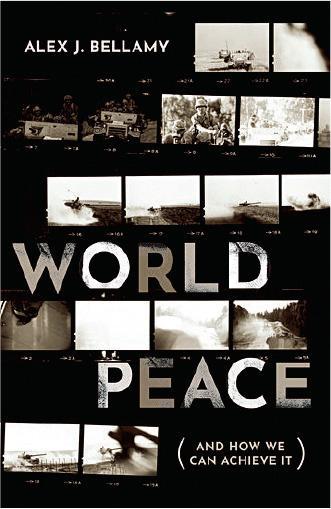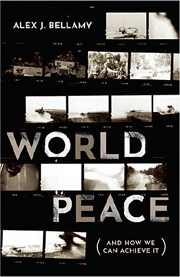【明報專訊】戰爭恐怖而常見;和平人人可欲,偏偏是冷門的學問。單就美國內戰的專著已有5萬多本,反之世界和平的專論數目不及其千分之一,故此和平與衝突研究學者貝歷覓(Alex J. Bellamy)的近作《世界和平》(World Peace)可謂難得之作,副標題亦充滿雄心:「以及如何實現」(And How We Can Achieve It)。在戰雲密佈的今日,維和的建言更顯參考的迫切。
戰爭非因人類天性?
何謂和平?對於19、20世紀之交的社運人士——例如首位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美國女性珍亞當斯(Laura Jane Addams)與和平學創始人加爾通(Johan Galtung)——和平並不單指「止戰」,更須包含社會公義,消除一切諸如貧窮、歧視及政治壓迫的結構性暴力,社會關係衝突的成因得以化解,是為「積極和平」(positive peace)。貝歷覓取法康德的永久和平論,偏向狹義詮釋:和平意味不涉直接衝突,有效預防戰事,靠非暴力手段處理紛爭,以及擁有合法的公民秩序。康德主張國際和平取決於國家性質,唯有全體國家奉行共和政體、法治綱領及互助友好心態,才有機會實現寰宇太平。貝歷覓同樣認為世界和平只能從各國一同遵守普遍律法,通過一連串「微小烏托邦」(minor utopias)逐步鋪墊而成,當中涉及價值體系之間的妥協磋商,不可能由單一世界政府自上至下施加而來。
一般以為戰爭古老而和平新興,貝歷覓證明此說不實,古代社會諸如米諾斯文明、腓尼基城邦(迦太基除外)和哈拉帕文明均曾享有千年以上的和平期。人類學及考古學研究亦表明,戰爭起源於約12,000年前,僅佔現代智人歷史不及十分之一時段,而隨着中石器時代的人類展開定居農耕,暴力死亡方才愈趨頻繁,反映戰爭源自社會模式形塑,而非人類天性。文化人類學家凱利(Raymond Case Kelly)指出,即使同屬狩獵採集部落,內部關係平等鬆散的「無分隔性社會」(unsegmented society)比起階層嚴明的定居「分隔性社會」(segmented society)更少經歷暴力,原因出於前者較少連帶責任與資源爭奪,難以觸發大規模紛爭。「戰爭是社會屬性,而非生物特徵。」霍布斯有關自然狀態充斥戰爭的學說經不起史實考證。既然戰爭與和平同屬人類的選擇,和平就有機會兌現。
戰爭不息原因與對應
書中多次強調,和平並不如想像中罕見,二戰後世界整體而言亦較以往太平:國與國的交戰大幅減少;東亞已告別戰事40年;南美自冷戰結束以來亦不再爆發重大衝突;就算內戰當道,2010年代中東北非亂局高峰期傷亡人數也較1990年代平均為低。貝歷覓將戰爭式微歸功於國際法體系、集體行動、雙互依賴性、貿易盛行以及人權崛起。即便如此,戰爭依然未見淘汰,貝歷覓歸納出三項基本原因:
(一)人類被劃分成利益與價值觀彼此衝突的不同政治組織:人類維生仰賴合作,由家庭到親族再到政治團體,發展出種種獨有的社會特徵(諸如語言、文化、歷史、道德、宗教、法律、經濟),一方面有助族群和諧壯大,另一方面各式分歧亦容易釀成族群與族群之間的不和,身分集團則擴大了紛爭的規模。
(二)戰爭有利可圖: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將戰爭定義為「政策的另類理性延伸」,不論其目的是領土、財富、榮譽、秩序建立抑或抽象價值,只要足夠多人相信箇中意義,開戰動機即告成立。從軸心國到同盟國,由殖民主義到反殖起義,不論是主動出擊還是被動還擊,盡皆相信暴力手段有利於達成其目標。
(三)戰爭具傳染性:按照「如欲和平必先備戰」邏輯,只要一國維持武裝,各國就不可能解除戒備,結果戰爭體制延續,隨時成為自我實現預言,戰爭史家基根(John Keegan)就斷言「戰爭從戰爭機制中誕生」。戰爭往往傾向升級,一國內戰會加劇鄰國陷入戰亂的風險,敘利亞戰爭即是一例,加上一旦結下仇怨就難以收手講和,牽連更廣。
針對戰爭持續的三項成因,貝歷覓提出三種對應方案,分別從國家、國際及個人層面止戰宣和:
改革現代國家:貝歷覓不諱言現代國家的暴力史,但亦指其同樣有維護和平的潛力。現代國家對外戰爭已見削減,對內降低暴力遇害率及改善生活質素,而法律制度、經濟發展和人權政策等現代體制特徵,貝氏認為都有益和平,好壞關鍵在於治理的性質。貝氏列出和平國度所需的五項條件:由國家壟斷合法暴力,防範有組織暴力發生;政府須按社會契約及法治原則向公民負責;人權得到保障,特別是平等待遇權和不受武力侵害權;確保人民享有如醫療、教育、經濟的各類基本生活保障;父權制與暴力息息相關,提倡性別平等有利加強合作,繼而孕育和平。
加大戰爭成本:戰爭代價愈大,愈能阻嚇好戰者。貝歷覓認為可從三類戰爭成本着手:直接成本方面,現代產業化戰爭所費大量人力物力之巨,足以令侵略國躊躇。2016年全球軍費(包括內部安全支出)高達10萬億美元,約佔9%世界GDP,戰亂在伊拉克、阿富汗和敘利亞摧毁近半國民經濟,就連美國「輕取」伊拉克,整場戰爭亦耗資超過3萬億美元,鮮有國家在開戰後比開戰前更強大;機會成本方面,不少國家的繁榮仰賴商貿,貝歷覓建議憑藉貿易進一步降低獲取資源的成本,促進各國人民的往來,以及開放更多競爭渠道,令和平比戰爭更有利可圖;至於政治成本,聯合國訂明邊界不可侵犯、禁止領土侵略及武裝組織分裂領土、提倡民主自治原則等,將戰爭由理所當然的國家權利列為非法,一旦發動侵略,該國的合法性將備受削弱。
扭轉利戰心理:戰爭不止出於理性計算,情緒亦是一大起因。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民族主義席捲歐洲,單在英國就有200萬人自願參軍,部分出於愛國情懷,部分則出於將戰爭浪漫化,貝歷覓故此反對有關戰爭報道的審查和限制,反而應盡可能還原戰場的殘酷,打破以身殉國的英雄情結。而要遏止惡意傳染,貝歷覓相信最好的做法就是締結友誼。國族、宗教、種族等群體身分本來互不相斥,一旦被敵意凌駕,就變成觸發衝突的火藥庫。貝歷覓呼籲建立「環球公民社會」,通過民間交流消弭排外心態,創造容納多元思維的跨國公共空間。
邁向和平的條款
書末仿效康德《永久和平論》,列出邁向和平的六項先決條款(preliminary article)、三項正式條款(definitive article)以及一項附加條款:
先決條款一:「任何國家不得違反國際法有關動用武力及衝突管理的規則。為確保法律受尊重,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不應使出否決權阻撓針對軍事侵略、種族滅絕、戰爭罪行及反人類罪的集體回應措施。」貝歷覓不斷重申,世界和平路上不缺法律,只欠實踐,當大國願意或被迫遵從國際法,國與國之間的交戰將告沒落。至於未被聯合國憲章覆蓋的內戰武裝組織,則可借助國際人權法規管其行徑,必要時安理會應予介入;假如有常任理事國牽涉衝突——例如今日俄烏戰爭——並出動否決權自保,安理會可訴諸「聯合一致共策和平」(「Uniting for Peace」)決議,經聯合國大會超過三分之二比數贊成即獲批武力介入,韓戰便是實例。
先決條款二:「所有國家均應協助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的決策得以從速完整落實。」國家應盡力支援國際維和行動及履行促進和平的義務,前者如提供聯合國財政支持及維和人員,後者則包括保障人權、發展經濟、改善治理能力等利好和平的基礎援助。
先決條款三:「任何國家或私人企業均不應向國家或非國家實體轉移有理由相信用於違反國際法的軍備。」武器貿易條約(Arms Trade Treaty)首次就國家購置及轉移軍備訂立規限,然而禁售原則並未覆蓋武裝侵略,而參與國不足以及缺乏外部監管和罰則亦急需改善。
先決條款四:「國家應與鄰國建立並維持安全共同體。」安全共同體(security community)意即區域各國確保以和平手段解決分歧,承諾既不支持域內衝突,亦不針對參與國備戰,同時具備各種正式體制以推廣合作和鞏固互信。西歐就是由世仇轉變為睦鄰的典範,東盟作為安全共同體相對鬆散,但在維繫國際關係上同樣成功。
先決條款五:「個人應享有獲普世善待的權利(universal right to hospitality)。」理念出自康德,本意指每人均有權利出入別國與他人交流。貝歷覓強調和平從來屬於國際主義,而友善原則對培育多元身分和跨國網絡至關重要。
先決條款六:「犯下種族滅絕、戰爭罪行、反人類罪或軍事侵略的個人須負刑事責任。」有罪不罰是眾多國家與集團持續違反國際法的主因之一,國際刑事法院管轄區不全、羅馬公約簽約國有限等問題仍然有待解決;鼓勵更多國家引入普遍管轄權(universal jurisdiction)以及接納侵略罪(crime of aggression)為國際刑事罪行,則已見初步成果。
正式條款一:「國家一概應為具備治理能力、負責任以及合法的主權國。」
正式條款二:「所有國家均應推廣及保障性別平等。」
正式條款三:「任何政府不應阻止個人規避戰爭。有關戰爭的自由報道、公開討論和異議以及拒服兵役的權利應受保障。」
附加條款:「個人應聯合行動並盡一切合理努力促進世界和平。」
一如國際刑事法院之所以成立,大可歸功於加拿大公民組織「世界聯邦運動」(World Federalist Movement);種族滅絕會被列入國際罪行,猶太裔波蘭律師萊姆金(Raphael Lemkin)功不可沒;如非英國法學家勞特派特(Hersch Lauterpacht)在人權問題上長年耕耘,「反人類罪」未必會成為法律概念。
過分吹捧國際法之嫌
基於任職各個國際維和組織的經驗,貝歷覓的世界和平方案傾向沿用現成機制,有過分吹捧聯合國與國際法之嫌,漸進思維缺乏批判性,論述不免流於片面。在貝歷覓筆下,國際法的發展史等於和平的進步史,完全無視早期法學家如格老秀斯(Hugo Grotius)和真提利(Alberico Gentili)如何以國際法將戰爭合理化;有批判法學家指出,貝氏視為維和里程碑的海牙公約(Hague Convention)表面上將戰爭「文明化」,同時也將戰爭視為合法乃至合乎道德的政策,規範固然有助監管暴力,但一日戰爭行為頂戴正當之名,世界和平就觸不可及。德希達曾表示,國際法對維護和平的貢獻應予肯定,不代表本身不無批判之處,畢竟國際法建基於主權、民族、邊界之類充斥問題的現代概念。貝歷覓對主權民族國家的未來似乎亦過度樂觀,事實是現代國家血腥程度比古代帝國尤甚,諸多衝突也是因民族、主權及邊界爭執而起,要求現代國家解決自身製造的麻煩,在現實中可作權宜之計,在邏輯上則是弱環。
資本體系滋生衝突難終結?
《世界和平》提倡以「自由公平貿易」促進社會和諧,並聲稱近數十年戰事劇減得力於「資本主義和平」多於「民主和平」——可惜資本主義從來等於剝削,歷史上亦是暴力的推手。書中未有對國家與資本作整合分析,也許源於作者拒絕將社會正義納入和平的定義。對同樣師法康德的柄谷行人而言,兩者關係匪淺,世界和平必然建立在公義之上。柄谷行人從社會系統分析出發,認為唯有超越資本主義的交易模式,在更高次元回歸「禮物經濟」,自社會到國際層面均貫徹以互酬原理,方可消解矛盾的潛在因素。「餽贈能夠發揮比軍事和經濟更強大的力量,普世法治並非靠暴力而將由贈與所支撐。」例如由合作社反抗國家與資本的運動做起,透過改變國家性質,最終轉化聯合國的內涵,柄谷行人相信如此才是康德所講「世界共和國」永久和平的真意。正如貝歷覓承認,現代實際上未曾經歷過「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國際事務繼續由大國政治博弈的邏輯主導。只要世界依然受制於資本體系的不平等結構,不公不義所助長滋生的衝突就不可能終結。
俄烏戰爭的爆發向世界拋出了一連串難問:領地侵略是否捲土重來?西方規則秩序會否沒落?數十年來的相對和平是否短暫的戰間期?對貝歷覓及烏克蘭人而言,類似問題太過離地,焦點還應放在眼前的戰場。貝歷覓長年提倡「國家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肯定國際出兵介入的必要,反對「非暴力主義」(pacifism)一類和理非論述。鑑於俄軍種種暴行,貝氏支持軍事援助烏克蘭,認同唯有協助烏國戰勝,才能令更多地方免遭蹂躪;維繫和平,由擊退侵略開始。或者和平的確是一寸一寸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