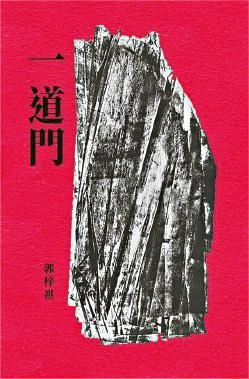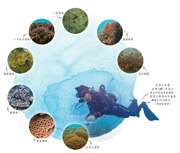【明報專訊】歷史上有不少的作家都被賦予極大的使命,基本盤也需要以文字打救世人,或者記錄時代的側面。這次訪問了一個很不合群的作家——郭梓祺,貼近時下潮流的形容,就是很「佛系」,隨心、任性,只寫自己喜歡的東西。郭梓祺新書《一道門》,以散文之姿投到香港讀者眼裏,如他的序所言:「散文集尤其注定如漁翁撒網,永不知道哪篇會在何時打動誰。」
新書名為「一道門」,起初是源於郭梓祺有一天在樓梯口看到鄰居的「尋門告示」,便覺得十分有趣,竟然有人在尋找門。後來,經歷了《蘋果》和「立場」的「關門」後,令他不禁反思:「有很多東西都閂了門之後,有沒有一些門可以打開呢?」他坦言,當時的專欄作家,包括自己都是抱着「寫得一篇得一篇」的心態去面對《蘋果》的倒數,而他得知《蘋果》結束的消息後,便在直播裏看着一份份報紙如何從印刷機裏產生,批量上到貨車,運到旺角,人龍排隊等待這份《蘋果》的畫面,令他印象深刻,感觸良多。他說:「現在實體報紙在我們很多人心目中已經fade out,由其他東西取代,但是直到看到《蘋果》最後那一刻,才會覺得印報紙原來有那麼強大的意義,仍然是可以凝聚大家,真的很神奇。」
《一道門》分為前後兩部分,上半部分的文章都曾刊於《蘋果》名采版,承接上一本將《蘋果》專欄結集的《無腔曲》,原汁原味保留了郭梓祺當時寫下的專欄文章;後半部分則是《蘋果》閂門之後的文章,以〈《蘋果》因緣〉為起點,延續下去,他說:「我不想這個專欄因為《蘋果》的結束而立即結束,我會覺得傷心。」他看到好友馮睎乾繼續在facebook專頁延續專欄的文字,他也產生了相同的想法,希望在網絡繼續「無腔曲」。
「無腔曲」的專欄始於二○一七年,郭梓祺受到馮睎乾的邀請,和王偉雄教授在周六輪流寫名采的專欄。他本是名采版的忠實讀者,得知能夠和其他出色作家共寫一版時,令他感到十分新奇——既是作者也是讀者的雙重身分,觀摩其他作家的文字,寫作者可以學習到不同風格。他指自己平常很喜歡看馮睎乾和邁克的專欄,偶爾也會看林夕的文章。星期六的專欄相比其他日子的版面更為豐富,郭梓祺認為名采的專欄質素高,是其他報刊難以比擬的,「這是與《蘋果》班底能找到什麼人有關,名采的專欄以往有很多很厲害作家,能和他們在同一位置寫東西,是與有榮焉」。他表示自己並不多看名采版以外的專欄,而且較常看舊一輩的作家,如喬伊斯(James Joyce),覺得他創作上和文字上的生命力與幽默感,可能還未被人充分認識,例如《尤利西斯》,其實寫得幾好笑,同時在玩弄整個英文小說傳統,反寫荷馬史詩,非常百厭。他也很有洞察力。「他對整場愛爾蘭獨立運動的態度頗冷淡,我並不是認同他的看法,而是看到另一個回應事物的態度。我覺得香港可能需要更多這種以另一個態度來回應的勇氣與自由。」
寫專欄的歷程
郭梓祺早在二○○九年便於《信報》刊登文稿,後來是「星期日生活」,發表對電影、書的想法。年輕的時候,郭梓祺會在電郵裏寫長文章,並傳給他的好友細看,一起討論。而這個三人小群組擁有一個特別的名字——「康德讀書組」。受到成員的鼓勵,郭梓祺將稿件投到《信報》賺取稿費,「那時候很開心,可以用稿費買書」。他坦言當年書寫這些文章時,有一種很強烈的寫作念頭,當時他看了不少歐洲電影,覺得這些電影都很厲害,很想和大家分享,加上那時又沒有什麼人提及這些電影,他希望填補這個空缺,「我覺得很不公平,這麼好的東西竟然沒有人知道」。時至今日,「康德讀書組」雖有成員已移民,仍然定時隔空Zoom着交流想法、互相學習。郭梓祺認為這種認真的好友非常難求,笑道:「隔了這麼多年,仍然有三條麻甩佬在講美學、哲學之類的話題。」
在二○一九年時,遭逢社會突變,郭梓祺一度不想寫東西,但礙於專欄的存在,他還是硬着頭皮書寫下去,「請假又會煩到編輯找替更。如果不是專欄,我想我當時不會寫。現在回看,卻慶幸當時寫了,流露了那時候的情緒和想法」。有不少作家遭逢突變時,會選擇以虛構的故事表達,但是郭梓祺一直都以散文作為主要的文類書寫。他認為這是自己最舒適的表達方法,也暫時認為自己沒太多東西要用虛構來表達。郭梓祺喜歡看散文,他在不同作家書寫的散文裏汲取了不少養分,如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散文,精煉,短促,常能在小事引伸開去,就不比他的小說遜色。散文於他,就是一個巨大的容器,「Essay這個詞本來就代表不是很有系統,或者帶有隨意的意思,它是一個不太受限的文體,令我可以將腦內的聯想、跳躍的東西、朋友的反駁等等浮現於寫作上。我就覺得這種浮游的狀態很好玩,也正因為寫,才會gen出將那些事物之間本來連自己也未必為意的聯繫,有時像砌好一副自己造出來的puzzle,會有驚喜。」
「好玩」也是郭梓祺的寫作特色,他的文字總帶着幽默感、有娛樂性。郭梓祺指自己的家人都喜歡「亂噏」、開玩笑,並非是取笑他人那種玩笑,而是拿自己來開玩笑。他並沒刻意要求自己專欄要寫得有趣,笑言自己沒被編輯投訴,便覺得應該還好。但是他對寫作也有一把隱形的尺,並以此來要求自己——不可以言之無物。
企開半步去寫作
可是隨着報紙的沒落,專欄的文化也漸漸消失,慢慢失去了專欄作家這回事。郭梓祺分享寫專欄有不少的限制,不只是寫作的字數長度,也不能和當下發生的事過分抽離。報章與社會發生的事緊密連繫,刊於報紙上的專欄自然不能避免對時效性的考慮,可是郭梓祺還是和「即時」保有一種距離——他認為人在瞬息萬變的社會裏,很容易被牽着走,所以他常常都會「企開半步」去思考事情,在寫作時亦然,不會立刻回應當下發生的事情,避免「跟得太貼」,以半步之遙來思考事情的其他角度,再作具有意義的補充。郭梓祺笑言自己是個「挺任性」的作家,即使在《蘋果》這種有很強公共性的媒體,他還是只寫自己喜歡的東西和「識寫」的東西。對現實生活的觀察尤其細微,喜歡以自身經驗和看法融入文章之中,「我寫作時很順心的,恰巧有些東西我覺得幾得意便會寫進去」。
郭梓祺和其他作家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對自己的寫作很滿足。和其他作家傾談時,都會留意到他們的抱負目標,對未來的寫作路的想像,但回歸郭梓祺的寫作之路,他常言:「我做凸咗(我做多了),做凸晒㗎啦大佬!我係得咁多,寫到咁多。」他續指:「我沒有很大的雄心和掙扎。」這種坦然的心性也和郭梓祺的家庭背景有關,他形容自己一家人對事都比較「laid-back」,「我們有少少是旦,最好不要太辛苦,但又做到些東西」。當他人希望獲得業界的肯定和獎項,或是文藝事業更上一層樓時,郭梓祺卻認為若說自己真有什麼成就,應算認識了一些要好的朋友,與人之間的關係:「我真的十分幸運,身邊有很多朋友、前輩都對我很好。這些關係不是努力就能擁有,比較虛地說,是緣分,也有好運。」
寫作和出版的時間差
寫作,可視為作者與讀者之間的緣分,不少作家都在意讀者的反應,郭梓祺也不例外,他道:「最好有人睇。可是有些作家,出書十八年後,我才讀到他,延遲了很多,作者本人也根本不會知道。」作者期待的回應落空,對於現在的郭梓祺而言,是自然不過的事,也是作者需要承受的事。郭梓祺形容世界走得太快,有太多的資訊內容,當下的確有不少事情都能快速地得到回音,若然沒有保持距離的自覺,就很容易被湧現的資訊帶着走,很害怕變得落後。他很慶幸自己無法跟得上時代的速度,不時被「甩開」,寫作正是讓距離和時差出現,停一停,找回思考的空間。他續說,即使寫得多快,和social media一比較下,就會顯得很慢,加上寫專欄要等待到某個日子才刊登,時差上的微妙致使閱讀有更多的面向。在序裏他引用保羅.利科(Paul Ricoeur)的「雙重日食」(double eclipses),指文本脫離時空脈絡後並非壞事,在寫作時,因為讀者被隱去,作者不知文本會被如何理解;在閱讀時,讀者也不必在意作者的原意,文本就在這兩重的遮蔽下,脫離當下的處境,有着無限的可能性和落差,文本本身可以代表自己說話。
出版《一道門》,除了是下筆和事件發生的時間差之外,還有出版印刷的時間距離,這種延遲比發表文章的時間距離更長。郭梓祺認為正正因為這種延遲,才令這本書具有意義,因為事件都距離當下一段時日,以及發生的事太多,令他不能清楚記得事件的發生次序,藉着這次出版,讓他能夠再以另一種距離觀察自己,「我再看的時候,都感到十分有趣,我像一個讀者」。
他續指出版是以書這種載體呈現,具有物質性,從排版設計、紙質的選取和印刷,都是文章總和以外的東西,是在報紙、網絡以外不一樣的風景。郭梓祺分享,這次設計《一道門》花了不少時間,讀者可以在書裏留意到封面的圖案是報紙過油墨、壓印的過程,隱喻了《蘋果》報刊成為讀者大門的狀態,此外為了讓讀者聯想到《蘋果》,在選取封面紙和襯紙時,都使用了《蘋果》的代表色——紅色和淺藍色。郭梓祺形容這次的出版十分順利,不論是編輯還是美術,都得以發揮各人的長處,造就這本《一道門》。
新書的出版,也算是「無腔曲」專欄的總結。雖然郭梓祺仍然會在Patreon發表文章,但是出版《一道門》後,令他不禁懷疑是否要結束這個專欄了?他說:「我想我會繼續寫下去,但是不是需要每兩個星期寫一篇散文,我不肯定。」他還是順從自己的內心,想寫就寫的隨性,沒有野心去實踐所謂「miles stone」,還回說一句:「我都做凸咗,miles乜嘢stone啫?」
info:郭梓祺
郭梓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學士、英文系哲學碩士,任教高中中國文學十多年,曾於大專教授歐美文學課,並在艺鵠開辦不同文學班。著有《積風集》、《積風二集》、《積風三集》及《無腔曲》,近著有《一道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