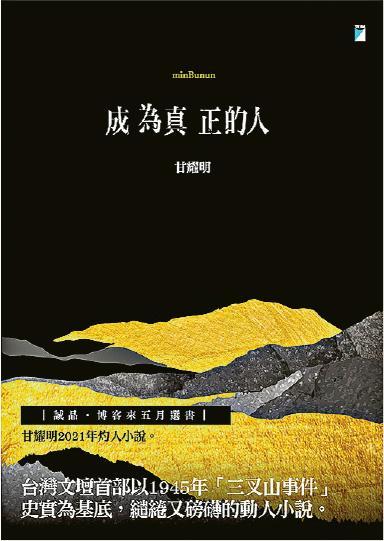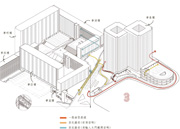【明報專訊】台灣作家甘耀明憑着《成為真正的人》榮獲第九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的首獎,「紅樓夢獎」由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主辦,旨在鼓勵華文長篇小說出版。甘耀明另一本書《邦查女孩》也曾獲紅樓夢獎的評審推薦獎,這次得獎可謂更上一層樓,對他本人來說,獲紅樓夢獎有着特殊意義。甘耀明曾受浸會大學之邀成為駐校作家,和香港作家交流,在香港也居住了一段時間,能夠在故地獲獎,他說:「可能是種緣分吧,這是一份情感。」
《成為真正的人》以歷史事件「三叉山事件」為根底,講述一段驚心動魄的高山救援故事。書名的英文名稱MinBunun,「Min」在布農族的意思是「成為」,「Bunun」的意思就是人,所以整句的意思為「成為人」,是布農族成人儀式,由小孩過渡成人,也是主角布農少年經歷苦難的成長之旅。
小說家的嗅覺與細節
甘耀明素來熱愛大自然,在2004年的一次登山的經驗裏,聽聞了「三叉山空難事件」,雖未有親身到遺蹟,也萌生了將之寫成小說的想法,一直到2019年才動筆書寫《成為真正的人》。「對我來說,這個創作的時間有點漫長,可見這個故事在我腦海裏像一根非常巨大而牢不可破的鐵釘,深深吸引着我。」「三叉山空難事件」發生於1945年,一架美國的飛機在運送盟軍戰俘的時候,因為颱風風勢猛烈而使飛機先著火、撕裂後撞向山脈。甘耀明指小說家對題材的嗅覺非常靈敏,「三叉山」的故事一下子便令他感覺到小說的張力——罹難的美國軍人被台灣及日本的搜救部隊搜救,而當時的日本人正正與美國人勢成水火,美國軍隊更是在戰爭中常常使用轟炸機轟炸日本部隊,而台灣因為是日本的殖民地,也不可避免地被炸彈波及,台灣人和日本人在這次戰爭裏也有不少死傷。「台灣人和日本人上去救難,其實是在面對自己不久前的敵人,心情是很複雜的,這就是張力。」甘耀明道。
在2020年時,甘耀明為了寫小說,特意親身到遺蹟現場調查,他形容現場是「十分駭人」,因為飛機在半空中撕裂,飛機的殘骸散落得到處都是,他聯想至當時的情景——美國軍人經歷了漫長而艱苦的戰爭渴望回到家鄉,卻沒有想到因為空難而葬身在台灣的高山;進入高山的搜救隊搜救行動極難,水源既不充足,也沒有遮陰的樹木。《成為真正的人》的資料蒐集也是非常仔細,甘耀明揚言:「我敢打包票,為了寫小說,我是台灣裏面研究這件事最厲害的人。」他指台灣沒有人找到飛機失事的主因,而自己在翻查美方的資料時才解開了飛機墜落台灣的秘密。
此外,「三叉山」除了是一件空難的意外,也是關於台灣原住民布農族的。布農族居於山上高處,而甘耀明以布農族少年為主角,也大量地蒐集有關布農族的資料,包括1945年山上的歷史氛圍、當年的樹木等等,「對我來說,這是重新體認一個族群的方式」。他續說:「我每次的書寫,都像讀一個碩士班,大量地蒐集資料,是建立我對那個環境的理解。我認為每個小說書寫者,都是這樣追求細節。」
歷史和虛構之間的小說
「三叉山」畢竟是歷史事件,當歷史和創作結合時,也需一定程度還原歷史。甘耀明訪談空難死者的後代時,他發現那些後代對於這次的意外也不太清楚,而且大部分死者死時十分年輕,沒有留下後代,當下的人對於當年的意外非常模糊。所以「三叉山」即使是歷史事件,也沒有很多見證,慢慢變成了登山人士的傳奇。甘耀明說:「實際上也沒有人知道整個真相,對我來講,這是可發揮的地方。」甘耀明續指自己不喜歡以真實作為切入點去寫小說,所以他常常以野史的角度去看歷史,而也因為「三叉山」的資料不多,歷史和虛構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比較其他清晰的歷史事件,小說的邊界和紅線是較明顯的,小說家可以進入創作的部分並不是這麼多。可是,在虛構的情節裏,甘耀明還是要拿揑一些正確的資訊,比如是罹難者的背景文化,這些故事的人物不能超出界線。
就如前文所說,甘耀明找到了飛機失事的真相,他感到非常興奮,可是作為小說家的他,轉念一想——或者讀者對此並不感興趣。後來,甘耀明也證實了這個推想,他在社交平台分享了這個歷史的真相,網友也沒有熱烈地回應,「對讀者來說,小說也是以人物的張力為主」。他續指:「寫小說跟寫歷史是不太一樣,我們是在歷史的縫隙裏找到人物的光芒,所以我寫這個小說,最重要的還是以虛構的人物為主,因為歷史裏沒有太多關於涉事的人的姓名、性格的描寫,只是一個模糊的、描述事件的東西。」而判斷讀者對哪些情節感興趣,甘耀明回應,作者同時是小說的第一個讀者,他在書寫的過程中,寫好每個段落後,會以讀者的眼光去看,而一個理想的讀者,他的品味是需要長時間培養。「我作為讀者的時候,我比較清楚的是理想的小說該如何呈現。」他補充,雖然沒有做法能夠滿足全部讀者,但是自己也是身處那一群讀者之中,有信心可以滿足這撮讀者的口味。
甘耀明在寫小說時,篩選了一些歷史的片段加入小說,這樣做的目的是剔除讀者不關心的細節外,也是回歸小說創作的本質。他認為將歷史事件重新塑成小說,以小說介入時,重點是在對死者的觀點和看法,還原以及同情他們在歷史場景裏的複雜感受。「這些人透過我的書寫,他們的人物性格會明顯一點,那也能讓讀者理解他們在山難、空難之中作出的選擇。」
書寫是去理解不同國籍不同情景
《成為真正的人》裏書寫了不同國籍的人,包括美國人、日本人、布農族人等。跨性別、跨民族的書寫向來都是小說家共同遇上的難題,畢竟自己並非某個性別、來自某個國家,理解上的差距是難以彌補。甘耀明認為,書寫另一族群或國籍有難度,但也是小說家的本分,比如自己在書寫布農族的時候,他閱讀了大量布農族的文化,也將《成為真正的人》給了布農族作家去閱讀,去審核自己的小說。他說:「我盡可能做的是,貼合美國人、日本人、布農族人的思維,我必須說,這個跨族群書寫對我有點困難,所以我小說的書寫必須客觀、公正地貼合他們的氛圍。」
而寫及日本人和布農人之間的關係時,甘耀明留意到布農人不滿日本人那種高壓懷柔的政治方針,可是甘耀明並沒有刻意將日本人塑造成強悍的角色,反而試着去理解日本人柔軟的內心。「寫小說還是要還原人的立體性,而不是他的單一性,盡量去還原角色的多種可能。」
《成為真正的人》的大環境是災難,小說家在故事裏想像人在極端的情况下,如何表現自我,探索人性。甘耀明認為人都渴望着愛,因為愛而不得才會感到苦痛,也因為愛人逝去也變得痛苦,很多作者都以苦痛去理解人性。而在小說裏也充滿着苦痛,比如在二戰帶來的生離死別,甘耀明舉例說搜救隊離開家人上山救援也屬於一種苦痛,他們對回家的渴望正正是《成為真正的人》裏重要的部分。「在窮山惡水和颱風下,他們想回家的念頭是最後的依靠。」所以在搜救時展現的人性關懷和愛,是處於一個瀕臨絕境的中找到希望,這種愛是更為耀眼。
對甘耀明最為深刻的發現是,那些搜救隊成員年齡是20至40歲,青年和中年男子也有。這些搜救隊員不止有搜救隊這個本分,更是別人的父親或兒子,是關乎十幾個家庭的生命。一個父親的喪生意味着幾個孩子的苦難,甚至是家庭的撕裂,所以甘耀明在思考如何塑造他們的感覺時困惑:「作為歷史小說,我該如何將救難人員後代的感受加入小說?」畢竟紀錄片可以客觀地將後代的想法直接加入而不突兀,於是他在小說裏創作了一個爸爸帶着小孩去救援的橋段,去描寫父子在救難時的情感,以及加入了角色回到山下去看自己兒子和女兒的情景,去刻劃這種兩代之間的親情。
詩意的文字 從山上而來
《成為真正的人》在紅樓夢獎獲獎點評裏,決審委員會主席鍾玲是如此讚揚:「呈現離奇的故事、多元國族的交匯、大自然的神秘和深邃、高超的小說技藝、通篇的浪漫氛圍和精美而富詩意的文字。」甘耀明在《成為真正的人》中對於在宏大場景之中對文字的處理特別用心。「我覺得這是個感傷的故事,想在感傷的故事裏有抒情的成分,比較詩意的文章能夠更加表達到角色的感情。」他自言在人物對於感情追求中的文字表達處理得比較好,以及布農少年在成長裏的情感也寫得比較吸引,這兩個部分的文字處理是獲獎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作為主角的布農少年,他也在故事裏寫詩,在敘事裏形成兩種不同的節奏,令通篇故事更富詩意。
甘耀明其實在其他作品裏的文字也富有詩意,卻沒有像這本《成為真正的人》特別被評為「詩意的文字」,他比較過往的作品與《成為真正的人》,認為《成》說故事的速度放得更慢,而這種「慢」,恰如其分地拿揑到一個分寸,令讀者留意到他在文字上的用功。他說:「我以前寫的文章,語言本來就比較特別,特別在於活潑,在於創造。可是這一次的小說除了繼承這些特點外,我也有用詩意的文字去營造小說的氛圍。」
另外,甘耀明比較喜歡書寫大自然,因為他從小居住在山村,接觸大自然,四周都是農田。「我從小就是山上的孩子,對山的氣氛和嗅覺比較敏感,也聽了大量山的傳奇。」童年聽到山裏的傳奇,成為了甘耀明的創作養分,他更在20多歲時登上台灣各個山頭,看到大自然宏偉的一面,山的味道又變得不一樣,他認為登高望遠是極為舒坦之事。為了書寫自然的不同層次,甘耀明更閱讀大量有關植物的書籍,希望能立體地看待山,看到植物的內在,擁有新的自我的觀察,不是用一眼就看得到的視角,而是用文化作為一個切入。「如果我們只用一雙眼睛去看大自然,你也只是走馬看花而已。」
《成為真正的人》就如書名一樣,在大環境的危難之下,人類如何成長、成為真正的人,人的條件又是什麼。真正的人都追求着愛,卻深受苦難的折磨,在這個特殊歷史背景下,甘耀明帶給我們一個有血有肉的故事,不同國籍的人在此交匯,同樣面對大自然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