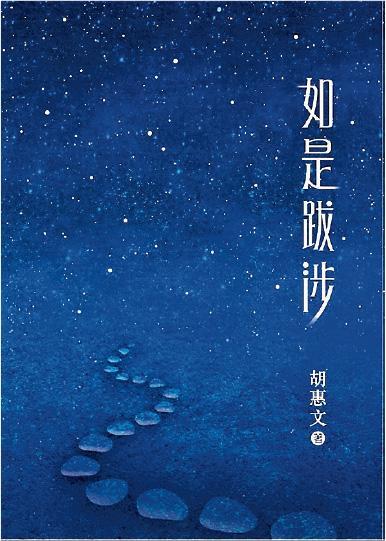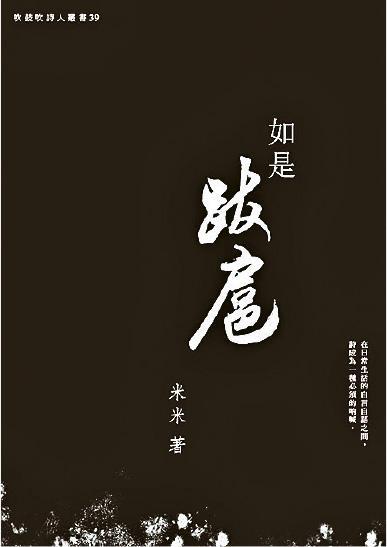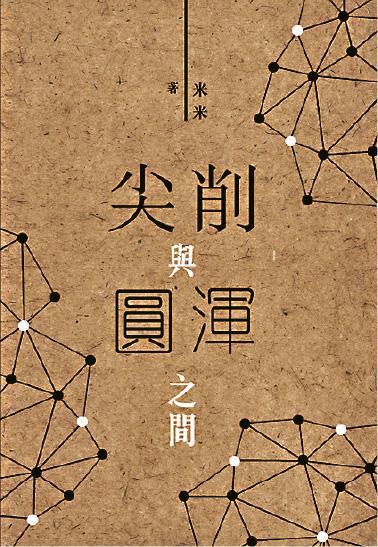【明報專訊】有些人創作起初是一個愛好,好比寫詩,看到文學家的詩才,就不禁投射將來的自己往這班成功、名傳千古的人身上。當這個愛好維持多年,便不再是愛好,是吃飯飲水般的習慣。他們早忘記了當初想成為誰的欲望,而是尋找自己的本質,風格也逐漸摸出屬於自己的路,思考透過藝術如何表達自我。在眾多年輕詩人出版詩集的暑季,寫詩已有20多年的香港詩人胡惠文,以質樸深藍色封面回歸讀者眼中,這本《如是跋涉》已是他第三本詩集。歷經不同寫詩階段的他,如今寫詩已自成一格,就如他的序所言:「我最大的希望還是寫出自己的聲音。」
「清湯牛腩」以外的詩意
胡惠文在《如是跋涉》出版之前,也有過兩本詩集——《尖削與圓渾之間》及《如是跋扈》,三本詩集的風格各有不同。首本詩集《尖削與圓渾之間》的詩風接近內地,取材比較多樣;第二本詩集《如是跋扈》,胡惠文希望擺脫「大陸腔」,於是模仿台灣年輕詩人的詩作練習,傾向寫抒情、個人想法的詩。胡惠文說:「如果你不認識我本人,可能會以為我是個廿四五歲的年輕人。」距離上一本詩集已有4年,現時50多歲的胡惠文,再次出版詩集時褪去寫詩的摸索和實驗,邁入寫作上較為成熟的階段,在創作上更接近自己的本質。新書書名中的「跋涉」帶有旅途的艱辛之意,寫出了詩人真實、困頓的生活,現在回望過去,他沉靜地說:「現在50歲人,經歷過許多事,詩集裏寫我的家族、我新界的生活、觀察到的鄰居,是比較接近我真實的一面。」
胡惠文在《如是跋涉》裏以生活作為題材,這本詩集亦是他回歸平淡的見證,此前他對詩的技巧有種特殊的追求,甚至覺得寫日常事物的本土詩「求其」,像極「清湯牛腩」,「好像強姦了香港的詩」。其中有一位詩壇的前輩和胡惠文在網上社交媒體「筆戰」,兩人不打不相識,最後更成為好友,而這也是胡惠文學習將生活帶入詩的轉折點。胡在前輩的介紹下,開始閱讀也斯的詩,他開始喜歡這些香港本地詩人,也斯、周漢輝、鍾國強等等,然後他跟着將一些日常事物寫入詩。「我從前最看不起的題材,有沒有搞錯?這些是散文來的,沒有詩味的。去超級市場寫成詩,和老婆吃飯又寫成詩……當我嘗試自己寫的時候,發現是很難寫的。」
從對這種日常敘事的詩不屑一顧,到學會欣賞,再到現在書寫,胡惠文認為寫日常事物是「有所感而作」,也是一首詩的基石。「憑空想像捏造出來的詩是很難感動人。」他補充,即使意象再亮麗,也只能吸引一些小文青,真正讀詩的人一下子便知道這些詩虛有其表。他領略了再多的技巧都是虛假的,唯有真實的情感才能打動人,至此他不再寫虛有其表的詩。可是,胡惠文亦強調,並不是所有的「清湯牛腩」、生活雜事都可以成為詩。「不能說去買個麥當勞也能感到悲天憫人吧?」只有觀察入微的詩意,才能成為一首詩,這是有關美感的判斷。
最近有不少網民提及賈淺淺的「屎尿屁詩」,既有人覺得不文,亦有人大感有趣。胡惠文認為只要用得其所、表達合切,任何物象都可以入詩,包括屎、尿、屁,可是若然是嘩眾取寵便不可取。他提及內地有一種風格奇特的詩派——垃圾派,專以屎尿之醜去挑戰傳統美學,他批評:「垃圾派妄稱一切醜為美,其美學基礎已經大有問題。」胡惠文指賈淺淺的詩是試圖以屎尿屁作為吸引眼球的手段,並不是以這些物象來探討生活。他感嘆:「當這些異類大行其道,眾生見之嘩然,實行口誅筆伐,一時之間,沉悶的文壇又好像多了點話題,其實有咩特別呢?」也希望作者不要拿排泄物大做文章,它們只是一類普通不過的意象,沒有任何值得褒或貶的價值。
愈慢活 愈快樂
自從開始書寫生活,胡惠文對生活、現實也看得比從前慢,也更仔細,寫詩也慢下來了。他笑說自己從前對詩狂熱得可以一日寫10首之多,可是現在要「慢慢來」。「其實不需要那麼快,人在慢的過程裏才懂得什麼是生活。」《如是跋涉》便寫了5至6年之久。「我不是為了寫本詩集而寫,而是有所感而寫,這些詩是一種積累。」胡惠文說。詩集有不少胡惠文居住元朗的影子,他在元朗過了20年歲月,平日騎着單車在元朗腹地打轉,觀察着元朗的景色、人們。他起初對元朗的喜愛是源於環境和童年接近,村屋和平房都予他親切自在的感覺。
胡惠文在農村水鄉長大,即使來到香港這麼長時間,仍然不習慣城市的急速生活,偏好大自然的世界。他回憶起童年的生活裏有一條重要的河,現在也不時夢見,而人們則在河流的附近生活,這條河流和周邊的花草也不時出現在他的詩裏。胡惠文自言書寫大自然是最接近他的本質,不論在過去或現在,他的生活都和大自然息息相關,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寫大自然對胡惠文而言,是一件相當信手拈來的事,他很自然就能將自然界的物事聯繫到生活裏,觸發他的所思所感,單單是〈如是跋涉〉的組詩,便出現了不少有關大自然的物象,比如蝴蝶、海鷗、海景、山景。「自然能觸動你某種非常隱秘的情緒,觸發了人和物之間的關聯,比如我看到白鷺孤單站在岸邊,我很自然便會想起自己的身世,很漂泊很孤單。或是看到榕樹的樹洞,我會想起童年時的爺爺,他會看着我在樹洞附近玩樂,這些會勾起我的回憶。」他補充,這種大自然的聯繫並不能刻意經營,而是「可遇不可求」,就如神的感召一樣。
而在這段創作時期,他開始叩問自身,比如在〈如是跋涉〉的組詩裏,以「思源」、「生長」、「往返」、「順流」和「習慣」為題,展開一連串對自己生命軌迹的觀察,反思自己。剖白自己又談何容易?對自己也需絕對誠實,寫詩不能虛構。胡惠文看到好友說他的詩像「豆腐火腩飯」,便笑指:「其他人的生活或許很有詩意,但我很在地,只是一個普通的麻甩佬,本來的生活如此。在放鬆的心態寫詩反而是寫得最好。真的不要做作。」
胡惠文對自己的作品也有很高的要求,他比喻自己的詩就像拍電影一樣,指王家衛拍《重慶森林》也有着無數個版本,他的詩作也如這般多版本,單單是〈秩序〉一詩便花了32年重寫。他每日也會以讀者的角度重看〈秩序〉一詩,常常都會有「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會將整首詩改頭換面。他覺得改詩的過程十分好玩,每個階段的變化都是一種娛樂。「原來第一次寫和現在相差這麼遠,改了又真是好一點。」他認為一首好的詩,是需要沉澱的,需要將詩作放入雪櫃,讓詩和詩人都各自沉澱思緒,過些時日會有新想法,當回看詩作時便需要好好審視它。胡惠文指一首詩剛剛開始改的時候,是十分不穩定的,模樣或會大幅變動,但去到最後,都是斟酌一些字眼。十年磨一詩,胡惠文就是最佳的體現。
元朗孤獨老人
在元朗生活的胡惠文,特別喜歡踏着單車去看周邊景色,以及寫下元朗人們的生活,觀寫眾生,在《如是跋涉》裏一共有30多首便是寫了人們生活的苦况,思考生命裏的低潮。他尤其愛好書寫低下階層、被社會遺棄的人們,「他們的生活是很有詩意」。在元朗市郊裏,胡惠文會偶遇到一些資源匱乏的家庭,貧困到香港人無法想像。他談起每天在小巴上看到的一家三口,妻子和孩子的精神出現問題,唯一有謀生能力的丈夫也十分委靡,三人住在鐵皮屋裏。每次他看到這些生活上被受折磨的人,都會產生一種同情,也感受到他們的絕望,因此想寫下他們。「我不是很沉溺這種絕望,我不斷問為什麼生活裏有這麼淒慘的人。我想幫他們卻無能為力,我很心痛又同情他們。」
「我不想相信這個國際大都市,這個盛世,是有這樣的事情發生。」胡惠文感嘆。從他的文字裏,也透露着對這種被受忽視的人所面對的生活,帶着毫無出路的絕望,而他僅僅是一名旁觀者,也只能夠抒發他對這些人的關懷。他在元朗看到很多孤獨的老人,他們沒有子女照顧,隨着年齡增長,不難想像到老人的未來。「我不覺得他們會有什麼出路,除了等死,而這些不是孤例,是很多個,很多個。」作為寫作者,他將這種具有公共意義的觀察寫成詩,寫出香港不為人知的真實倫常,質問:「點解香港係咁嘅?但事實上就係咁。」
在〈秩序〉一詩裏,胡惠文也選取了一個在下白泥居住的伯伯作題材,他的房子下陷,喜歡看着周六日時的年輕人耍樂,是他一生最快樂的時間。因為真實的慘况是如此誇張、血腥,他傾向以呈現的手法寫出生活的細節,寫出了這個伯伯孤獨的生活。他是如此寫道:「如果植物不枯/訪客仍隨意把無用的細碎/丟棄在這地方/他就可以整日忙碌……」這些真實的生活觀察是需要花上時間,而細節帶來的生活質感,是令讀者動容。他表示自己有一段時間也感到相當孤獨,也並非刻意要看到這些同樣孤獨的人,而是舉目皆是,孤獨的人太多。
網絡論壇遇伯樂
書寫詩,胡惠文也清楚這是一件十分小眾的事,閱讀的人口就如一杯茶那麼少。反而,他認為詩太流行的話,會傷害了詩的高貴。胡惠文說:「假如你去茶餐廳,阿伯拿着詩集而非馬經,去到這個地步,就不覺詩高貴了。」他認為詩就是罕有的興趣,才會變得珍貴。年輕時的他,便是喜歡小眾、獨立的興趣,彰顯着自己的與眾不同,比如聽英國的獨立音樂、到影藝戲院看一些文藝電影,他認為那時候已看到詩性開始醞釀。在剛剛開始寫詩的時候,他不像進入學院、於詩刊發表詩作的詩人,反而隱匿在自己的書桌前默默寫詩,將工作遇到的迷惘、生活的困窘以詩作發泄。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發現有人在網絡論壇上發表詩作,他便分享了自己的作品,也得到一些回應和批評,讓他與其他詩人連結起來。他的第一本詩集《尖削與圓渾之間》便是由網絡論壇上認識的伯樂「橋」資助而出版的,受到他人的鼓舞,令到胡惠文更加鑽研詩藝。
他分享自己透過寫詩,認識了很多良緣,是一種寫作人和寫作人之間的惺惺相惜。他曾到訪新彊拜訪詩人朋友,在火車站告別的時候,那個朋友明明是一個7呎男兒,卻在告別時眼有淚光,「我們都知道這次的告別很難再相遇」。胡惠文說:「詩人的內心都很溫柔。」正正是這種溫柔的內心,才能寫出體恤人情世故的詩作,對世界才有這麼多的關心。
寫詩已成生活一部分的胡惠文,他已視詩為個人的哲學和宗教,而自己是一個教徒,「不敢想像沒有詩的生活」。寫詩,就像他其中一個出口,讓他逃離終日都在打工、庸碌的生活,也是他對生命的觀察留下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