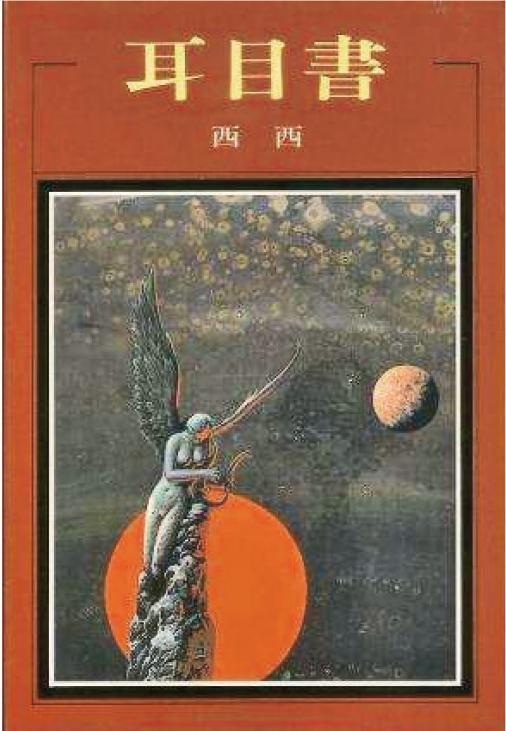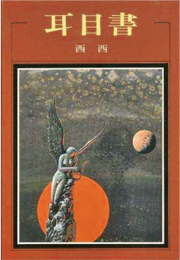【明報專訊】人們說,悼念作家的最好方法,是坐在角落靜靜讀他或她的作品。追念西西,不少人都會在書架上挑出她的小說,而其實,虛構世界以外,足球賽場亦是這位頑童多年來深深着迷的魔幻之地。一九九○年,國際足協世界盃落地意大利。其時,《明報》一整個月的「世界盃特刊」每日連載專欄「西西看足球」。在那小小方格內,西西摸透地把五百字左右的文字繫至書本、電影,以至種種文化理論,與一般波經𠝹劃開截然不同的氛圍。思念西西的這段日子,我們重新摘錄刊載「西西看足球」,並邀來當年「世界盃特刊」的編輯石琪回憶這個神奇的體育專欄,一則一則地爬梳「西西看足球」的舊報足迹。
這是用腳踢出來的書 /文•吳騫桐
十二月中旬,世界盃以美斯淺吻大力神盃的畫面拉上終幕。如果球迷作家西西仍在世,不知會如何閱讀這個童話一樣的美滿結局?找回舊報紙。一九九○年,西西在《明報》寫第十四屆意大利世界盃的連載文字,看完只感覺不可思議,那雙眼睛,真的一頁一頁地把球隊、球證、觀眾、足球自身如同文本似地掀開來看,就像她所寫:「看足球,其實好像閱讀一本書。」
西西原名張彥,父親張樂是業餘足球員,退役後在上海當教練,亦是球證,綽號「十二碼大王」,一九五○年代來港後,輾轉於任職的九巴公司重操球隊故業。而西西,則自母親肚皮內到落地跑跳的不少日子,都磨耗在足球場內。她在〈球證衣缽〉裏回顧童年時光:
父親是球證,所以我從小上球場看足球。二、三歲時,坐在母親膝上自言自語;五、六歲蹲在地上拔草挖泥沙;八、九歲時,等待休息時間有人來派發汽水;十一、二歲時,光看球員的彩衣花衭。後來,才一點一點慢慢學習看足球。(「西西看足球」六月十七日)
沒有承接父親的衣缽,但裁決球賽那種電光眼般的精準目力,仍耳濡目染地留在西西體內。翻看當年「世界盃特刊」版面,非體壇中人的專欄有李碧華「界外球」、何嘉麗「妝台點評」等。西西發出的異聲截然不同。那如球滾動的隨筆,導引讀者敲響不同領域的門:〈錦上添花〉嚷嚷米蘭開幕禮的時裝表演為何沒有設計師阿曼尼;〈足球與鐵塔〉用法國莫泊桑和羅蘭巴特的鐵塔故事,勸慰世界盃月裏不愛看足球的人;〈鐵幕足球〉以結構主義人類學家李維史陀的強弱文化論調,評點球隊風格的改變……
看足球猶如文學閱讀
而看足球是閱讀這用力戳破界線的宣言,出自〈足球如文章〉:
譬如意大利對奧地利,我是當散文看;蘇聯對羅馬尼亞,我當小說看;阿聯酋對哥倫比亞,我當戲劇看。哥倫比亞隊尤其是喜劇作品,你看那個守門員,完全是魔幻寫實的踢法,全場奔走,一會兒是前鋒,一會兒是清道伕。難怪哥倫比亞的作家說,在我們的國家,一切事都是可能的。(「西西看足球」六月十一日)
限時競技的框架下,不同球隊對壘碰擦出各異的節奏感,或快或慢,或鬆散或嚴謹——小說、散文、戲劇的分類看似破格,仔細比照卻又非常合理。文學與足球的可比基礎,我想,某程度上是它們同樣扎落的一大片故事草場,那裏,總被無形的作者之手(球員/教練/球證/觀眾/你和我)佈陣,其間,情節有的中斷,有的得到發展,部分人躍升主角,或瞬間被罰離場淪為配角,大結局峰迴路轉又一下子無聊頂透。套用西西的話語,當代足球評論不應再只「新批評」地聚焦於射門與否的單一文本,而應擴展至整場賽事肌理的深廣結構。
因此,在她筆下,哥倫比亞隊狂人希告達輸關鍵一球後,俯伏禁區線前的畫面,是終幕的悲劇,是馬奎斯首部映照拉丁美洲的小說《迷宮中的將軍》,是那繞不出幻覺榮光而自毁的統治者。魔幻寫實。純屬虛構。愛爾蘭隊輸了,同樣令她聯想起伯爾的散文集《愛爾蘭之旅》,彷彿耳聽作者勾勒的那些愛爾蘭人自我開解:幸好,只是摔斷了一條腿。
她在專欄末篇如此總結:「世界盃是一部長篇小說,是巴赫金所說的『複調小說』」——短暫逸軌的狂歡時間,顛倒常規,加冕和脫冕之中,雅俗平等打成一片,互換對話。在她,一九九○年那場國際球賽最值得閱覽之處,是其特別多角度、多語言的眾聲敘事。何福仁的〈從頭說起——和西西談足球及其他〉收錄了她的解釋:「這一屆的冠軍之爭,很巧合,很富於巴赫金所強調的二重性,正是新舊冠軍的比賽。新和舊,歐洲和南美兩種不同的風格,大多數人眼中的正與邪。」二○二二年的世界盃,有這樣撞擊的火星嗎?揮動受難故鄉的旗幟、不唱國歌的球場表態……不論如何,一個月的世界盃嘉年華完結,複調聲腔亦隨即被扭滅。有什麼話還要說,留待下屆從頭來過。
足球這部書的登場人物
撇開愈挖愈艱澀的文學理論,「西西看足球」偶有幾篇技術含量飽滿的純球評,說賽果,評球星,一口氣談出局或進級的那些隊伍。夾雜其間,發現一種猶如用雙筒望遠鏡放大細察的人物寫生。草圖似的筆觸。比如〈出局大軍〉和〈南美的希望〉開首一句,彷彿有顆特寫鏡頭忽然湊過去:「禾拉坐在觀眾席上,摸摸項頸,舐舐嘴唇,從踢球變成看球,就看列度怎樣配合奇連士文了。」「哥高查緊抱皮球,然後放在地上,飛奔出禁區。」而〈只是一條腿〉更置入了轉換視點的小說技法:
開角球的時候,我就看見他了,握着一幅巴西國旗,站在球場邊緣的觀眾席上。他是巴西球迷,他還沒有回家。[……]穿十號球衣的人今天怎麼了?史度高域老射失,南斯拉夫要輸了,他想。咦,馬拉當拿射的球竟給守門員輕易接住,糟糕,阿根廷要輸了,他想。[……]南美的球隊還不至於完全被淘汰。他高興地揮動巴西國旗,我發現我就是這個揮動巴西國旗的球迷。(「西西看足球」七月二日)
直播鏡頭猶如眼睛,帶她走到地球另端的比賽現場,還未夠,隔着熒幕,把眼睛和心偷偷附在那位巴西球迷上。他想其實是我想。支持同一支隊伍的共感鏈結如此強大,心連心。想起西西一九八六年在小說〈這是畢索羅〉裏,亦是此般想像其時三十三歲的巴西傳奇國腳薛高輸掉世界盃後的複雜心理。她最愛的一支國家隊。南美緯度的赤熱陽光溢滿街頭,黃與綠,不時奏起的森巴鼓樂配着巴圖卡達的嘉年華拍子,永遠澎湃,永遠自由——她覺得,那地孕育的足球是一種藝術,專欄也反反覆覆地寫,如〈苦守不輸波〉:
只有在南美,以至非洲,還殘存某些把足球當藝術,當表演的踢法。你看哥倫比亞的門將吧,他一直很享受足球,他可不是小丑[……]這是實用主義的世界,從做人到踢球。然則為何我們會批判巴西小小的妥協呢?巴西過去輸了球,舉世怪責它唯美;到它寫實了,又反過來抱怨,嫌它不再巴西。這是我們在現實主義之外,深層心理裏仍有一種對美麗嚮往嗎?(「西西看足球」六月二十三日)
文學,某意義上從來是一份對美麗的嚮往。西西的文學之眼,使她從足球,從這項追逐與奔跑的運動中,看見夾縫裏一切盛爛的美好——人類肆意揮灑生命力的自由意志。(但,即便是不太喜歡的球隊,她也嘀咕着花了一整欄篇幅寫,如〈狐狸教練〉:「把西德和意大利稱為狐狸球隊,是因為兩隊都有一名足智多謀的教練。」)好的文學總是連帶深刻的人物,足球亦如是。
短短數百字,由足球到文藝,話題牽來扯去織成巨大的星圖,佈在三十二年前一份日報體育版的特刊裏,閃閃發亮。那專欄方格,是西西夜夜流連的球場,也是挑戰讀者的實驗場。熟知球圈又囤着如此豐厚學識的文壇作家,可遇不可求。現實裏,西西鮮少再闢類同的足球專欄。想當然,狂歡式看球是很累人的事——她在收入「西西看足球」大部分文章的《耳目書》序裏,提到那年世界盃幾近掏空了自己:「什麼也不做,每天給報紙寫五百字左右,這是我近來最愉快的一段日子。結果,眼紅、耳痛、牙痛,耳裏彷彿灌滿了水,休息了一個多月才恢復。居然一口氣看了三十多天球賽,常常是一晚看兩場,自認是小小的奇蹟。」
二○二二年的今天,沒有舊報紙,只可翻閱洪範書店出版的《耳目書》。整齊地佔滿一版版書頁的文字,仍然有趣,但讀上來總有種孤零零的感覺,就好似,失去了與其他人和事碰撞的聲音,那玩耍着搶佔閱讀地盤的報刊趣味。
………………………………………
訪一九九○年「世界盃特刊」編輯石琪
吳:吳騫桐
石:石琪
吳:為何會邀請西西寫世界盃球評?
石:我以前在《明報》做編輯,會幫忙做世界盃、奧運的版面。一九九○年,我負責做「世界盃特刊」,想找幾個人寫專欄,其中一個就是西西。西西是陸離幫我聯絡的——陸離是我太太,她和西西是好老友,我們三人是很多年的朋友,年輕時因工作認識,大家都在《中國學生周報》寫東西。
至於為何請西西寫呢?因為她是足球迷,她父親是球證,她自小就好熟悉足球。
吳:那麼,「西西看足球」專欄當時評價如何?
石:她在《明報》寫世界盃的專欄,得到好多人稱讚,那時總編董橋還說:哇,搵到西西嚟寫,總之好讚賞她。西西的角度和普通球評不同。她是一個文藝人嘛,用文藝家的角度來寫,不是一般「波牛」。
吳:你作為編輯,有沒有和西西討論過專欄文章的方向?或者修改過?
石:沒有!當然是讓她自由發揮,一隻字不改。她很專業,寫作很嚴謹,對自己很嚴謹,對文章要求也很高。基本上沒出過什麼問題,她每晚都好準時用傳真機交稿。
吳:那個年代的報刊專欄,是不是較少女性評論足球?
石:是的,當時熟悉足球的女性不是那麼多。而西西不止感性,她真的熟悉足球知識,這一點相當特別。那次「世界盃特刊」,除了西西,我們還找了另外一兩個女性專欄作家,都寫得好好,好得意,與男性講波很不同。
其他男性作家——我知道有很多人是球迷,但不太清楚他們會否寫球評,或寫得好不好。那時找西西,也是因為她的家庭背景,她父親是上海和香港的球證,她自己有一直跟進南美波、歐洲波的情况。
訪問、整理•吳騫桐
……………………………………………
「西西看足球」專欄摘錄 /文:西西
鐵幕足球(一九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朋友談足球時說過:沒有自由,就沒有好球。以往鐵幕國家的球隊,以蘇聯為首,其次是東歐各國,亞洲則殿後,但放諸世界,充其量仍不過是二、三流。這是因為足球比賽的變化比排球、籃球都要大,不單依賴體力、合作,還需涉及許多方面。以往的鐵幕國家,以體能、紀律取勝,卻囿於思想的包袱,變化少,臨場應變的能力低。此外,他們的球員,大抵是足球工廠的產品,依一個模子炮製,勝能保障相當的質量,可是真正的足球天才,往往來自街頭,像拉美的比利、馬拉當拿,那是自由塑造,各具性格,然後再加工的成果。也只有這樣,足球才成為藝術。
還有一點,足球其實也正如文學藝術,要多觀摩與交流,那是視野、意識的開拓。這一屆西德的幾位主將,馬圖斯、奇連士文、布林美、禾拉等,都有進步,多少是外流意大利足球圈的收穫(意大利近年集各地精英,是目前全世界最高水平的地方)。尤其是奇連士文,去屆並不顯眼,今屆已能獨立闖關了。以往鐵幕國家球員國際賽的經驗少,球員出外的機會不多。
當然,結構主義人類學家李維史陀所云「過分交流」也是一個問題,受外來文化的影響而喪失自己文化的例子也有(這與文化的高與低、文明與原始無關,因為影響力可以通過經濟、軍事之類因素發揮出來)。比如巴西吧,不少球員也跑到意大利、葡萄牙去了;為了適應歐陸作風,不得不改變踢法,而且因為差距太大,成為一種質變。巴西的得失,見仁見智。至於東歐,目前只限觀摩,交流太少。
這一屆世界盃,東歐適逢政治改變,正處於歷史的過渡,而足球竟也表現出來。自由了些,可是同時失去了過去的體能、合作和紀律。蘇聯正處於青黃的尷尬期,水平稍降;奇妙的是羅馬尼亞必然會出現一反傳統的極端個人主義球員希格。為吸引歐陸球會,他們都爭相表現。如今南斯拉夫和捷克都能進入八強,整體成績是進步了。真正的自由,終能產生好球。
足球如文章(一九九○年六月十一日)
看足球,其實好像閱讀一本書。這本書可以是散文,可以是小說,可以是戲劇。譬如意大利對奧地利,我是當散文看;蘇聯對羅馬尼亞,我當小說看;阿聯酋對哥倫比亞,我當戲劇看。哥倫比亞隊尤其是喜劇作品,你看那個守門員,完全是魔幻寫實的踢法,全場奔走,一會兒是前鋒,一會兒是清道伕。難怪哥倫比亞的作家說,在我們國家,一切事都是可能的。
讀書要選擇可讀性高的作品,看足球這本書也一樣。事實上,在足球場上,兩隊作戰,除了和局,總有一隊輸。世界盃這本大書,包括了各式各樣的輸。這正是值得一讀的「輸」。譬如阿根廷對喀麥隆,阿根廷為什麼輸。驕兵必敗?沒有足夠的熱身賽?單靠一個足球巨星?國家隊只有三枚隊員,其他都出國効力?球賽頻密,一個球季下來,鐵打的球員也散了?
可讀性(readable)高的書是一本好書,但更好的是重讀性(rereadable)高的書。上屆法國對巴西的一場「世紀之戰」,真是一本好書,不單可讀,而且可以重讀,可以一讀再讀,百看不厭。我喜歡巴西球隊,因為他們永遠是值得閱讀的好書,雖然,好書不一定暢銷。今年的暢銷書是意大利,但願會是一本可讀性高的書。我喜歡閱讀小說式的巴西、散文式的西德和戲劇式的荷蘭。
勇哉英格蘭(一九九○年七月七日)
英式足球,表現得漂亮的時候,真令人歎為觀止。我們在本屆世界盃準決賽中,終於得以一見。英格蘭踢得真好,如果這支球隊一早遭淘汰,將是球迷多大的損失。從英格蘭來看,不禁想起巴西、荷蘭、蘇聯那些有實力的隊伍,還沒有恢復狀態,提早出局,太可惜了。阿根廷不是也要到準決賽時才漸漸回勇麼。
勇哉英格蘭,帶動了球賽的速度,球員不斷飛快地奔跑,使西德不得不捨棄較緩慢的推進。在一百二十分鐘內,雙方都顯示了驚人的體力,連綿不絕,把皮球由這邊的禁區帶到那邊的底線,忽長忽短,又從那邊的龍門口逼到這邊的小禁區。巴西球證不時給予得益球,使球賽更流暢,節奏更明快。
加士居尼、柏加不斷在我們眼前跑來跑去,英格蘭把馬圖斯和奇連士文盯得很緊,使他們發揮不出更強的攻擊力,施路頓頻接險球,比時下某些浮躁自負的守門員更令人敬佩。胡禮穩重、連尼加敏銳、柏列靈巧,英格蘭隊員個子高大,頭球凌厲,使西德的角球也不敢大意斬入龍門口,而常常彎出十二碼外再施行勁射。
兩支出色的球隊表現了開幕以來最好的一場比賽,能夠握手言和多好,可惜又要互射十二碼。華度的一球太離奇了,不過,正如意大利總理所說,坐在看台上,一切看來都容易。
十二碼球(一九九○年七月八日)
十二碼球的得失,不全是由運氣所支配,運氣佔一部分,體能一部分,信心一部分,另一部分,卻來自練習。一位門將說過,既然十二碼球是球賽中的一環,很重要的一環,尤其是在淘汰的賽制裏,由十二碼球定斷的機會那麼高(數數看,今屆世界盃有多少場呢?)賽前就要做好準備功夫﹕自身技術的訓練不算,還要留神觀看對方射手踢十二碼球的習慣,翻看錄像,觀看他們的比賽,擅用左腳抑或右腳,喜歡選取哪一角度。因為劇戰一百二十分鐘之後,半數球員在體能下降,以及重大壓力之下,只會踢出他們平素習慣的球。
日前就有一個最佳例證,強如馬拉當拿在阿根廷對南斯拉夫時,把球踢向對方門將艾高域的右下角,結果被救出。前此,在其他場合,艾高域也曾救過馬拉當拿這樣的射球。如果意大利的辛格肯瞄瞄馬拉當拿上一場的錄像,摸摸他過去在拿玻里的球習,牢記一下,就有五成機會。事實證明,這位世界球星踢出同樣的十二碼球,力度不足,角度也並不太好,辛格卻撲向相反的方向。
同理,在這種淘汰賽裏,領隊、教練也應該讓球員做好踢十二碼球的準備,訓練足夠的話,也有助於提高信心。努力總會帶來收穫的,何獨踢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