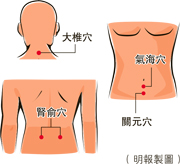【明報專訊】20多年前,伊朗聖城馬什哈德16名女性性工作者遭連環殺害,兇手竟受民眾支持,認為只不過替天行道、淨化聖城。最荒誕的是,這並非小說情節,而是真有其事。現正上映的電影《聖誅》,伊朗導演亞里亞巴斯不止描繪伊朗厭女惡况,更旨在闡述病態社會如何扭曲平凡人。
「『厭女和伊朗政府非常不好』,我用一句說話就能告訴你,根本不需要拍部電影來說明這件事。」亞里亞巴斯(Ali Abbasi)神態自若地說。
他是40歲出頭的伊朗新生代導演,10多年前到哥本哈根修讀電影,定居至今,並在歐洲發展電影事業。頭兩部電影Shelley和《邊境奇聞》(Border)皆以歐洲為背景,但今次執導的《聖誅》(Holy Spider)則改編自伊朗連環殺手的真人真事,講述在2000年的馬什哈德,賽義德哈奈(Saeed Hanaei)誘騙女性性工作者到其公寓,連續殺害16人,得名「蜘蛛殺手」。虛構女記者拉希米(Rahimi)追查真兇,但水落石出後,伊朗民眾竟支持蜘蛛殺手替天行道、淨化聖城。
「厭女不單止是宗教的事,我覺得它更深層次地,是一個文化問題。」亞巴斯在之前訪問也多番强調。他雖認為伊朗政府助長了厭女氛圍,但《聖誅》並非要批判伊朗宗教或政治,只因厭女文化在伊朗社會上盤根錯節。或許,亞巴斯更想透過電影反映伊朗的病態社會。
平凡人淪連環殺手 反受擁戴
亞巴斯從Maziar Bahari的紀錄片And Along Came a Spider(2002)留意到,賽義德哈奈徹頭徹尾是一名平凡男性,他是建築工人、3孩之父、虔誠的穆斯林,參與過兩伊戰爭,走到街上也毫不起眼。《聖誅》描繪的賽義德哈奈同樣平凡,亦不時見到他對着家人流露的真摯,也或因參軍兩伊戰爭而身心受創。平凡的他在病態社會中扭曲,「我認為這更近乎他現實中是個怎樣的人」。但他也强調,電影世界不一定要100%貼近現實,兩者之間存在許多自由創作的空間。
《聖誅》特別描述到,賽義德哈奈東窗事發後,其子竟然欣賞和崇拜父親的行為,原來也是亞巴斯從紀錄片中觀察到的一點:「那個兒子仰望他的父親,並視他為英雄,我想這算是從(紀錄片)中得到的奇怪印象。」他續解釋:「他視父親為英雄,因為他根本不明白他(父親)究竟做了什麼……有些人說『你要繼續抬起頭』、『你父親沒有做錯』,批判思考對他來說太難了。我覺得他只是個孩子,還失去了爸爸,所以(兒子的行為)很合理。」厭女文化無緣無故地在下一代萌生,20多年後仍穩如磐石。
「頭巾示威終結是假象」
今年9月中旬,伊朗庫爾德族女性阿米尼因佩戴頭巾(hijab)時露出頭髮,被宗教警察拘捕,拘留期間死亡。事件引發「頭巾示威」,演變至今已不單是女權運動,示威期間不少死傷,更有不少人被處決。被問及《聖誅》於當下有何信息,亞巴斯道:「那裏(伊朗)人們不再示威是個假象,因為迄今已經3個月了。」
「我不是超級政治化的人,不想做任何政治聲明。但像《聖誅》,電影有時會超出我預期。伊朗的事已經發生了,我們也沒辦法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當然希望觀眾留意《聖誅》的電影價值,但我也知道伊朗發生了很多事,有些電影情節會被人拿出來相提並論。」雖然如此,他並不介意人們討論此作時談論頭巾示威,但當然希望觀眾感受到電影的藝術價值和觀影體驗。
亞巴斯雖不熱中政治,但有時想用電影反映社會就會被捲入政治其中:「尤其在一些國家像伊拉克、伊朗,可能你在中國也察覺得到,不用花多大工夫,所有事就會很政治化。就如中國和伊朗,處理新冠時變得很政治化,不應變得那麼奇怪,應是很簡單、直接的事。」記者問他會否擔心惹上麻煩時,他雙手托頭淡然道:「嗯,已經有麻煩了。當然,我不懼怕。當這部電影面世時,我已料到會出現很多反應,但現在很多反響(與我原先預料的)有點不同,因為現在(伊朗)有更大麻煩,他們(伊朗人)正為了生存而奮鬥。」
伊朗故事 更是普世故事
伊朗導演離散在世界不同角落,他們的電影大多都未能在伊朗上映。無獨有偶,近年不少香港電影也未能在香港上映,例如《窄路微塵》導演林森與任俠聯合執導的劇情片《少年》,還有兩部紀錄片——周冠威的《時代革命》和陳梓桓的《憂鬱之島》等。即使離散,伊朗電影卻仍然連結伊朗人的心:「很多人之所以離開伊朗,並不是因為他們想離開,而是非離開不可。那些離開的人仍有希望、夢想,和來自伊朗的回憶,情感上依然與她(伊朗)相連。」亞巴斯更笑言,伊朗人自有方法去看在伊朗看不到的電影。就算不再定居伊朗,亞巴斯創作伊朗故事時也不覺有距離感:「我在伊朗出生和成長,也定時會回去,並非20年來都沒有回去。我希望這個故事(聖誅)不單止是一個伊朗故事,更是一個普世故事,就算你是否伊朗人也可與之連結。」●
聖誅
預告片:bit.ly/3EuhV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