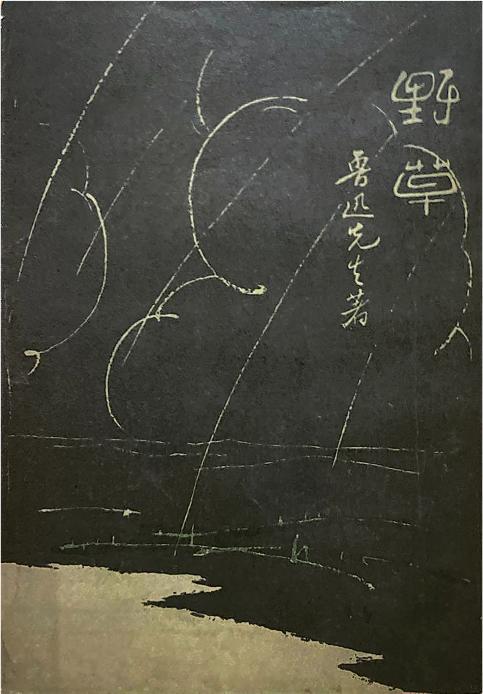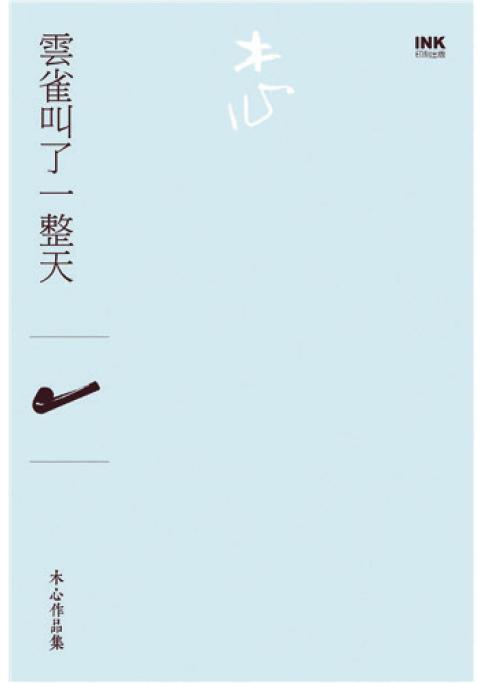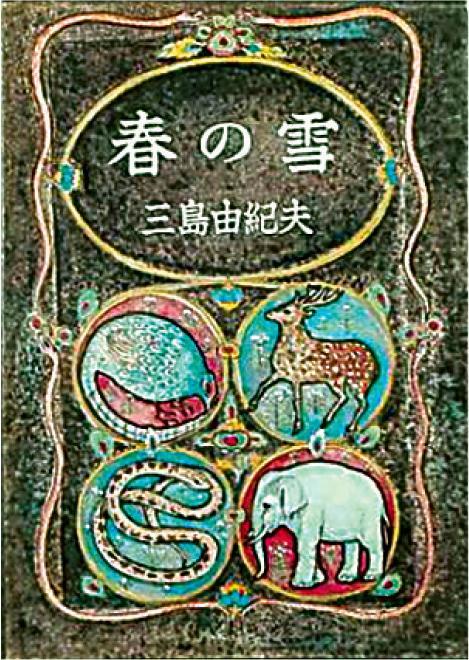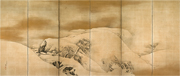【明報專訊】「雪」是一個常見的文學意象,但相比起其他自然景物,雪自有其特異之處。大凡日月星辰,高山流水,若不是意指循環,就是象徵恆定。自從「風景」被發明以來,各種自然之物自有其位置,或如日月的周期隱現,或若山水的靜謐穩定。在這一自然景物的意象框架中,「雪」則顯得奇詭多變了。
有很多種方式可以考察「雪」在風景中的再現形貌。例如「雪」意味着冬和冷,它隱含着四時變遷和溫度變化,而「雪」則是這些變化的極點,年盡而冷,冷盡則雪。但「雪」也象徵了對風景面貌的高度改寫,從大雪紛飛到白雪皚皚,天地山水在短時間內被蘸上白色,原來的色彩和景致被覆蓋,令人頓然覺得天地突變。至於變成怎樣,則視乎文人作者投射的心境了。另外,雪也有地域性,在中國,南方少雪,北方以雪習常,兩地之人的雪意也有抽象與具體之分。當然說到極地山巔的長年嚴苛雪態,又是另一番景象了。再者,既然很多地方的「雪」都是一年之中的異托邦式時空,「雪之始」跟「雪之終」也很容易觸發書寫者的敏感神經,初雪起,雪止了,都是經常說到的意境。
轉喻內在心境與人格
中國古典詩詞中的「雪」,除了被視為外物風景,再引伸為炎涼世態時局的隱喻外,更深刻的乃是以雪的冷峻轉喻為個人內在心境和人格,極致者如唐代柳宗元的〈釣雪〉:「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風景之物全滅,只剩雪,跟「釣雪的人」,儼如天地間只有雪跟人,這也是獨立於雪景中而想到蒼茫之意。另一種則是借雪之嚴酷引發高傲人格,常見的是託於雪中梅花。例如唐代黃檗禪師名句:「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梅花耐寒,時見為隆冬之喻,於是從雪冷到梅香,就成為一種人格上升的象徵。
關於雪與梅的辯證,尚有流傳甚廣的〈雪梅〉二首,宋代詩人盧梅坡作:
梅雪爭春未肯降,
騷人擱筆贊評章。
梅須遜雪三分白,
雪卻輸梅一段香。(其一)
有梅無雪不精神,
有雪無詩俗了人。
日暮詩成天又雪,
與梅並作十分春。(其二)
詩人從詠雪到詠梅的轉折,在於不只以雪梅為「喻」,更在於有意識地將「雪梅爭春」視為一個跟詩人對話的場景。詩人不再自况為傲雪的梅,而是自視為雪與梅這番爭逐的見證者。詩裏說「有梅無雪不精神,有雪無詩俗了人」,其實雪、梅、詩人,三者缺一不可,有了詩人,「雪」才不「俗」(應是「雪梅爭春」才不「俗」)。此詩體現了詩人面對雪時的後設自覺。
魯迅「詠雪」的現代性
但中國古典詩詞對「雪」本身的起伏變化不大敏感。這可能跟中國文化中「與自然冥合」的內涵有關,重意境象徵而不重客觀觀察。對此我們可以舉民國時期魯迅的一篇作品〈雪〉作比照。此文收於《野草》,讀過《野草》的讀者都會知道,書中所收文章表層是寫事寫物,但背後往往有着相當複雜的精神思辨。有人會將文章歸類為「散文詩」,但此分類拼湊感太強,掩蓋了魯迅文字的深邃絕妙。〈雪〉寫的是兩地的雪:江南的雪,跟朔方的雪。魯迅是浙江人,他對雪的早年經驗應在江南。文章說江南的雪「滋潤美艷之至」,還「隱約着的青春的消息」;他也寫了雪中孩子們造雪人的愜意情境:「孩子們呵着凍得通紅,像紫芽薑一般的小手,七八個一齊來塑雪羅漢。」 然而文中的主體「他」(可能是魯迅本人,也可能是他創作投射的主角)卻獨自坐着,彷彿無雨無晴地看着江南的雪的變化:「但他終於獨自坐着了。晴天又來消釋他的皮膚,寒夜又使他結一層冰,化作不透明的模樣;連續的晴天又使他成為不知道算什麼,而嘴上的胭脂也褪盡了。」此段如此一寫,其實是烘托後段寫「朔方的雪」(即北方的雪)的文字。後段裏不再見「他」了,只有客觀地描述北雪的種種形態:「永遠如粉,如沙,他們決不黏連,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這樣」;「在晴天之下,旋風忽來,便蓬勃地奮飛,在日光中燦燦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霧,旋轉而且升騰,瀰漫太空;使太空旋轉而且升騰地閃爍」。
文末當然才是精髓所在:「是的,那是孤獨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有論者認為,魯迅借論南北之雪喻當時北伐前後的時局,但我們也該注意他寫南雪是融入人情,寫北雪則是抽離冷眼。這是一種中國文學中「詠雪」的現代性。
關於雪態之變,還可以舉台灣詩人楊牧的兩首詩。一是〈第一場雪〉。詩分三片,俱以「今年冬天第一場雪」一句開首。換言之,楊牧寫的是「初雪」,這從無雪到有雪,從未冬到入冬的交接時空。詩的第一片寫道:「今年冬天第一場雪/起初是驚訝,淺淺的/喜悅——可以讓我描寫了/滿足你的好奇。雪」那是遙遙呼應了盧梅坡的題,即「以雪入詩」的後設想像,初雪引起詩人的驚訝、喜悅,及跟「你」對話的興致。
然後詩說到詩人打算藉初雪回信給「你」,同時又因初雪想到與「你」在地域連帶體感溫度上的距離:「你是豐饒的大暑/雖然你說冷鋒過境/始終你還是永遠是」。
但第三片筆鋒就轉了,雪很快就停了:「今年冬天第一場雪/入夜以後就停止了,我在/研究室裏打字,試論/文學批評的方法和態度/明天早上松鼠和小鳥/也會出來在雪地上打字/論核桃,翅膀,和童謠」,詩人借雪論文學,同時類比小動物踏雪而過,這都是在「明天」雪停後才進行。由此,由雪所引發的詩興,乃是來自一場短促的雪:雪起了,然後雪止了,詩人就捕捉了這個短暫的異托邦,寫了一首詩。
另一首楊牧詩是〈雪止〉,詩人捕捉的則是雪止之後一刻:「雪止/四處一片寒涼 我自樹林中回來/不忍踏過院子裡的/神話與詩/兀自猶豫/在沉默的橋頭站立」,同時馬上借雪想到詩的本體問題,但詩人卻敏感地環顧四周,從「屋裏有燈」、「飄零的歌」,再注意到「一盆臘梅低頭凝視」。這臘梅可能不存在,只是詩人呼應古人詠梅傳統而寫,但從「聽見像臘梅的香氣的聲音」,他轉入了「你的夢」,也跟〈第一場雪〉一樣,意識的「我」與「你」的氣溫差距:「我自異鄉回來/為你印證/晨昏氣溫的差距」;「若是 你還覺得冷 你不如把我/放進壁爐 為今年」。
我即是雪,雪即是我
楊牧寫雪,依然是借雪回應自我內在的詩性思想。他比古典詩詞都更自覺於如何以雪在自然界中的起止,作為誘發詩興的景物。可是,尚有一種更逼近雪的寫詩方法:就是「自比為雪」。例如台灣詩人周夢蝶在〈讓〉一詩中有一名句:「讓風雪歸我,孤寂歸我」。全詩是這樣的:
讓軟香輕紅嫁與春水,
讓蝴蝶死吻夏日最後一瓣玫瑰,
讓秋菊之冷艷與清愁,
酌滿詩人咄咄之空杯;
讓風雪歸我,孤寂歸我,
如果我必須冥滅,或發光──
我寧願為聖壇一蕊燭花,
或遙夜盈盈一閃星淚。
雪歸詩人,其實就是將雪連同雪意中的孤寂導入詩人的人格中。這與古典詩詞中以雪喻孤獨,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境界。周夢蝶至情至性,以迹近修行之身逼近「孤寂」作為一種形而上的存在狀態,於是雪,就成了這個境界的擬物化表現。
除了周夢蝶,還有木心。內地網絡廣為流傳一首聲稱是木心寫雪的詩,是這樣的:
我是一個在黑暗中大雪紛飛的人啊
你再不來 我就要下雪了
雪飄下來 我是雪呀 我是雪呀
但其實詩不是這樣的。此三句原來分別摘取自不同的地方,第一句是出自木心一首名叫〈我〉的,全詩就只有這一句,收到木心詩集《雲雀叫了一整天》;另外兩句同樣來自《雲雀叫了一整天》,集中有一個「輯乙」,收錄了大量木心的無題短句,此兩句同收於此,但不是並排的。將三句拼貼成一首「詩」,可能是網民有意無意的誤傳,乍看之下,此拼貼滿有文藝腔,很適合文青們消費之用。這也是木心被長期庸俗地解讀的一個例子。事實上,將三句詩拆開回復原貌,會比較容易讀出木心的深意。
木心畢生追求的,是一種本體論式的美感。第一句詩的詩題為「我」,清明簡潔地將自我置於一個「黑暗」跟「大雪紛飛」的場景中,但要注意的是,此句不是解讀為「我在大雪紛飛的黑暗中」,而是應解作「在黑暗中,我是一個大雪紛飛的人」,即將「我」自視為「大雪紛飛」,不只以雪自况,更具體地以「紛飛的雪」以形容詩人本人的「離散」處境(木心曾以「飛散」一語來形容他的離散經驗)。把握了「飛雪」,是詩人個體化(借榮格術語)的一個境界。我們或可以猜測,「輯乙」中的那兩句:「我就要下雪了」、「我是雪呀」,很可能寫於〈我〉之前,詩人最初只道自己是「雪」,但去國經年,經歷了不同的雪意,最後才體認到「飛雪」最接近自我,因此才有了〈我〉這首短詩:以短短一句,斬釘截鐵,就把話說盡。這也是很木心的作派。
雪國意象與「物哀」
當然說的雪與文學,還有日本的「雪國」意象。「雪國」也是川端康成著名小說的書名,在這日本文學系譜中,我們可以找到不少以冰天雪地為場景引入小說故事的作品,比較著名的尚有三島由紀夫的《春雪》。
川端康成的《雪國》以藝妓駒子為中心,講述她與恩客島村、情人行男跟少女葉子淡然而糾纏不清的情緣。故事以行男病故、葉子意外身死、駒子失常崩潰告終,而一向置身於外的島村,則在結局中懷緬着逝去的雪國人事。至於三島由紀夫的《春雪》則是講清顯跟聰子互生情愫,私相幽會而最後珠胎暗結。但清顯優柔寡斷,而聰子則與皇室早有婚約,聰子的家人只好悄悄讓聰子打掉胎兒。最後婚約解除,聰子也出家為尼,清顯則無法接受失去愛人,積憂成疾,最後在雪中病逝。
論者常以《雪國》到《春雪》這一脈絡為近代日本文學中的「物哀」典範。「物哀」源於平安時代的《源氏物語》, 據江戶時代學者本居宣長分析,「物哀」是指個體接觸到外事外物時產生的心理活動,當中混合了喜悅、哀傷與憂愁,在情感之上更有美學意涵。因此所謂「哀」,不過是一個標記,並非純然是指悲傷。《雪國》跟《春雪》中的雪意,觸發了主人公對命途的哀思,尤其是當他/她的生活以至生命都趨向毁滅,其哀至極。但此哀則同時帶有美感,正如《雪國》中通篇寫雪,蒼茫而美麗,卻美麗得令人窒息。所謂「淒美」,即有此意。
日本半地雪國,但世界上不少地方卻幾乎是終年雪域。雪也不再是四時將盡的異托邦時空,而是民族生活與國家命運的常態。文章最後,我們可以舉兩詩為證。一是西藏詩人旦真旺青的〈雪山和雪山人〉(節錄):
雪山
如果你不能像人一樣站起來,
那麼你即使處在世界最高的地方,
那也只是讓每個人更加清楚看到你的醜陋,
躺在最高的地方,
不如站在最低的地方。
二是烏克蘭詩人謝爾蓋.扎丹(Serhiy Zhadan)的〈就像這冬天從未出現〉(節錄,彭礪青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