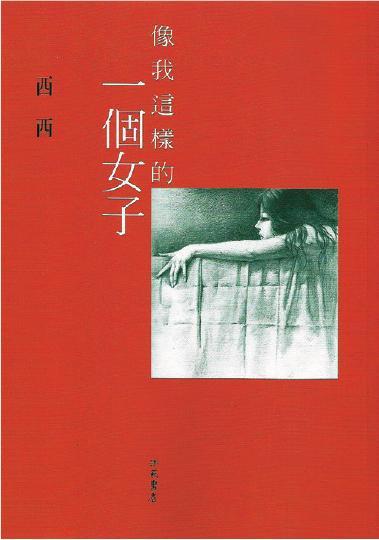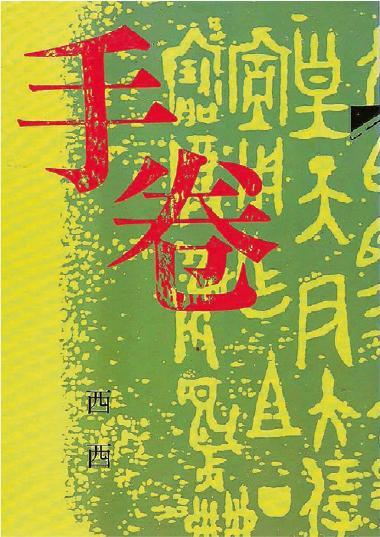【明報專訊】西西仙遊,回歸星塵。筆者是中文教師,自然成為朋友發問的對象:這位作家有何了不起?欲一窺其文學世界,該從何入手?雖然西西與金庸、倪匡同屬「國民級」作家,即逝世消息會成為頭條新聞的那種,但她與後兩者的最大分別,大抵是多數港人其實未曾有緣一讀其作品吧——除了現年33至46歲的一批,他們該念過〈店舖〉,因它曾是會考中文科課文;但囿於功利應試文化,啃過課文後會進而涉獵作者其他著作的,相信也為數不多。說穿了,這現象反映了一直以來「文學」與「流行文學」之隔閡,實在是可惜之至。我反正為友人開列了書單,那倒不如因利乘便,也向廣大讀者提供一張入門指南吧。
若論西西代表作,當然是《我城》。然而若以它為進入其世界的敲門磚,卻易令人生畏。它並不是普羅讀者心目中那種「長篇小說」,人物刻意地平凡,情節刻意地鬆散,運用了大量陌生化手法(如把麻將牌寫成「透明軟糖」),這分明是有意拖慢讀者閱讀速度,迫令他們用全新角度審視生活。單是全書首句「我對她們點我的頭」,數年前便曾掀起一場不大不小的網上筆戰。事緣有哲學教授初讀西西,劈頭便遇上此句,結果看不順眼,認為行文冗贅,繼而大筆一揮,再找來作家另一些文章修改一番,引起部分文壇中人不滿。這實在是令人扼腕的一場風波,《我城》在西西芸芸作品中本屬進階級別,卻受盛名所累,結果嚇跑了讀者。其實換個角度看,就當西西某些文句是嘮叨好了,但有些人說話方式就是這樣,當我們認識他們深了,便見怪不怪(記得當年論戰時有位網友留言,說有人也曾這樣修改三毛的文字,改後果然是通順了,但已完全認不出是三毛文筆)。前提是:如何讓讀者先好好認識西西這位說故事的人,和她筆下種種角色?最好辦法當然是找來她較平易近人之作,好讓大家先交個朋友。
從短篇小說切入
筆者教中文科,換個說法便是「書本推銷員」,慣於把書的優點說得天花亂墜,但求把同學引了「入局」再算,反正當讀者找到合適切入角度,便易進入書中世界。就西西的情况來說,她的短篇小說是較容易交的朋友——即使是《我城》,我也曾做實驗,節錄其中兩節權充短篇(第五章阿髮準備學能測驗、第八章阿果第一天上班),結果同學尚能受落。眾多短篇集中,《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一向是教師同行推介的首選,一來書名像極了文藝小說,二來同名篇章之「人物設定」(遺體化妝師)本身極具賣點,三來論者素來以「童話寫實」概括本書風格,似乎「童話」一詞對孩子有莫大吸引力。那麼讀者反應呢?一如所料,〈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和〈感冒〉兩篇最受歡迎,後者獲My Little Airport樂隊一曲 〈我在暗中儲首期〉的一句「不要重演西西的〈感冒〉」加持後,更受文青青睞。其他篇章則反應平平,〈玻璃鞋〉和〈蘋果〉等篇的所謂童話元素,同學更高呼「貨不對辦」。對中文科教師來說,這並不算滿意的「戰果」:既不欲同學把西西誤認為通俗言情作家,再者「童話」一詞似乎又不足以成為引導讀者領略西西妙處的鑰匙。西西是個有趣的人,一方面她見識廣博,筆觸出入古今,橫貫歐亞非美,甚至上窮宇宙,下至動物界,能一洗年輕人對華文文學老氣橫秋的印象;另一方面她筆法總是出人意表,思想也絕不老套,新生代在字裏行間當能找到共鳴——甚至現今流行的kidult和躺平主義,在其文章也多有呼應之處。這樣說也許對讀者更具吸引力。
近年評論流行文化喜用「Universe」一詞,即作品之間共同分享的角色和背景架構,最典型的有Marvel Universe(漫威宇宙)。其實西西眾多作品也自成宇宙:當中那些特立獨行的人、位處世界邊緣的人、旅行的人、喜歡運動的人、做工藝的人、從事教育的人,還有孩子們、動物們,以至萬物生靈,在那不斷擴張的作品宇宙中,我行我素,自來自去,卻又互相交往聯繫,組成一張綿密的網,各自傳遞着他們對生活的熱愛,對保持生命本真的執著。在這份指南裏,筆者會以較易讀的《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和《手卷》兩書為軸心,再旁及其他篇章,期望能勾勒出當中反覆出現的主題和形象,從而反映這個宇宙是何其繽紛寬廣。
西西宇宙中的「零號原型」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裏短短數頁的〈碗〉(也是目前中學中國文學科僅有的香港文學課文),頗適合成為這趟旅程的起點。它的主角葉蓁蓁,可謂西西宇宙中最核心的人物原型。她穿樸素的方格子襯衫,喜歡踢足球,皮膚曬得很黑——熟悉西西的讀者,馬上就認得這是她本人的寫照。葉蓁蓁毅然辭了小學教師的工作,拋棄主流觀念裏的鐵飯碗,不欲做一條噎死在碗中的金魚,每天自在地逛公園、看動物、讀書,這也來自其生平經歷。這隨意適性、任真自得的人物形象,將在其作品宇宙中不斷重現。作品由兩個人的獨白交替組成,葉蓁蓁偶遇事業有成的舊同學余美麗,二人卻自說自話,交而不通,這種寫法新穎但不晦澀,可讓讀者初步領略西西小說形式的創新。而故事發生的場所——香港動植物公園,這個囿於藩籬之內、卻又壓不住勃勃生機的空間,當中那些漂亮的鳥和猴、空靈的雲和樹,亦是西西小說裏最具象徵性的場景之一:「陽光暖暖地照在我的背上,太陽以它熾烈的針灸甦醒我冬眠過似的骨骼。」「有一片樹葉落在我的頭上,我從它的模樣尋找到它的母親,伊的名字是七星楓,伊使我抬起頭來,向高處看,向遠處看。我仰望樹,仰望天空,我看見了沒有翅膀但會飛翔的雲層。」有些人只看過西西某些刻意拙樸的文句,便武斷地認為她文筆稚嫩;若讀過〈碗〉這些靈動的句子,自當有所改觀。
西西的篇章常常互相呼應,在同一集子中,往往先來一篇短的,再敷展成另一較長篇章。與〈碗〉併成一對的,正是名作〈感冒〉,只要讀過前者,便能領會後者並不止於一篇關於悔婚的言情小說。〈感冒〉的虞(旁人喚她小魚兒),活脫脫就是葉蓁蓁另一化身——又或是〈碗〉裏那條被困於碗裏的魚(在〈感冒〉中又化成舒伯特歌曲中被捕獲的鱒魚)。在前作中,主人公的樊籠是世俗的職業觀念,於後作則換成婚姻制度,但那渴求真實地活着的靈魂,是並無二致的,這也說明了為何二人都喜歡運動。與其說觸發小魚兒出走念頭的是那重遇的男子,倒不如說是她對於自由游泳的欲望:「我並沒有枯死,如今我在水中游泳,有一種說不出的欣喜,我緩緩地游着游着,讓暖洋洋懶洋洋的水包容我的軀體,讓暖洋洋懶洋洋的陽光落在我的背脊,我是那麼地自由自在、無拘無束。」這與前作那在陽光下甦醒的描寫,同樣傳達了重拾自主意志的喜悅。此外,作者還安排了一條暗示生命復蘇的線索,即那些貫串全篇的詩句:由典雅的古詩,漸過渡至前衛的現代詩;而當中一開始引述了《詩經》「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句,兩篇互文關係呼之欲出。
姑且把葉蓁蓁和小魚兒這兩位帶着作者身影的女子,視作西西宇宙中的「零號原型」吧——都是追求回復生命本真的人。當掌握了這條鑰匙,她集子中一些較抽象的散文化小品,便較容易解讀了。像《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裏,〈抽屜〉中那反客為主地宰制了人們日常生活的抽屜,〈奧林匹斯〉中那患了「腦瘤」只見死物不見生靈的照相機,都是那扭曲生命價值的「碗」的寓言版本。《手卷》裏也有〈猬的二三事〉,那在郊外營地裏與大自然格格不入的「猬」,大概是〈碗〉的余美麗或〈感冒〉的丈夫之變奏;另一篇〈獎品〉裏那無視問答比賽規則,攜手逃離競賽場地的「我和他」,也同樣是不願遵守社會標準的一群。
「游於藝」的生命線索
由此出發,我們可發掘出另一種原型:從事工藝的人。西西的主人公們癡迷於各種嗜癖愛好,但那不代表他們像余美麗所說的「不愛工作」,只不過他們把工作視為藝術,心無旁騖地投入,也不計較旁人愛憎。在《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的開篇〈玩具〉,賣魚人製作冰雕,但冰遇熱即融化,無從保存,看來像西西弗斯那樣徒勞無功,但他偏自得其樂。《鬍子有臉》也有一篇〈檔案〉,那麵粉人小販也如是:他手藝神乎其技,可惜故事裏的學者只視之為死的研究對象,而他每遇「走鬼」時,麵粉人又散落一地遭人踐踏。沿着這條工藝者線索,當可明瞭〈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並不只是愛情故事:身為遺體化妝師的女主角,正是這樣一位卑微而高尚的工藝者,她默默而寂寞地為死者塑造完美遺容,做着別人懼怕的工作,這正是生命的全情投入。她看來受命運操控,重複了怡芬姑母的人生軌迹,而且這份職業同時遺傳自父親。但根本這一切是她自由意志的表現,因為她「毫不畏懼」,就如她的母親對嫁給遺體化妝師也甘之如飴。女子在咖啡室等候追求者,她預言對方得悉其職業後必落荒而逃。脆弱的世俗愛情,只是強大生命意志的對立面。
當掌握了這個原型,看來鬆散的《我城》也就容易理解了:第七章那造門的阿北,固然是敬業樂業的工藝者;第八章阿果跟隨麥快樂學習維修電話線,何嘗不是在正心誠意地學藝?西西晚年克服身體機能障礙,潛心於各種手工藝,且卓然有成,從《縫熊志》和《猿猴志》的布偶,到《我的喬治亞》的玩具屋,可見孔子所言的「游於藝」,本是她個人生命的線索。
古道熱腸的教師形象
西西前半生獻身教學,是故她對「教育」這主題總是念茲在茲。從上述的工藝者原型,又衍生出另一形象:從事教育的人。教師角色在《我城》早已出現,就是那位勸勉阿髮要創造「美麗新世界」的班主任。「目前的世界不好,我們讓你們到世界上來,沒有為你們好好建造起一個理想的生活環境,實在很慚愧。」這番語重心長的話,奠定了西西作品關懷孩子的基調,也與四十多年後她那常被引述的話遙相呼應——「年輕人並不欠我們什麼,相反,是我們欠他們,欠他們一個理想的社會。」
她的短篇中,〈假日〉隱晦地提及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文憑教師罷工運動,〈鬍子有臉〉為愛發問的孩子平反,〈聖誕老人與煙囪〉以電玩裏疲於奔命地救火的聖誕老人暗喻教師困境,都觸及教育課題,到《手卷》裏的一組作品:〈貴子弟〉和〈雪髮〉,教師更成為舞台中央的主角。〈貴子弟〉是別出心裁的極短篇,由四個似是不相干的部分組成:一、一篇名為「怎樣乘搭地鐵」,看來像說明書的學生文章;二、一位家長向校長投訴中文老師,指她出的作文題目不知所云,欠缺教化意義;三、校長與教師開會,眾人轉述「她」對傳統作文教學的強烈意見;四、一位同學的內心獨白:他深深愛上老師那既有趣又實用的作文堂,可惜老師遲遲沒來上課。小說的主人公從未露面,但她對教育的理念已躍然紙上。短短數頁,幾乎抵得上一齣《暴雨驕陽》(Dead Poets Society)。
古道熱腸的教師形象,在〈雪髮〉裏有所延展。這個故事,由作者早年一首新詩〈訓導主任〉敷演而成:一個被視為生性頑劣的孩子,被校方指摘踢毽子時讓紙屑散落一地,終日給罰站於紅牆之下;而那些碎屑,其實是魚木飄落的漂亮花瓣。這是西西作品中文辭最瑰麗的一篇,內容也異常豐富。「雪髮」是一位代課老師,在思想僵化的環境中,她對被標籤的「壞學生」充滿體諒(可與最近廣獲好評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對讀)。而她的教學方式靈活有趣,尤其注重誘導學生親身接觸大自然(早前ViuTV電視劇《野人老師》就是談這個),這也預示了西西後來寫出《猿猴志》這本自然之書之原因。此外,本篇還有兩項主題:首先是對異鄉孩子的關懷,故事中那孩子自江南移居香港,他所受的歧視某程度上源自地域——在半自傳式的《候鳥》裏,我們會發現這包含西西自己的童年經歷。其次是對萬物生靈的崇敬,在故事高潮,孩子爬上節果決明樹,凝視昆蟲百態,描寫可謂美不勝收。他在樹上「染上一身蔚麗的斑彩」,輪廓更是耀目動人。這天人合一的「自然之子」形象,將預告西西作品的新方向。(下周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