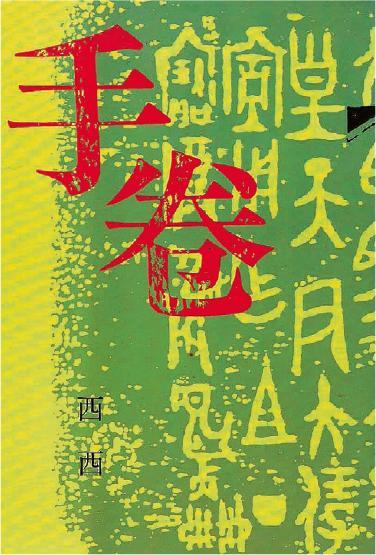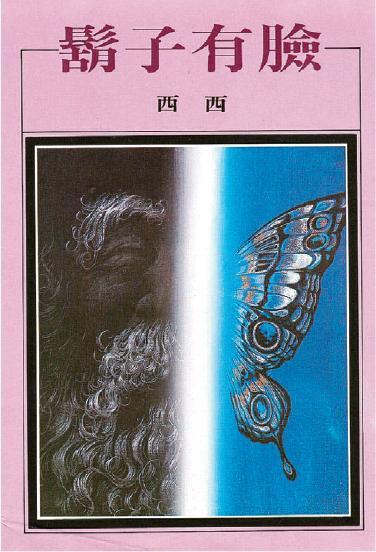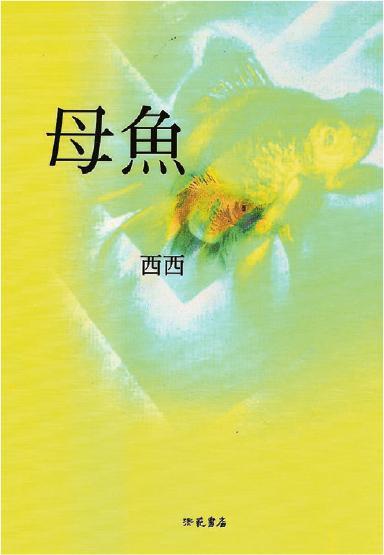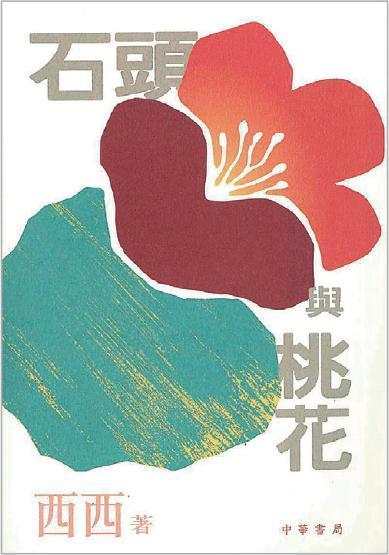【明報專訊】在華文寫作世界裏,西西是最具「全球意識」的其中一位,這可能跟她喜愛世界文學(像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又熱中旅遊有關(如她遊埃及後便寫成〈圖特碑記〉),但也許亦包含個人情感因素。她在《候鳥》提及小時因皮膚黝黑而被誤當南亞人,大抵她因此對其他種族更感親切。她的作品舞台上,站滿來自不同國度的人。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就有一組作品,寫居於本地的異鄉人:〈魚之雕塑〉白描一具遭魚活活吞噬的屍體,原來是游泳逃亡來港的難民,西西運用極反常的陌生化手法,把魚咬人喻為藝術雕塑,令讀者怵目驚心。與之呼應的是〈十字勳章〉,乃本地文學中罕有對啹喀兵的描寫,篇中的德罕大哥,職責正是堵截〈魚之雕塑〉所刻劃的偷渡者。德罕的形象可敬可親,與一般影視作品的南亞人刻板形象大相逕庭。他執法時的克制態度,於今回顧更難免令人刮目相看。其實,無論捕獵者與被捕者,皆同是他鄉客,篇末德罕憶起老家弟妹一幕,分外教人唏噓。
到《手卷》一書,西西進一步擴闊了關懷範圍,加強與現實連繫(即流行語所謂「貼地」),相信是其作品的最佳入門本。延續前作的偷渡者題材,本書有配成一對的〈手卷〉和〈虎地〉。前者模仿傳統畫卷的「移步換景」手法,宏觀地概述了內地偷渡兒童「特赦日」的一天景象。它的手法別出心裁,作者刻意在文句間留下空白:篇末寫新移民的夢想:「移居到他們心目中美麗的、勇敢的、痛苦的、燦爛的、悲壯的、[ ]的、[ ]的新世界。」對比此時,浮城中人於去留之間苦苦掙扎,換了他們會如何填寫這些空白?箇中實在不無悲哀和諷刺。至於後者,題目與「苦地」語音雙關,記述了當年被囚禁於「禁閉營」中的越南船民生活,西西把他們與動植物公園內的美洲虎平行映照,當中對自由的省思,如今讀來也歷久彌新。
集中另一組作品,則記述地球另一端的人們。〈名字阿札利亞〉觸及南非種族隔離爭議,這是1980年代熱門新聞。本篇從香港角度切入遠方,一方面對因戰事失學的孩子表達悲憫,另一方面,那長篇累牘的女子購物清單(甚具高達或桑堤艾格曼電影的况味),也側寫了此地人們囚於豐盛物質的處境。〈這是畢羅索〉則是巴西足球名將薛高的故事。它以球場上諸物件為線索,追溯巴西一代熱愛足球的孩子之成長,並記錄薛高於1986年世界盃巴西對法國「世紀之戰」中射失十二碼的憾事。文中貫串了敘述者模擬與已逝父親共同觀戰的心靈對話———熟悉西西的讀者,當知道這隱含作者自傳,她對足球的熱愛,正來自她擔任業餘球證的父親。作品讀來質樸平淡,但假如讀過1990年世界盃時《明報》的「西西看足球」專欄,便知她視足球為藝術,觀賽角度自成一家。一般人看球,每從消費者角度出發,如遇球員失準則狠狠責罵,有時更不避種族歧視用語。如此看來,〈這是畢羅索〉篇末薛高戰敗回國,家鄉球迷對他的包容體諒,便顯得難能可貴。南美民眾視足球如信仰,相信球迷最近目睹阿根廷球迷於美斯終於捧得世盃後的狂喜表現,也會因這種赤誠而動容。西西鍾情南美球星,把他們與馬奎斯與波赫士等魔幻文學大師等量齊觀,從這個角度看,她筆下的球壇巨匠,也是芸芸像魔術師般的工藝者之一員。
黃子平曾概括《手卷》特色:「西西似乎傾向於認為,灰闌中弱小者的敘述具有較大的可信性,她捕捉、傾聽這些微弱的聲音。」《手卷》一書最受注目的作品,首推運用圖文互涉手法,以馬格利特畫作寓言香港前途問題的《浮城誌異》。西西作品中的本土意識,歷來學者多有討論。但如果把這些談論香港身分的作品,置於上述邊緣者系譜中,則可看出另一番意味。
賦予邊緣者發聲機會
書中另有一組指涉香港問題的作品:〈瑪麗個案〉把一則國際新聞加以發揮:一名居於瑞典的荷蘭籍女孩,向法院提出更易監護人的訴訟。〈肥土鎮灰闌記〉也是公堂審訊戲碼,重寫了元雜劇《灰闌記》(即《舊約聖經》所羅門審斷爭兒案的東方版本),放在肥土鎮(西西宇宙中隱喻香港的虛擬城市)的時空中。孩子馬壽郎站在公堂一隅,本文從他的角度出發,冷眼旁觀包公審案時的兒戲與人治;而當他欲道出真相,偏又無人理會。不少論者均指出兩篇均是香港命運之寓言,尤其在當時中英談判的背景下,香港前途受制於宗主國的意味呼之欲出。但與此同時,兩篇均是以兒童為本位的作品,它們的結尾都不約而同地強調「兒童的意願」。以此觀照,西西作品中的本土意識,不止一種政治話語,相反它有着更宏觀的視野:在她的宇宙裏,種種位處於邊緣者,無論是勞動者、不同種族的人、學校裏的孩子,以至動植物公園裏的生靈,都重新獲賦予發聲的機會,得到平等的對待。正是基於這種哲學,西西對恆常處於權力結構邊陲的肥土鎮,以及它的市民們,才特別着力書寫吧。
西西後期有一本奇特的長篇小說,把這個命題發揮至極致。《我的喬治亞》表面上是她製作玩具屋的紀錄,其中攙雜了有關十八九世紀英國歷史風俗的百科全書式知識。但在這現實敘事層底下,喬治亞屋中的玩偶竟漸漸蘇醒,獲得生命:像女僕馬利安、少主湯姆,他們自行對話辯論,討論女性命運、民主真諦,甚至人偶的自主權問題。這些玩具們,最終竟得以與人類平等對話。它把西方工業革命(也是一場「人工物」的革命)的演變,微縮在玩具屋的微型宇宙裏;不過它的主題,仍是人與人(尤其弱勢者),以至人類與其人工創造物之間的感通。在西西的哲學裏,一貫強調溝通之必要,這從書中最後一位登場、與人偶湯姆少爺展開對話的角色命名便可得之,那是靈媒愛倫——西西在《中國學生周報》年代的筆名,正是張愛倫。
有情的眾生宇宙
隨着西西作品宇宙不斷擴張,人類以外的萬物生靈,漸漸走到舞台中央,與眾多人類角色平起平坐。「萬物自有生命,只消喚醒它們的靈魂」,當年會考範文〈店舖〉曾引述馬奎斯《百年孤寂》的這番話,相信33至46歲的一代還略有印象吧。這種具泛靈論傾向的思想,在西西後期作品佔的位置愈來愈重。
西西是愛動物的人。她早年的散文〈狒狒〉描寫動植物公園那巨大鐵籠內「斜陽柔柔地自樹蔭灑落,照着一名動物飼養員和一頭狒狒,一起坐在一截粗大的樹幹上」,那和諧的畫面教人難忘。也許礙於當年動物權利意識仍處於起步階段,該文對動物園圈養動物的做法未有明確評論,但字裏行間也可體味她對動物的偏愛和悲憫:既然人和動物都脫離不了種種有形無形的樊籠,何不嘗試平等共處?到了《鬍子有臉》裏的〈鳥島〉,青海湖的群鳥成為獨當一面的主角,無論是冰上舞蹈的天鵝、攜手抗敵的魚鷗和棕頭鷗、南歸前依依惜別的斑頭雁,在她筆下均是有情眾生。誠然它較近於博物志,小說筆法只見於首尾兩段「動物研究員」的對話:那些科學家以研究和教育之名義,不惜殘殺動物,製成標本;他們對動物又抱着高高在上的姿態,有時刻意捉弄,甚至把一己價值觀加諸自然法則之上,自作聰明地「主持正義」。西西對此極盡嘲諷之能事,表現出愈來愈明晰的動物權利觀。同一集子中的〈海棠〉,同樣嘲諷了人類對生靈的偏見:啞巴栽了一盆海棠,不過更愛花叢中那條毛毛蟲,但他的朋友眼中卻只有嬌艷花兒值得愛惜,竟自作主張替啞巴把毛蟲打死,教他欲哭無淚。在西西筆下,眾生無論妍媸美醜,一律平等,一般可親。她把對動物之愛,一直灌注在寫作生涯中,於是便有了《猿猴志》,以及遺作《動物嘉年華》。在後者,她再寫了一首狒狒詩,這次肯定地表明了她的願望:「狒狒啊/我多希望有足夠的力氣/把你拔出籠外/回到你生活的故鄉」。
永恆的孩子 宇宙的心靈
輯於《母魚》的〈宇宙奇趣補遺〉,是西西萬物系譜中最奇特的一章。本篇由卡爾維諾《宇宙奇趣錄》改編而成,只是原作的恐龍Qfwfq,在本篇變了垃圾蟲──1970年代港府推行清潔運動時的「吉祥物」。Qfwfq在本篇多次變形,由統治地球的巨龍,絕種後墮落凡間,成為人人喊打的塑膠充氣巨蟲,被焚毀後再回歸大氣,化為星雲。本篇固然是一則關於人類破壞生態的寓言:當局為了宣傳反污染,結果卻創造出尾大不掉的塑膠廢物。但西西的環保思想,並非只從效益主義角度考慮,相反源自她的萬物有靈信仰,是故她以Qfwfq為敘述者講述這個故事。Qfwfq在西西的邊緣者譜系中,可謂「集大成」者,其身分同時包括:非生物、絕種動物,以及人類罪孽的代罪羔羊;而教人捧腹的是,它又偏偏受到眾多邊緣者所擁戴,如拾荒者和被誤解的孩子。在結尾,它那薄薄的膜質體始終未能完全焚燒分解,結果融入永恆星雲之中,當中對人類以宇宙中心自居的反諷,可謂妙到毫顛。
永恆的孩子,宇宙的心靈——西西作品中最重要的兩個原型,在其晚年力作〈星塵〉終於相遇。本篇收錄於她另一本遺作《石頭與桃花》。因星體碰撞,一朵星塵被掃出星群,墜落在小三學生明明家中的晾衣架上。星塵為了充電,由插頭走進明明的電腦內,卻導致全區停電。星塵於是在電腦裏發出聲響,與明明展開對話。對話觸及不少關於宇宙的課題。明明以為星塵是外星「人」,星塵卻否定了這想法:在小說一開始,它的外形已不斷轉化——由紅外線,到牆上的灰黑腳印,到一團漿糊狀、顏色卻詩意得像「幾度夕陽紅」的星雲。它取笑明明:「你以為只有你們這樣的樣子才是樣子。你以為,你們的演化,已經完成了嗎?你們的演化,一億年,最多,我剛才知道,這地球出現,生命的迹象,也不過在四十億年前。對宇宙的歷程來說,小伙子,還說不上是BB。你們說的怪物,其實也是你們一些人的想像。」(引文句子斷續,是因為星塵充電尚未完成。)西西再次質疑「人類本位」的思考模式,指出生命的形式不止一種,人類更不應滿足於現今的進化階段。她藉星塵之口,描述了巨分子雲演化為恆星,超新星爆炸,直至恆星塌縮為黑洞的過程。這朵星塵,正是宇宙本身的擬人化書寫。
〈星塵〉獨特之處,是它在宇宙進化的大敘事背後,暗裏潛伏着點點滴滴的本土小敘事,例如土瓜灣滿街的自由行店舖,還有一位徹夜溫習的小三學生明明——他是《我城》裏阿髮的後裔,40年前阿髮頸上掛着鬧鐘,應付的是「學能測驗」,如今它借屍還魂,成為「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幸好明明未被應試教育消磨了學習興趣,他雖不再讀《哈利波特》等「out了」的課外書,不過也肯翻翻爸爸的小說。他對萬物尚能保持求知慾,認識彩虹和紫外線,懂得詩詞和圍棋,做錯事肯說對不起,志願是當天文學家。在這篇壓卷之作,西西念念不忘始終是教育;而她心目中最理想的文學形象,大抵就是對宇宙懷着永恆好奇的孩子。事實上,無論是明明還是星塵,兩者均是學習者——本篇最前衛之處,是它構想了「星際智能」的自我學習和進化機制:它一面充電,一面在網絡吸收人類文明的知識。在寫作生涯臨近終結之際,西西對未來依然樂觀:她雖勸喻讀者靜心傾聽宇宙浩瀚的聲音,但仍然肯定了人類心靈潛藏的真善美:「我知道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規格,但我不會因此成為莎士比亞;我懂得顏色更多細緻的分別,但我不會有列奥納多、莫奈等人的筆觸,就是那麼一touch,突破了天地的洪荒。這是人類了不起的奧妙。」這該是她對「人工智能會否取代人類」此一命題的答案吧。
本文介紹西西短篇小說之人物群像,讀者若跟這些有趣角色交了朋友,再進入其長篇小說世界也便輕而易舉了。對香港前世今生感興趣的,當然該看《我城》、《美麗大廈》和《飛氈》;若想深入了解西西其人,可看自傳成分較重的《候鳥》、《織巢》和《哀悼乳房》;至於後期《我的喬治亞》和《欽天監》兩本奇書,更是作者對於宇宙萬物更細緻的藍圖。文中提及的的短篇小說集,不少出版於八九十年代(近年另有內地版),也許不太好找,但相信再版可期。此外,十數年前何福仁曾精選「肥土鎮系列」數篇,編為《浮城1.2.3》,願將來有更多類似選本出現。最後,讀者如欲把本文提及的篇章找來一讀,其實尚有一個簡便辦法:就是香港中文大學的網上「香港文學資料庫」(https://hklit.lib.cuhk.edu.hk),不少文章均設免費閱覽和下載,部分更是首次於報刊發表的版本,甚具歷史價值。
西西在〈方格子襯衫〉開頭說:「你選擇了我,我很高興。」她窮畢生精力,創造了一個趣味盎然的文學宇宙。願大家能選擇一把屬於自己的鑰匙,開啟那巧奪天工的玩具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