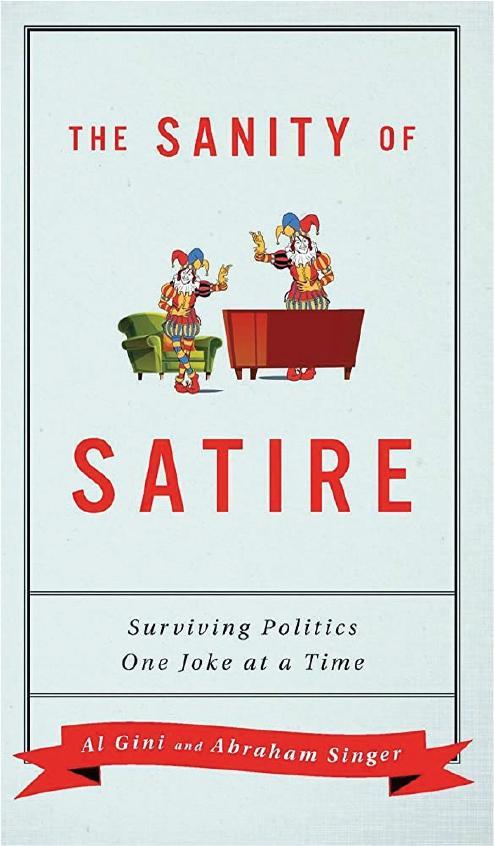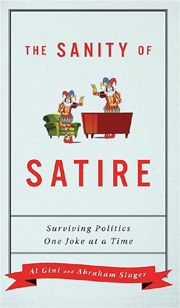【明報專訊】從政治漫畫到諷刺節目,從特朗普氣球到棟篤笑,政治笑話(political humor)或者諷刺(satire)的歷史可謂跟喜劇(comedy)一樣久遠。但又因為過於日常與市井,因而長期備受忽視。諷刺除了令人發笑之外,還有什麼更重要的文化政治角色呢?為何在不同的時空與文化脈絡下,我們都能找到各種諷刺時政的文化現象,彷彿嘲笑政治人物或者現實條件某種普世性的語言,且其變幻莫測的內容特質,往往使其能擺脫強力的政治打壓,像野草一般絕處重生。這牆腳下的不死綠草,為這黑白的世界添上無限生機。所以,為了更深入了解諷刺的歷史和作用,我特地翻閱一本名為The Sanity of Satire的著作,看看Al Gini跟Abraham Singer這兩位作者,如何以文字捕捉諷刺文化背後的政治力量。
所有笑話都是政治性的
基本上,所有事物都是政治性的,因此所有笑話都是政治性的。同一時間,笑話可以牽涉到各種不同的主題或者範疇,以至任何事物都可以成為笑話的內容。一如黃子華或者許冠文的棟篤笑中,小至排隊去廁所,大至社會運動和國際關係,都可以成為笑話的成分。而根據作者所引述,如今歷史學家發現最早的笑話,大概是出自公元前1900年的蘇美人(Sumerian)文化。你不得不佩服古人對於笑話的執著,即使在寫作極其不容易的時代,他們也要用蘆葦稈削成的尖筆,一筆一筆地把楔形文字寫在泥板上,執意要把笑話傳世。
有賴前人對笑話的用心記載,今天的我們才得以欣賞這接近4000年前的笑話:「有一件從古至今從未發生過的事情發生了:一個年輕女子居然沒有在她丈夫的腿上放屁!」放屁的笑話,實在是人類的重要文化遺產。但這個笑話可能過了最佳享用日期太久,以至當我轉述講給內子聽時,只見她一面無奈,再問我笑點在哪裏。笑不出的主因,自然是因為不了解笑話的脈絡,就像我看其他地區的喜劇,也不太把握到那些引得滿堂發笑的笑位。早期蘇美人仍然是女人主導的母系社會,因此女性在婚姻之中享有主導的特權位置,以放屁來宣示主權,想當然不用過問男人。因此這笑話實質上是戲諷當時的不對等,講笑話者通過這玩笑來嘲笑一下當時既有的社會秩序。換句話說,這看似人畜無害的笑話,其實像是幾千年來的無數政治笑話,充滿了對當時傳統既有價值或者現象的不滿,通過顯露其荒謬來批判或申訴一番。
笑話在人類文明的普遍性,當然是因為笑話本質上便是人溝通的方法之一。人的文化與政治,離不開溝通和交換資訊意見,因此阿里士多德才會說,人是政治的動物,因為只有人類才會說話,通過言語來理解和討論信念和價值。但阿里士多德沒顧及笑話,笑話在當中如何扮演着一定的社會政治作用呢?作者借用了政治學者Sammy Basu的講法,探討諷刺的幾個重要目的。
在笑聲中省思 跳出固有框框
首先,笑話鼓勵我們跳出既有的框框,從各種新的可能思考問題,或者在看似天馬行空的想像中,摸索不同觀念或者想法。因為,每每在各人的時空脈絡和文化政治背景之中,各自帶有諸多不同的預設、立場或者對事物的觀感,處理政治議題時往往因循舊路。因此過於不同的想法,往往變得難以想像或者開口。但諷刺則可以游走在可能與不可能之間,通過嘲笑各樣的荒謬時,不自覺地跳出了過去的自限空間。
在這嘲弄的過程,我們得以瞥見自己過去視野的狹隘,在笑聲中發覺個人思考的不足,從而開放自身的世界,包容更多不同的見解。這也跟第二點有關,便是笑話有助化約不同政見或立場的衝突和敵意。畢竟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有時度盡劫波而兄弟在,相逢便一笑泯恩仇好了。通過諷刺,通過笑聲,不同立場者或者都避免了討論講數般嚴肅嚴厲,以至為着面子與認同而大動干戈。笑話像杜汶澤在《低俗喜劇》談的潤滑劑,多少身體或者言語衝突,或者都能在潤滑中化約甚至化解。甚至當面對各種衝突仍然能幽默起來,背後都能形成某種共同體的團結性,那便是在抹去恩仇的笑聲中,認定彼此都是為大局着想,為着大家的福祉而討論甚至爭執,因此無需要走到衝突的地步,開個玩笑大家開心便好了,有事便慢慢說吧。
因此,若整合上述的元素,不難發現笑話或者政治譏諷,為何在民主社會成為空氣般的養分,來到威權世界卻成了無名的禁忌。因為笑話總是嘲弄着當下的社會慣例、既有道德價值或者權勢分子,藉以從言語上帶來權力上的逆轉。譏諷漫畫因而總是挑戰性的,總是不安於室的力量,通過突顯現實荒誕來參與政治改造。雖然笑話終究不能取代政治論述與理性說服的過程,但不會被後者所取代。笑話的門檻低,容易理解和傳播,而且往往好的作品都是擊中制度的要害,使得民眾得以在政治公關或者口號之外,笑着直視現實的荒謬,制度的朽壞,讓政治意識得以飛入尋常百姓家。
因此,高舉民主價值,重視言論與表達自由的地方,自然對於笑話和幽默有着更大的包容土壤。先不論特朗普整個總統任期,成為美國喜劇作家的地獄,君不見歷代幾多個美國總統,幾乎都成了各種漫畫清談的嘲笑對象,可能是關於華盛頓的牙齒有多爛、傑佛遜有多沉溺女色、列根的記性有多差、或者林肯有多像長臂猿之類,這些笑話連我在班中的十來歲美國大學生都能隨意枚舉十個八個。但是在香港,連小熊維尼的恐怖電影也不敢上映,只可以說銀幕上的恐怖,遠遠比不上銀幕下的美麗新世界。幾格博君一粲的漫畫,都會成為政權喊打喊殺的對象。
不難想像,以英語書寫的政治笑話史,自然不會多提華文世界的思考。而在五四之後,許多民國時代的學者也很有系統地引入和討論幽默和諷刺的觀念,且提出許多有趣的觀點。例如老舍在〈談幽默〉一文中,便曾嚴格地區分開幽默和諷刺,他認為「幽默者的心是熱的,諷刺家的心是冷的;因此,諷刺多是破壞的〔……〕一本諷刺的戲劇或小說,必有個道德的目的〔……〕諷刺因道德目的而必須毒辣不留情,幽默則寬泛一些,也就寬泛一些」。可以見到從老舍的分類中,我們上述談的政治笑話應該算是諷刺,而非狹義的幽默。
寬容反諷與中國文化
另一位民國才子林語堂,同樣十分關注幽默與諷刺的討論,在其芸芸作品之中,至為暢銷的一本是《生活的藝術》(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當中對中國文化的想法便借用了相關概念來闡述,「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一直是一個對人生有一種基於明智的脫悟上的『達觀』(detachment)者。這種達觀產生『曠懷』(high-mindedness),它使人帶着寬容的反諷(tolerant irony)度過人生。」有學者認為,這寬容反諷的人生理想,源自林語堂對於幽默和閒適的理解,「幽默」閒適化便是道家精神,而幽默閒適並行不悖,又不期然充滿儒家色彩,兩者相連便帶有中國文化的高尚人格境界。
只是如今,政治諷剌在黃土上成了禁忌,歷史的玩笑總是來得如此的殘酷,一如老舍投湖自盡,林語堂半生飄泊,血色淹沒了時代的迴聲。但無論雨怎麼打,幽默諷刺仍是會開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