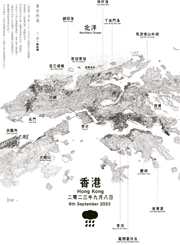【明報專訊】黃大仙民政專員黃智華離任赴京進修,上月底獲建制派社團及地區人士籌辦43席歡送宴,引起建制內的風波,特別是前特首、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他一批再批鋪張浪費,強調要整整風。此後,既有建制派人士想緩頰打圓場,亦有人帶點尷尬地辯護兩句,例如「又唔係大酒店」、「唔駛咁破費」等。我雖然沒研究過香港地區社團及政治,但對這樣的儀式活動不感意外,倒是對有人意外感到意外。
以前泛民人士經常批評或揶揄建制派「蛇齋餅糭」,飲食與香港地區政治一直是分不開,而且很重要,沒有人天真地認為,地區政治只限於開會、選舉及投票。簡單分類,建制派的飲食政治可分成兩層,下層是惠及小市民的派月餅、食蛇羹,上層就像黄智華歡送宴這一類。有人認為,政治變成飲食款待,小恩小惠,非為政之道。我倒覺得這說法太簡化了,我不相信有很多人會如此簡單,有飲有食便出賣自己的政治立場及信念。然而,請客食飯絕對是政治的一環,但要弄清楚這一環卻殊不容易。在泛民的地區政治,「飲食」成分較少,但茶米油鹽衣食住行這些也不會缺,只是跟建制那邊有點不一樣。不過,下一屆區議會到底有多少泛民人士參選?又有多少當選?恐怕前景極為黯淡,我們可以不理泛民這邊了,齊來看建制的政治戲碼吧。
請客食飯 政治一環
政治與飲食,關鍵不是有與沒有,不是場面大小。嚴格來說,不是飲食本身,而是飲食場所,它是地區政治互動的重要場域,即所謂儀式場所。
有人說,地區團體要「擦」地區專員的鞋,我不知內幕,但直覺認為不是重點。歡送不是歡迎,黄先生離任,上京深造一年,他個人大概沒有什麼直接恩惠可以施予地區團體。因此,關鍵不是什麼實質利益交換,而是儀式。梁振英抱怨,儀式太長、背景板沒有作用、精美場刊浪費等。可是,如果從實用角度看,任何儀式也總是冗長與繁複,甚至是浪費,因為儀式不生產什麼實質的東西,只不斷生產嵌入社會關係,特別是關係中的符號意義。
首先,儀式是一場又一場的戲,最重要是人物角色,以及角色間的關係:「地區專員—地區團體人士」,前者代表了「官」,後者是地區精英身分,他們又自稱代表了「民」。既然如今地區建制人士組成的「三會」(分區會、防火會、滅罪會)是重中之重,掌握大權(例如提名區議會候選人),但成員又由官府委任,那麼,儀式裏「官」與「民」的角色,以及他們的關係就變得異常重要。角色離不開場所,這種場所讓眾人演出自己的角色,並展現彼此關係:官員領導有方,官紳民和衷協濟,香港政治前景光輝燦爛。
透過「演」建構政治現實
正因為宴會裏的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人,而是角色,所以嘉賓要在姓名前加「尊貴的」,也要加「金紫荊星章」與「太平紳士」等榮譽勳銜。儀式主要不是反映現實,而是透過演來建構政治現實,當中情未必真,但戲絕不假。地區專員在這種宴會演出,乃至學會扮演自己的角色,實踐出與對手的關係。在另一邊,地區社團的話事人,也需要這種場合來演活自己作為地區鄉紳的角色,展現自己與官的關係,顯露在建制派中的資歷排輩等。甚至很可能,不同地區之間也需要攀比一下,演出比鄰區更好的官民魚水之歡、盛世景象。
這種日常地區政治戲碼一直存在,正如有人指出,10年前黄大仙有另一位民政專員離任時,歡送晚宴規模比黄智華多一倍,為什麼現在大家會看不過眼?我想,大概有幾個原因:
問責不是儀式重要部分
首先,過去有泛民存在,有他們不一樣的政治儀式,甚至是制衡力量,建制派的飲食政治表演,在常人眼中只是地區政治的一部分,如今卻幾乎成了全部。反諷的是,竟然連建制派也有人看不慣了。梁振英說,如果是換屆典禮,新上任的官員應說說未來一年計劃為地區做點什麼。看來,政治歷練極豐富的梁先生,可能層次太高,還是缺乏點地方政治經驗。在建制這一邊,在地區裏,「問責」不是儀式的重要部分,它比較屬於幾乎已被清除的泛民議員。
第二,政府在「完善」地區行政架構時似乎沒有想過,地方政治中的理想角色是如何塑造與扮演。地區專員權力愈來愈大,按原有的儀式邏輯,這類歡送會應該要愈做愈大,才能彰顯他們更重要的領導角色。畢竟,未來地區專員甚至會成為區議會主席。若地區專員不該出現在這類儀式中,那麼地區團體真是一下子不知該如何與他互動了,如何演下去。民青事務局長麥美娟說,寫封感謝信便足夠了,這樣簡單的戲碼,實在不容易演,不足以讓地區團體演出他們獨特的角色(誰不會寫信呢?),以及與權和威愈來愈大的政務官的關係。架構似乎弄好了,但不同角色如何去演?恐怕還沒有編排清楚。
最後也是更麻煩的是,該如何期望政務官這個角色?
政治版圖中如何定位?
政務官在早年的英國殖民系統裏叫官學生(Cadet Officer),有別於殖民地部委任的商界及軍政界精英,他們還沒有什麼工作經驗便考進公務員系統,接受在職培訓,成為管理殖民地的行政官員。早年,靠他們溝通華洋兩界,協助殖民地的秩序統治,後來重點在不同部門之間協調管理,推行政策。他們的權威、經驗及資歷,完全來自官僚系統,並不專長於任何行政體系以外的領域,這就是後來所謂公務員政治中立性的濫觴。
如果現在還是跟從1970年代以來的港英管理主義,這倒是好辦,他們真的只是行政系統中,在港督/特首之下,最頂層的管理人員而已,做得好,的確寫一封感謝信即可。然而,如今在被完善過的地方行政中,他們擔負如此重的角色,在由亂入治之中負責地區安穩,他們該以怎樣的權威之姿面向地區精英及居民呢?建制派有人蕭規曹隨,但上面有人覺得,AO又不是黨自小培養的精英人才,也不是香港親北京陣營中歷練出來,官威不能過大。很明顯,如梁振英這樣資深的國家領導人,可能看不慣這種「水鬼升城隍」的戲碼,看!這小子不過是個有十餘年資歷的AO,他還要去北京深造呢!
但是,他們若還「未夠班」有此等官威,又該把他們放在新香港政治版圖的什麼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