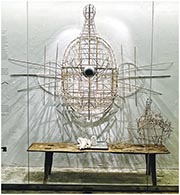【明報專訊】(編按:回應上期江逸天Olivier的〈聆聽空間〉)
O:
讀過你的文章,我這幾天散步時都放下耳機,嘗試聆聽四周的聲音。從灣仔走到中環,我聽到牽着小孩的母親生氣夾雜着憂心的呼喝、遊客拍照時的倒數、煩躁的司機在堵塞的路上響咹,把平常不敢說出口的髒話對空氣發泄。旁觀的我總被這些聲音牽動思緒,暗暗展開評論:既然這麼勞氣,為什麼還要生仔?是一時衝動還是遵從社會規範?明知響咹不會帶來改變,為什麼要製造更多噪音?內心不止的論述,終於讓我亂得靜了下來,發現原來喧鬧的並不是街上的人,而是藏在意識深處、那嚴厲的批判聲。彷彿嫌棄是我的本能,以不安現狀為由,逼迫自己和別人不斷「進步」,任由它發展成批評,蒙蔽雙耳,讓我沒法好好傾聽他人。我為我的自大感到羞愧,也不敢想像我因此忽略了多少生活的細節,這件事是多麼諷刺。
O,對於嚴厲的自我批判,我相信你不會陌生。我很想切實地面對這個課題,希望能夠坦然面對生活,放下執著與期許,安然認清內心。
我這年來喜歡上研究原住民的文化歷史,最近我讀到了日本人類學家森丑之助先生的故事。他是一位非常優秀、生前卻籍籍無名的學者,一生醉心研究台灣原住民和植物學等,成為第一位走遍台灣深山、與眾多不同部落的原住民成為莫逆之交的作家。有趣的是森氏並不是學者出身,他本來是東京某大家族的少爺,沒有上大學,年輕時為脫離家裏的溺愛而逃到台灣,那料他一下船便受到部落儀式所吸引,往後長達30年在山上記錄原住民的風土與生活。森氏並沒有如當時在台日本人般對原住民自鳴優越,而是下苦工學習各部落的語言,他的謙遜讓他能深入原住民的家裏,捕捉很多常人沒法接觸的細節。可是,森氏的作品並沒有為他帶來名譽,反因他的低學歷,更令他的研究被冠上更有地位的學者之名出版。一直要到中年時才熬出頭,得到學院派的承認。但此時卻遇上台灣政府和原住民因過度開發部落土地而陷入僵局,迫使森氏做出人生最重要的抉擇:究竟他應該置身事外,繼續當他的學者專心書寫;或犧牲名譽財產,與當時的政府和商人抗衡,保護那些被政權剝奪家園的朋友?最後,率直的森丑之助選擇把他畢生的研究學以致用提倡建置「蕃人樂園」,可惜經過多番努力還是失敗,心灰意冷讓他選擇自盡,終年四十九。
看完森丑之助的故事,我不禁自問,我究竟有沒有森氏的骨氣能夠義無反顧去追隨自己的初衷?我有他的能耐來抵抗眾人對他的誤解和不屑,擇善固執?也許,當有一天我能夠放下「批判」時,我也可效仿森丑之助,走進心裏那座平靜的深山,學會以真實、原始的語言與自己對話,用純真的眼睛看待世界。
V
註: 有興趣了解森丑之助作品的讀者,可以參考 《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
文:蔡宛蓉 - V,以藝伴活,以字生香。香言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