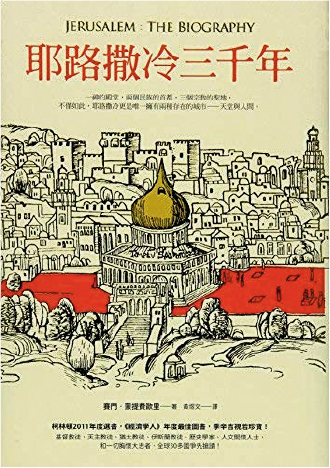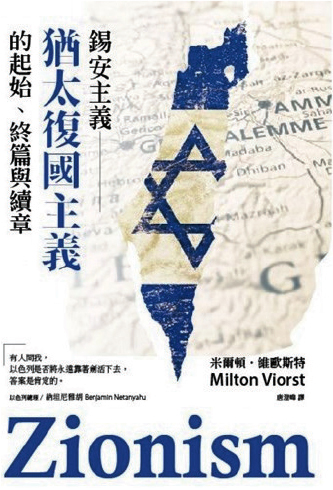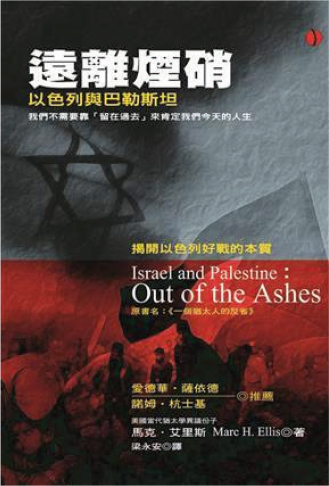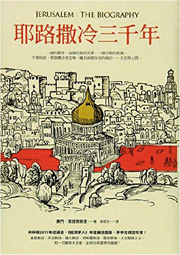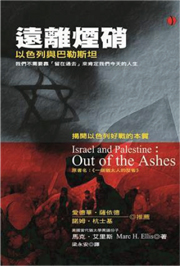【明報專訊】「看來沒有巴勒斯坦人這回事……他們並不存在。」1969年,時任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Golda Meir)曾經拋下這句著名但惹人憤怒的話。這一年,薩伊德(Edward Said)只是一名普通的比較文學教授,尚未出版他的成名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1978),卻毅然決定接下這個批判的使命,用言論證實梅爾夫人的話是錯的。
巴勒斯坦人當然存在,薩伊德本人就是切切實實的巴勒斯坦人。此後多年,薩伊德貫徹地發揮他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影響力,長期為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發聲。他不止著書立說,還身體力行擔任「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的一員,為巴勒斯坦爭取民族自決。只是他生活的地方是美國,而美國則是一個長期親以色列的國家。薩伊德曾言道:「為巴勒斯坦人說話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你得到的回報只是羞辱、謾駡和排斥。」他長期批評美國政界和知識界對巴勒斯坦問題避而不談,西方媒體肆意扭曲伊期蘭的形象,繼而掩飾了有關以巴衝突的真相。
薩伊德對巴勒斯坦的觀點,幾乎都出現在他後期所有著作的字裏行間,散論、文章、訪談乃至專著。簡單來說,他的分析方法承接自其著名的「東方主義」論述:對他者的刻板印象,造成對他者的權力操控和壓迫。例如在《遮蔽的伊斯蘭》(Covering Islam,1981)一書中,直指西方媒體和中東問題專家長期抹黑伊期蘭世界,令西方社會認定穆斯林就是恐怖主義分子。此書出版時尚未發生9‧11事件,而直至過了許多年,經歷過多場反恐戰爭後,國際社會才對美國這種妖魔化他者的政治操作有所知覺。
以巴衝突令人不安地持續多年至今,而向被視為西方社會中的巴勒斯坦良心的薩伊德,亦已逝世20年。我們對巴勒斯坦問題的普遍認識,某程度上仍停留在薩伊德的批判框架裏。我們比較容易看到主流媒體呈現的戰爭暴力,卻未有清楚意識到這些呈現是經過篩選的,背後政治操作亦相當複雜。今天比20年前進步的是,我們現在有大量網絡資訊、影像、即時報道和即時評論,我們亦已知道主流媒體不可盡信。可是,我們也愈來愈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在網上所看到的資訊,對有什麼真相被這資訊之海所遮蔽,卻愈來愈不敏感,就急不及待宣示自己的立場:支持以色列,或支持巴勒斯坦之類。
歷史非「懶人包」能說清
網絡媒體是即時的,散布假消息的可能也很高。現在很多人喜歡在網絡上閱讀(或觀看)「歷史懶人包」文章或影片,作為避免誤判事件的預防針。但網絡資訊永遠不能代替讀書,例如我們要了解以巴衝突的歷史,「懶人包」多數會告訴你可由1967年的「六日戰爭」讀起。這不錯,但不全對,因為歷史是多元決定的,弄清遠因近因,不是三兩千字能說得清。
若你貪婪一點,由歷史上千年的宗教衝突讀起,鑽研一下耶路撒冷史,可讀歷史學家蒙提費歐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的洋洋巨著《耶路撒冷三千年》(Jerusalem:The Biography);或視野拉近一點,先對以色列建國史有所認識,自然也不能繞過錫安主義(Zionism)的歷史脈絡,例如身兼記者和學者的維歐斯特(Milton Viorst)所寫的《錫安主義:從猶太家園到猶太民族主義》(Zionism),即提供了一個以歷史上幾個重要的錫安主義推動者所建構的敘事框架,娓娓道出從猶太復國思想在19世紀開始滋長、到20世紀建國,然後更一直說到當代,並以現任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作為當代錫安主義的最後倡導者。書中指出,錫安主義思想是當代以色列激進右翼的思想根源,也是巴勒斯坦問題愈演愈烈的主因。
猶太作家自省:受害變加害
在權力關係長期不對等的情况下,著書立說者也傾向站在同情巴勒斯坦人的立場,這大有繼承薩伊德的批判精神之意。有人或會很種族主義地說:薩伊德是巴勒斯坦人,當然支持巴勒斯坦。但歷史——尤其是我們能在書本中讀到的思想史和論述史——則告訴我們,對以色列這個「現代國家」反省最深的,不是別人,正是猶太人/以色列人自己。譬如20世紀享負盛名的哲學家鄂蘭(Hannah Arendt)是猶太人,曾在二戰時逃避納粹而移民美國。她一度積極關注猶太復國運動的發展,但後來卻對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猶太國家產生懷疑:這將導致巴勒斯坦土地上的阿拉伯人流離失所,讓他們重演猶太人無家可歸的流徙歷史。這顯然是不道德的。
美籍猶太裔學者馬克.艾里斯(Marc H. Ellis)是猶太史研究權威,其著作《遠離煙硝:以色列與巴勒斯坦》(Israel and Palestine:Out of the Ashes)既有史學研究的深度,卻又以一種對自身民族(猶太人)進行自省的口吻,敘述了一個曾經遭受大屠殺的民族,如今卻帶着哀悼、以被迫害者的身分去迫害着巴勒斯坦人。艾里斯跟薩伊德可謂一鏡兩面,同為巴勒斯坦人發聲,同樣在美國主流社會中遭到批評和打壓。但艾里斯卻不是為自己的民族發聲,而是為其反省。
尚有一本同樣出類拔萃的民族自省之作,是亞瑞.沙維特(Ari Shavit)的《我的應許地:以色列的榮耀與悲劇》(My Promised Land: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Israel)。沙維特是知名記者,曾擔任以色列國防軍傘兵。跟艾里斯的著作不同的是,沙維特先由家族史說起:其曾祖父是多世紀前首批到以色列考察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之一,於是以色列的命運,就跟沙維特家族糾纏在一起。書名以「我的應許地」為題,表現出沙維特對自身民族的熱愛,但書中又狠然批評,猶太復國主義者是如何透過泯滅巴勒斯坦人及其歷史,才能建立起「以色列」這個猶太人之國。沙維特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既愛護和同情,又滿懷忿恨和憂心。
艾里斯跟沙維特筆下的以色列,可說是「以色列人的另一個以色列」。在這個以色列裏,巴勒斯坦終於存在了,並且是作為說明「以色列之所以為以色列」的關鍵而存在的。當然,我們還是需要巴勒斯坦人的主體聲音,拉什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是美籍巴勒斯坦人,跟薩伊德出生於耶路撒冷的背景不同,哈利迪生於紐約,是巴勒斯坦移民的第二代,身分上比薩伊德距離巴勒斯坦本土更遠,但在政治上同樣表現激進,長期批評美國對以巴衝突的立場。2003年薩伊德過世後,哈利迪加入哥倫比亞大學,並擔任現代阿拉伯研究的「薩伊德教授」(Edward Said Professor)一職,大有承繼薩伊德遺志的意味。
在《巴勒斯坦之殤:對抗帝國主義的百年反殖民戰爭》( The Hundred Years' War on Palestine: A History of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Resistance, 1917–2017)一書中,哈利迪完成了薩伊德一直沒有完成、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完整論述建構。他清楚將以色列治下的巴勒斯坦定義為「屯墾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並將歷史上以巴衝突的六個重要時刻定性為「六次宣戰」。哈利迪寫道,西方一直流行將巴勒斯坦貶低為貧瘠落後之地,這些歪曲歷史的論述合理化了這六次具有殖民性質的「宣戰」。哈利迪著作中的敏銳和勇猛絕不遜於薩伊德,而他亦跟薩依德一樣,毫不諱言地抨擊巴勒斯坦領導層的失誤。哈利迪是當前「巴勒斯坦人的巴勒斯坦」最具分量的聲音之一。
今天哈馬斯以殘酷的方式反擊以色列,儘管哈馬斯絕不代表整個巴勒斯坦,也絕不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但看來永久和平已沒機會在可見將來實現。薩伊德曾跟攝影師吉恩.摩爾(Jean Mohr)合作,出版過一本名為《最後的天空之後: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After the Last Sky: Palestinian Lives)的書,以圖文書的方式呈現巴勒斯坦平民的生活。此書名字「最後的天空之後」一句,則是出自巴勒斯坦詩人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的詩歌〈大地正逼近我們〉:
最後的邊疆之後,我們應走到哪裏?/最後的天空之後,鳥兒應飛往哪裏?/最後的一口氣之後,植物應長眠在哪裏?
以巴詩人書寫同一片土地
達爾維什堪稱「巴勒斯坦民族詩人」,地位儼如以色列的殿堂詩人阿米亥(Yehuda Amichai)。有一個說法是這樣的: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戰鬥中,以色列士兵會念着阿米亥的詩上戰場,巴勒斯坦士兵則會念着達爾維什的詩以激勵士氣。戰爭無情,而文學則成了人性的最後一點血脈。這兩位民族身分上敵對的詩人,儘管立場南轅北轍,卻一直惺惺相惜,互相敬重,因為他們兩人所寫的,是同樣一片土地。
達爾維什曾經說過,阿米亥的詩向他提出了挑戰。阿米亥依照自己所需來引述的風景和歷史,是源於達爾維什被摧毁的身分。由此,兩人存在一種競爭:誰擁有這片土地的語言?誰更愛它?誰寫這片土地寫得更出色?看似文學上君子之爭的言論,背後卻恰恰是上述論者筆下的以巴衝突血腥歷史。我們在媒體和論著上看到種種軍事上的鬥爭、現實政治上的鬥爭、還有論述上的鬥爭,但最終還是達爾維什說得好:巴以衝突是「兩種記憶之間的鬥爭」。詩歌不能停止戰爭,但能保存消弭憎恨的希望。
「我不是以色列的情人,我沒有理由成為他們的情人。但我並不憎恨猶太人。」這位曾寫過一首題為〈來自巴勒斯坦的情人〉的長詩的詩人,是如此描述他對敵人的「不憎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