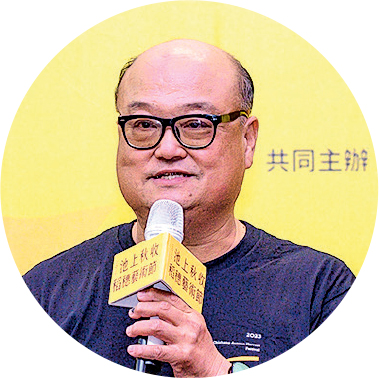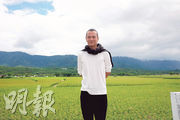【明報專訊】經濟產業與藝術文化,二者從來並非斷裂、獨生的塊莖。就像台灣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今年10月辦到第 15 屆,那稻田上方的天然舞台,貯藏了米業革新、旅遊觀光、身分認同、場域限定表演等繁複的互動鏈路。
池上鄉文化藝術協會理事長兼建興米廠第三代糧商梁正賢,多年前赴日本學習MOA自然農法。他在紀錄片《稻浪上的夢想家》說起那食育、美育、能量療法並行的方法論時,感到不可思議:「我們是學怎麼種有機米,欸,怎麼學插花、學茶道?還有一個MOA美術館、箱根美術館?」耕種如果與生命供給相關,那藝術盤根的應是一種永續發展的人文養分。
相較吸引旅客的顯明利益,藝術節對農業為主的地方意義重大。如MOA自然農法創辦人岡田茂吉在《自然農法》寫:「我確信,真正的真、善、美、歡樂,只有在自然當中才會被發現。」農業不單生產物質糧食,更讓人們透過勞動貼近大自然,達到身心昇華的美學境界。
在台東縣的池上鄉,台灣好基金會選定為「地方創生」(regional revitalization)試點,盼望藉藝術體驗,讓人們重新注視農鄉之美,願意待在日漸少子化、高齡化、青壯年人口外移的鄉村,發展一己事業。基金會在2009年舉辦首屆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把陳冠宇的鋼琴獨奏搬上飽穀田野間,可謂重新發掘了人類與那片土地的感情,使其可被感知、共享。當年《時代》雜誌更把現場相片選為網站上的pictures of the week。
美麗舞台 燙破舞者腳皮
一連兩日的池上藝術節以歌舞媒介為主軸,歷年嘉賓有歌手伍佰、張惠妹、盧廣仲等。當中,4度參演的職業舞團雲門舞集,切切實實地以身體再現了被城市人遺忘的務農精神。10年前,舞團藝術總監林懷民率舞者與池上農民一同收割,跳演稻米四季的《稻禾》,頌揚生命不息輪迴;10年後,接任的鄭宗龍帶來雲層映彩的《天光‧霞》。在表演開場白,他說到這個美麗的舞台其實非常殘酷,晴天,高溫燙破舞者腳皮,陰天,狂風幾近把舞者吹倒,「但我們覺得很幸運,可以稍稍在這幾天裏感受一下,辛勤工作的農夫們是怎麼克服大自然、怎麼在這裏工作」。離開石屎巨廈,藝術在田畝裏劇烈呼吸,律動四肢,像修行一般,煉取人類和天地的共生核心——認知到這層意義,或是討論藝術節怎樣運營等實際面的前提。
農戶對藝術節最直接的支持,大概是讓出那一方稻田區演出場地。《成為池上:地方的可能性》一書描述了那匹比大劇院規格的2500席空間是如何由零打造。劃為舞台的天堂路3塊田,稻米品種統一為「高雄145」,以提早收成並搭築平台。建興米廠向農民提供合作誘因,如碾米優惠、收購價提高等。為了遼闊的舞台風景,當地米廠亦達成共識,演出前不放機械到田裏收割,過後才爭分奪秒二期秋收。
「池上米」這3個字是公共財
10多年過去,田野仍然金燦,燕雀仍然流竄,如此觀演視野有賴當地人苦心維繫。想起《天光 ‧ 霞》公演前一個清晨,記者隨2022年台灣有機米組冠軍唐金滿大哥到大坡池旁繞了個圈,駐足、遠眺,風吹過穀粒又刮過皮膚,他曾有那麼一句話,「要珍惜『池上米』這3個字,這是公共財」。農夫指認的公共財,除了那任人拍攝的1500公頃壯麗水稻景觀,還包括「池上米」品牌盛載的土地情感和身分歸屬。
響亮名堂得來不易。池上米發迹受益於由上而下的政府方針:對外,台灣稻米產業自1940年代開始受國際自由市場衝擊,如1960年代配合美國消耗其剩餘農產品,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對內,台灣長期實施稻米保價收購,嚴重缺乏商品競爭力。種種困境,促使政府1980至1990年間推動食米精緻化政策,研發新品種和適栽區,落實分級檢驗制度等,在質在量帶起了池上米「優良無污染」的名聲。
另一方面,池上米能挺過低價仿冒潮,在整體農業萎縮、務農人口下降的千禧潮勢下維持巨大的耕作面積,仗賴的是一班住民的努力:梁正賢自1986年接手建興米廠,一直心念有機米發展,2000年到MOA大仁實驗農場觀摩,翌年成立「萬安社區有機米產銷班」,歷經波折,終於在2005年得到台灣第一張地理標章「池上米」產地證明,穀價從此拋離平均值,節節上升。
須考取研習證書才可申請的產地標章,不但為農戶換來自足有餘的收入和尊嚴,更為在地人營造了一份集體意識。2004年的電線杆風波便是一例,其時,台電公司應某戶私宅的申請,計劃在伯朗大道往新興村兩公里多的路豎40多支電線杆,被居民以防礙農事等理由攔阻,到最後,完整無障礙的廣遼稻田視野終被合力保住。
池上子弟「薪傳」地方記憶
這種池上人身分的情感連結,以「志工」形態回到藝術節的運作裏頭。《天光‧霞》公演當日,一把把稚嫩卻齊整的「歡迎來到池上」口號響徹會場,順聲音源頭望去,一排排曬得黝黑的孩子緄起黃綠色稻禾頭巾,井然有序地在各路口處指示方向、收取門票、舉座位牌——他們是池上的學生志工。記得從台北飛往池上那晚,大家邊吃黏糯香軟的池上米飯,邊談到觀光業會否影響當地居民時,志工之一池上國中教師詹永名一臉驕傲地說,外人總以為百多名孩子是被學校迫着當志工,但他們真的很喜歡家鄉,真心想觀眾看見池上最好一面。此般熱情非天生內有,由最初主任以活動時數來徵召,到家長學生校友主動報名,志工文化經數載時光浸染,如那九年級女生在《稻浪上的夢想家》坦白,一開始只為時數,後來慢慢喜歡上這工作,「客人很熱情跟我們互動,可以得到別人的稱讚就感覺很開心,有一種成就感」。以優秀的稻作產業為根基,民眾的向內凝聚力促成了地方策辦大型藝術節的可能。
藝術本就是讓人重新知覺生命依歸的媒介,歷史、身分、情感、家園……如同這年藝術節除雲門舞集的《天光‧霞》外,另有由林懷民指導一群零舞蹈根柢的池上子弟,重跳《薪傳》其中一段〈耕種與豐收〉;雖只是數分鐘的簡化版,但看着自薦上場的16個小身影按節拍彎腰播種,奮力完成難度極高的舞目,最後由主持一一念出名字鞠躬謝幕,感動莫名——這場表演彷彿一個承諾:我們,新生代,願意背負起承續地方記憶的責任。
經濟藝術共生值借鑑
以藝術為通路,台灣好基金會於2015年展開駐村藝術家計劃,2017年把米倉改建成池上穀倉藝術館;今年特設展覽「池上‧薪傳」更齊集新舊作品和口述記憶,打造的恰是一套能在鄉地輩輩口耳相傳的「故事」。
在可見未來,如此歸屬感,將迴圈一樣滋養地方或農業或觀光或更多元的產業鏈。台灣好基金會董事長柯文昌這樣總結「地方創生」的大致過程:「鄉鎮的發展,先要有地方經濟做底,因為賺錢才能夠令年輕人來,賺了錢之後一定需要一點藝文,讓人感覺到這是很好住的一個地方。」經濟與藝術互為深耕運行的池上模式固然不可複製,然而,二者根本上的互通值得借鑑,由企業成立的基金會擔當集資、統籌角色,似乎也不失為一個可持續方向。10多年過去,農夫和藝術家作業細水長流,池上和各鄉鎮的路還需繼續走下去。
池上觀光藝文活動回顧
1997年:伯朗咖啡廣告在池上稻田取景,「伯朗大道」掀起熱潮
2009 年:首屆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邀來陳冠宇獨奏鋼琴
2013年:金城武在「伯朗大道」上一棵茄苳樹拍攝航空公司廣告,「金城武樹」帶動觀光人潮
雲門舞集林懷民啟發自池上稻田的《稻禾》在藝術節首演
2015年:首名池上駐村藝術家蔣勳留下了《池上日記》、《池上印象》等書畫作品
2017年:池上穀倉藝術館開幕
2023 年:池上穀倉藝術館策劃特展「池上‧薪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