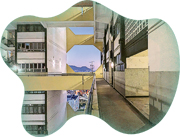【明報專訊】在以往的「去埋呢度先」之旅,不少以看海作結,維港兩岸風景彷彿就是香港的身分象徵——但這次與從柏林回來的Cherry站在祖堯邨停車場,眼底收不盡是貨櫃碼頭的壯觀,也許是「真係好香港」景色之中,更貼地的一個模樣。屋邨高踞山上,Cherry跟很多人一樣,常常坐車經過看到,但總感覺與貨櫃碼頭是截然劃分的這邊與那邊,於是我們就從邨裏走到碼頭,用腳步組織記憶裏模糊的城市脈絡。在路上,任建築師的Cherry憑她的觸覺,也帶給我們很多發現。
簡介:《香港散步學》、《城市散步學》作者黃宇軒每次約一位即將離開這座城市的香港人,了解其性情、喜好,設計一趟旅程,做幾粒鐘朋友、情留香港半天。「我一直覺得,我們每一個人到了這年代,不論是否別離,都似在跟香港進行一場漫長的告別。如果離開前,有許多地方想去埋先,一直去一直去,會否永不離開?」
日期:2023年11月18日
行程:祖堯坊→啟敬樓→荔景站→貨櫃碼頭
初嘗共同探索之樂/文˙ 黃宇軒
第十一回,我約了Cherry。她跟我有幾個共同朋友,好像過去5、6年來都有模糊印象,Cherry是定居在柏林的香港人,朋友到訪該城市時,對她引領的散步讚不絕口。今年初在社交媒體分享第二回「去埋呢度先」的汀九之行時,我多次用上浪漫二字,說香港這座城市也可以很浪漫,Cherry那時第一次聯絡我,第一句話就是,「那真的很浪漫」。
相距半年後,她再度回港,我們終於成功相約一行。見面時她也說同一句話,在城市走來走去,作為一件浪漫的事,在她生活的他方中幾近是常識,是大家都認同的。
用心領會眼前美景
回看年初的對話,那時Cherry說她特別掛念「建在坡道上、多層次的城市環境」。這次我跟她傾「去埋邊度先」時,她提到依山而建的祖堯邨一帶,我就想,Cherry真是始終如一的人!過去十回,我都沒去過全然陌生的地帶,這回選了祖堯邨及通往貨櫃碼頭的路後,我跟Cherry說,一起去我們都從沒踏足過的香港,是這欄目未試過的,這回少了我「帶路」的意味,多了共同探索之樂。
完成這次旅程後,Cherry跟我分享Alain de Botton的The Art of Travel一書,作者提及要在自己的家找到刺激和新鮮感,全然跟心態相關,她又分享非常美麗的一段,「單單張開雙眼我們就能充分地看見美麗,但這種美麗可以在我們的記憶存活多久,就視乎我們有多存心領會」。如果要給她送一份道別禮物,我會想起創辦Alain de Botton的School of Life,其出版的一系列書中,有一本叫《如何在城市生活》(How to Live in the City),討論如何跟一座城市建立親密關係,我想Cherry會很喜歡的。
………………………………………
當年最高公屋 有八角形標記/文˙ 曾曉玲
第一次從荔景站走到祖堯邨,就是一個「跨過心理關口」的體驗——你必須相信眼前不相連的兩個地方,真的可憑雙腿到達。只要從A1出口走到荔景山路對面,找到社區會堂旁一條小路的短樓梯,就能輕易攀上高一層的敬祖路,其實這個山頭層層而上輪廊清楚,並不難懂,亦沒想像中「隔涉」。
午後走進邨內商場「祖堯坊」,會感受到它像個房協「示範屋邨」,樑柱上貼着細拍邨中樓宇及空間設計的攝影作品,中庭休憩桌椅以繽紛插畫裝飾,小孩在陽光下踩着滑板玩樂。Cherry抬頭看了看,說撐起上層通道的三角樑柱有心思,還特意與主體之間隔開一點以突出其形態;看看用料,如圍欄用上玻璃,應該是商場經歷翻新的變化,則稍顯與原有設計格格不入,她補充這在政府設施常見,方便清潔保養。
一睹破世界紀錄建築物
繞到露天停車場,宛如一個從商場延伸出去的觀景台,事實上也是祖堯邨一個攝影勝地,可眺望貨櫃碼頭如巨獸集結的吊機群,以及青葵公路上不息的車流,呈現鮮活的城市脈博。在荃灣長大的Cherry說乘地鐵時會見到這片風景,她一直很喜歡。Sampson提到認識幾個英國建築師朋友,曾興奮地向他介紹旁邊的亞洲貨櫃物流中心,是座破世界紀錄的建築(健力士世界紀錄為largest industrial building,物流中心官網稱為「全球最大多層式貨運處理中心」),Cherry亦從教授建築的朋友口中聽說過大樓的厲害,會與意大利Turin的Fiat舊汽車工廠(Lingotto factory)比較,裏面的大型迴旋坡道最讓建築師着迷。
城市埋藏許多值得留意的角落,Cherry自2015年起在柏林生活,也會帶來訪的朋友四處走走,探索沒記在地圖上的地方。她說在當地散步是平常事,同意Sampson提倡散步說得浪漫,「可能在香港的人會覺得你很奇怪,但在柏林,那真的是個浪漫舉動,跟一個朋友相識或約會,都會問shall we have a walk?」她反思過是不是又得歸咎香港的消費文化,「然而我又不想完全妖魔化香港的商業空間,因為穿插在商場之中也是特別的體驗,外國沒有這些重重層次,身在其中一樣可以當作散步」。
迷戀跟山勢有關之地
離開商場後,我們這天還幸運地有機會進入邨內標誌建築啟敬樓。在1976至1981年落成的祖堯邨共9座樓,其中38層、1981年建成的啟敬樓是當年最高公屋,中間通道直排的大八角形已成為其標記。外面離遠看是有趣,人在裏面、站在八角形框前往外看,則頗為震撼,每個巨框都為我們精挑外頭一幅景像,定格框內讓人觀賞。
每次Cherry回港,都會好好看一眼這個她視為根的地方,「今年4月回來,我到半山走走,荷李活道、山道、第一街、第二街、正街……我覺得所有跟山勢有關的地方都是特別的,因為柏林是一個很平的城市,周圍都沒有山。我會拍下來把這些留住,還記得在摩羅街拍一個地盤,工人在有蓋位置放了些花盆,變作他們的臨時花園」。在外地生活多年的她,少不免有過迷失時候,「剛開始時想成為當地人,久了以後又會發現並不會變得跟他們一樣」,散步於是在這過程中別具意義,「我在柏林會這樣做,因為它對於我來說一開始是個新的城市,所以周圍發掘,或者是我需要不斷去證明這個城市是個很有趣的地方,它是豐富的,能讓我留下生活。其實跟香港一樣,當討論哪裏要重建、哪裏要保留,(理解和感受)這些討論會令我開始感覺到,我屬於那個地方,是跟城市互動和建立連結的過程,令你對她產生一點感情,所以是一件浪漫的事。我不想說什麼公民覺醒之類宏大的話,但我就是這樣去參與在這個城市之中」。
步出啟敬樓,在接駁樓宇之間的電梯天橋上,能看到石坡與車路;乘電梯再上,往下看石坡,立時在視覺上顯得更加高陡,這何嘗又不是與維港、碼頭一樣「很香港」的樣貌?「很多人會說柏林是個come and go的城市,很多人來幾年就會走,但我有時覺得不是城市放在那裏,你就會喜歡它,而是你怎樣去定義喜歡和不喜歡,自己是不是可以有方法喜歡一個城市?」對於香港亦是如此,她談到Art of Travel一書,「有個章節說當你離開了日常很習慣的地方,回來時會用更新鮮的視角去看它」。
陣陣車聲「像海浪聲」
後來當然,Cherry找到自己了,現在她希望能夠將兩地吸收到的養分逐漸結合,用於社區,同時亦會跟柏林朋友述說香港是怎樣的。這幾年我們討論往外地生活,或許多着眼政治、社會情况,與各國接收香港移民的政策,然而早在外國開拓新嘗試的Cherry卻提醒我們,香港本身有她獨特的城市身分,「在柏林的朋友會覺得香港是個大都會」,她也會不斷認識自己的家鄉充當解說的角色。
這天尾聲,我們解鎖心中一個既定印象,山上的祖堯邨與海邊的貨櫃碼頭,並不是截然分割開來的,走走就知道了。回到荔景站橫跨天橋,我們走在碼頭邊陲的行人路上,迎面零星有放工走向港鐵站的人,頭頂被龐大高架路覆蓋,陣陣車聲迴響,敏銳的Cherry形容得特別,「聽上去像海浪聲」。潮起潮落,Sampson憶起10年前的碼頭罷工,人們怎樣走着這條路,一步步認識這陌生一角原來與自己生活息息相關。達陣已天黑,我們就此回頭,留待下次一路往前探索,便是另一段旅程了。
【我的。私藏】
地鐵廣播聲
「下一站係」、「請勿靠近車門」、「嘟嘟嘟嘟」……「對我來說這是城市中很多人會聽見的聲音,要待久了才感覺到這種在地的熟悉感。假如有一天人聲換了、廣播改了,大家就會感到突兀。對遊客來說,去一個地方第一次聽到廣播,我的經歷是聽不入耳,或當作是white noise;直到久而久之在某一天聽得夠多,便變成一個指標,告訴你對這個地方有多熟悉,例如聽到柏林subway的關門聲,也會令我覺得『回到柏林了』;每次回港在地鐵聽到,就會知道已身處另一個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