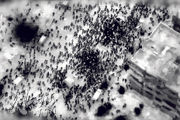【明報專訊】Taylor Swift何許人也?報載新加坡政府不惜每場補貼300萬美元公帑,搶去其演唱會東南亞獨家主辦權,泰國首相賽塔說早知星洲如此進取,他便開價5億泰銖云云。不少香港人(包括官員)此時才如夢初醒,赫然發現有這一顆巨星,當鄰國紛紛招手,此地卻懵然走寶。有人仰天長嘆:香港的國際都會地位又降一級了──從「國際娛樂視野」角度來看,確然如此。曾幾何時,米高積遜、麥當娜、大衛寶兒、佐治童子都是家喻戶曉的名字,連《香港早晨》也特闢環節倒數英美大碟榜,還在念小學的筆者因而認識了「皇后樂隊」、「警察樂隊」和「威猛樂隊」(譯名如此有型,難怪令小孩自此入坑迷上搖滾)。這些港式譯名,正好反映當時歐美音樂何其普及,而現在Taylor Swift卻仍然只是Taylor Swift。
這場茶杯裏的風波,Taylor讀到大概一笑置之;不過這位《時代周刊》年度風雲人物此際身陷政治漩渦,成為彼岸報章頭條人物。事緣她在上屆美國大選力撐拜登,自此成為特朗普擁躉的眼中釘。上月超級碗決賽,她專程入場支持男友Travis Kelce(美式足球明星),全球媒體一早嚴陣以待,直播賽後二人世紀一吻;但由於兩人都支持民主黨,一種「深層國家」式陰謀論竟在廣大右翼群眾中滋生,認為這場童話式戀情根本由五角大樓一手策劃,連Kelce所屬的肯薩斯城酋長奪冠也是造馬,目的是締造一場挺拜登大騷。
網路時代的大娛樂家
全球樂壇久無超級巨星,Taylor Swift如何躍升為當今世界首席歌手?這兩件事剛好說明答案。一方面她正邁向演藝事業頂峰,但單憑entertainer身分並不足以構成如此影響力;與此同時,其政治取態日益鮮明,反映她致力踏上嚴肅的singer-songwriter之路。她的崛起,正是這兩道冉冉上升的軌迹交匯之結果。
先說她的商業成就。不少評論談及其巡唱帶來的經濟效應,即所謂Swiftonomics。演唱產業發展經年,何以Taylor一枝獨秀?簡言之是她的粉絲特別忠心,往往穿州過省一路追隨。當某些破敗小鎮有幸獲選其中一站,霎時間大批歌迷湧入,酒店餐廳連連爆滿,泡沫便吹起。對於此番狂熱,即使外國也有不少「中年大叔」樂迷大惑不解,Reddit討論區便有大量Why Taylor Swift so popular帖子,引來不少Swifties(其歌迷群體䁥稱)義正辭嚴地解答。粉絲最常掛在口邊的,是她的歌relatable(譯「帶來共鳴」還不夠貼切,更準確是「與自己有關」)。更有長篇大論讚美她勤於與歌迷建立parasocial relationships(擬社會關係),說穿了,就是網民單向地認為自己與網上名人交了朋友;例子有她定期抽出幸運歌迷,在新歌推出前邀到其大宅率先欣賞;又如作品隱藏「彩蛋」,像在唱片歌詞冊、MV、網帖等埋下信息。粉絲不自覺地感到與偶像的獨特聯結,聽偶像唱失戀情歌,就仿如閨密私語;Swifties之間也因而產生社群歸屬感,像英美不少大學都開設「Taylor Swift學會」。
本地讀者不難發現:這不就和近年MIRROR熱潮同出一轍嗎?粉絲文化由來已久,不過社交媒體卻促使偶像步下神壇,與歌迷建立似近還遠的虛擬關係。現在歌手不時網上直播,更發展出種種圈內術語笑話,溝通方式有如秘密會社,像Serrini便是經營虛擬社群的能手。若說Taylor的商業成就有何彪炳之處,該就是她把網路世代的心理經濟學發揮盡致。
「覺醒」世代的文化旗手
再說她的政治取態。Netflix有她的紀錄片《美國小姐》(Miss Americana),活脫脫就是其社會宣言:她自言曾經厭食,後來下定決心不再臣服女性定型;曾因被性騷擾上庭作證,因而體會司法程序對性侵受害者的二次傷害;2018年中期選舉時毅然表態,原因正是她家鄉田納西州的共和黨女候選人竟公然反對有關女性平權、打擊家暴和保障LGBTQ的立法。她在網上呼籲年輕人登記做選民,卻阻止不了該名候選人當選。影片紀錄了Taylor創作Only The Young一曲的過程,這可說是她最單刀直入的一首抗議歌曲(And the big bad man and his big bad clan. Their hands are stained with red.)。
坦白說,Taylor這一代雖以覺醒(woke)自居,其激進程度與五六十年代活在麥卡錫白色恐怖中、還被白人種族主義者丟石頭的老派左翼歌手(像Pete Seeger)相比,實在不可同日而語,畢竟左翼論述已成荷里活主流,對拉攏年輕群眾百利而無一害。更諷刺的,是Taylor本身的金髮白種鄰家女孩形象,加上與美式足球明星的戀情,本來就是美國神話的化身;即使她「左」,也是最人畜無害的那種左吧,表面的政治表態也許不代表什麼。
不過,她出道的鄉謠音樂圈,正是南方保守價值重鎮。若她不挺民主黨,特朗普想必加以禮聘為他助選,情形就如列根當年想在「工人皇帝」史賓斯汀(Bruce Springsteen)身上打主意那樣。聰明若Taylor,必然深知箇中吊詭,《美國小姐》的主題曲Miss Americana & The Heartbreak Prince,一如史賓斯汀的Born In The USA,是打着紅旗反紅旗之作。它挪用了高中啦啦隊女生的傳統角色:女孩扯破了禮服,在紀錄敗績的計分板下亡命,要把這座城塗上一片藍──稍為關心政治的樂迷,一聽便知藍色代表民主黨,這首歌分明是關於一場選舉的隱喻。難怪《時代周刊》把她比作卜戴倫和保羅麥卡尼,因為她的確能運用詩的語言,藉歌曲帶出故事。
破天荒的女唱作巨星
且回歸流行音樂史理解Taylor Swift現象。無論其作品是否過譽,無可否認,這是史上首次由女性高踞流行之巔──想當年娜姐還是屈居MJ之下。更重要的,是Taylor以女唱作人身分,執全球樂壇之牛耳,絕對是足以載入史冊的成就。從披頭四、卜戴倫到U2、Radiohead,所謂的偉大流行/搖滾樂創作者傳統,一直由男性主導;女歌手如Aretha Franklin、麥當娜到Adele,總是被視為演繹者。其實她們很多也能寫歌,像麥當娜成名後,便漸多參與創作,不過其驚世駭俗的表演太深入民心,才令大眾忽略作者身分;後來的Lady Gaga和Lana Del Rey情形也類似。固然也有傳奇女唱作人,像Carole King、Joni Mitchell、Patti Smith和Kate Bush,但未成主流(像後者,相信不少聽眾是因《怪奇物語》播紅Running Up That Hill才認識),幸好近年如Lorde和Billie Eilish已扭轉局面。當然Taylor Swift走紅後的作品往往與其他音樂人合寫,因此有人(像Blur的Damon Albarn)質疑其真正參與程度。不過從紀錄片所見,她似乎確具出口成詞的功力,也能自彈自唱,大抵曲詞多數出自其手筆,編曲則較倚仗他人。
縱觀歷史,能登上殿堂的音樂人,往往不斷昇華求變,最經典例子莫過於披頭四,1964年還在唱熱熱鬧鬧的Can’t Buy Me Love,三年後已埋首創作迷幻玄奧的A Day In The Life了。Taylor應該明白這一點,她早年演唱流行鄉謠(鄉村味道委實不強),搖身一變電音天后,主要為了取悅大眾。然而,自她因版權糾紛憤而把昔日唱片重新灌錄,到COVID封城期間閉關創作,於毫無宣傳下接連推出轉趨沉鬱的兩張大碟Folklore和Evermore,都顯示她掌握創作主導權的決心。若套用披頭四的比喻,此際她大概處於前者1965至1966年間的轉型關口,正欲蓄勢待發。
且聽Folklore唱片,其過半歌曲與另類樂隊The National結他手Aaron Dessner合寫,瀰漫後者的招牌低迴琴聲和空靈電音節奏。據Taylor表示,封城期間她看了大量老電影,種種意象在腦海盤旋不去:「沉沒的戰艦,舞廳高懸的鏡球,散發歷史氣味的毛衣,浸着陽光的八月」,詩化句子不時閃現歌詞,各式魅幻形象也時隱時沒,像苦苦掙扎的酗酒者(This Is Me Trying)、遭家暴的童年玩伴(Seven)、二戰時在所羅門群島奮戰的祖父亡靈(Epiphany)。The Last Great American Dynasty更是《大亨小傳》式諷刺浮華的巨構:昔日名媛被豪門幽禁,受盡流言蜚語,終成瘋婦幽靈不散,曲終時,其身影更與剛購入大宅的歌者重疊。作者大概旨在自嘲娛樂圈經歷,但又一首開宗明義以美國命名的歌,當中可有史賓斯汀式的史詩野心?唱片末的隱藏曲目是The Lakes,牛津大學莎劇教授Jonathan Bate在《泰晤士報》撰文擊節讚賞,指出Taylor機智地把尋訪詩人華滋渥斯(William Wordsworth)英國湖區故居之旅,與版權糾紛時期的創作低潮加以對照。歌詞說:「帶我到詩人爭相赴死的湖區吧,我將攜同繆思前往」,這看來怎麼也像一位躊躇滿志的詩人自許。
走筆至此,不禁想起此地女創作歌手風氣也盛,不少也具詩人氣質。Taylor來港演唱告吹,樂迷倒不如轉為本地薑捧捧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