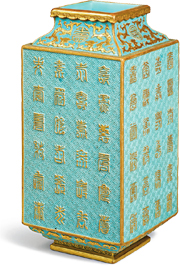【明報專訊】德國科隆是歐洲音樂重鎮:上世紀自二戰後至1970年代,一時多少怪傑在當地設總部的西德廣播公司將電子作曲技法發揚光大;古典音樂迷都會知道成立於1827年的居策尼茲樂團(Gürzenich-Orchester),德奧浪漫樂派巨匠,如布拉姆斯、理查.史特勞斯、馬勒等,都曾託其首演重要管弦樂曲。樂團當然樂於善用自己獨特的歷史背景配以所在城市的文化氣息來設計節目。4月中一連三場的音樂會「Ecstasy」,在樂團駐地、設2000席的科隆音樂大廳舉行,請來在歐美炙手可熱的港產指揮家陳以琳執棒,3天節目大致一樣,唯獨是首天下半場加演兩首電子音樂,包括法國印象派宗師拉威爾《F大調弦樂四重奏》第三樂章的電子音樂改編版。
去聽最後一場原因有三。首先,從倫敦即日來回科隆,風塵僕僕,只為一睹陳以琳的風采,而首天加演節目由樂團樂師組成的弦樂四重奏和一德籍電音藝術家擔綱,陳氏並不參與其中。再者,自己並不如科隆市民般成長於古典及先鋒交纏的音樂氛圍中,我對古典樂的新詮坦白說興趣寥寥,當天在音樂會前,另到西德廣播公司朝聖,已於願足矣。最後則是很想知道連續三場下來陳以琳和樂團的表現。
協奏曲不止分庭抗禮
音樂會以俄國作曲家普羅哥菲夫(Sergei Prokofiev)的《C大調第三鋼琴協奏曲》開始,演奏者是去年秋天曾在香港大會堂舉行獨奏會的英國鋼琴家葛羅夫納(Benjamin Grosvenor)。陳以琳多變的指揮動作使這首輝煌的協奏曲特別賞心悅目。在一開始木管聲部如歌般的引子,她揮舞的範圍其實很小,但靠微微彎身、前傾,使得頓挫仍明顯。然後是普氏在這曲著名的對比寫法(在全曲多次運用),樂團忽爾提速,引入清脆飛快的鋼琴聲部。普氏以挑戰傳統音樂調性的新古典主義聞名於世,筆下和聲新穎,對位複雜,陳以琳的處理方法也很直接,就是時而將一拍化簡為繁,清楚額外揮出分拍來指示樂隊穿梭不同織體。如果當晚棒下的是她自己任首席指揮的比利時安特衛普交響樂團(兩位香港管弦樂團前音樂總監迪華特和梵志登也曾執掌此團),或許會有其他調度方法。不過,這正是作客其他樂團的挑戰,亦不難解決。
單是4月份,葛羅夫納已把此曲先後跟兩個樂團彈了足足4遍。顯然對這首協奏曲駕輕就熟。他演奏不屬大開大合類型,有時還有些新意,卻令人聽出陳以琳對細節的執著。幻變的第二樂章有5個速度、聲效都很不同的變奏,第四變奏是鋼琴與樂團的對答。葛氏接連彈出了幾個尾音出奇地響的上行琶音,乍聽有點特別。這音型在接下的樂隊段落重現時,陳以琳棒下的銅管聲部竟能以同樣的音響回敬。如此就不單是鋼琴家臨場神來一筆,而是精心鋪排過的設計。協奏曲拉丁原文原有競賽意,最大特色為樂隊不是附庸伴奏,而是跟獨奏樂器分庭抗禮。話雖如此,在炫技和厚重段落外,好的指揮能在不顯眼處帶出樂團和獨奏聲部的微妙關係。
以音符擊破刻板印象
其實是第一次現場觀看陳以琳的演出。有樂評說她身形嬌小,實則她雖不像上世紀演繹華格勒(Richard Wagner)的權威滕施泰特(Klaus Tennstedt)般六呎昂藏,但個子談不上小。在今時今日看來,以刻板印象形容任何性別的指揮或音樂家都已過時。甚至早在2016年,她已經在英國《衛報》撰文說不想性別和女性氣質成為自己的助力。這些年來,取文字而代之的是以音樂擊破刻板印象,本年3月她首次指揮頂尖的紐約愛樂,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亦再次肯定這「讓音樂說話」的力量。
說起華格勒,皆因當晚第二首選曲就是其歌劇《崔斯坦與伊索德》之〈前奏曲〉與終曲〈愛之死〉連奏。陳以琳全程無用指揮棒,任盡十指各自發射細微至極的指示予樂師,因為這組音樂有著名的「崔斯坦和弦」,代表渴望,時常出現綿長漸強,其中各樂器聲部不斷出出入入,須靠指揮仔細堆砌。只見她手掌向下,十指微張,指示弦樂聲部交替奏出上行跑句,不同管樂期間聽令而入;在悲壯的終曲,她雙手用力握拳往身前聚攏,持續激發樂團的音響。這些都是唯有不用指揮棒才能做到的身體動作。
捨棄指揮棒也絕不是出於所謂陰柔的考量,在音樂早段,大提琴首席竟已疑奏斷弦線。如樂團首席出事,常見應對方法是直接跟旁邊同是拉小提琴的第一副首席對調樂器。但龐大的大提琴無法在擠迫的樂池如此擾攘,故這位首席不得不即時悄悄回後台處理。陳以琳和樂師絲毫不受影響,想當觀眾(至少我)亦如是,直至有一下驀地見大提琴首席在大家全然不覺中已又悄悄穿過七八排弦樂同事,回到樂團拉奏,才發現陳以琳所散發的音樂氛圍有如此令人完全只專注在音樂間之力量。
色彩斑斕的海外詩篇
港產志士能人在彼岸發光,毋須一味嗟嘆甚至奚落香港留不住人才,但其中一個在外發展的不能忽視的吸引之處是能演奏一些在香港未必受太大歡迎的作品。在第19屆大阪國際音樂比賽鋼琴聯彈組別獲得第一名的鋼琴家梁梓俊是我好友,一同在港大音樂系念本科期間,他已積極鑽研史克里亞賓(Alexander Scriabin)的音樂,現於倫敦發展,經常演奏這俄國作曲家的作品。在港辦音樂會,市場考量卻非常實際,劍走偏鋒的選曲往往不易吸引觀眾。
史克里亞賓《狂喜之詩》是陳以琳音樂會的尾曲。6個敲擊樂手、兩部豎琴和額外的圓號手進場。這排山倒海之作極考驗指揮的情緒調整,史氏譜下的狂喜,除以難以捉摸的全音階和不盡和諧的增五度音程為特色,還對比極烈,多次在狂風掃落葉後突然轉入平和樂段,例如樂團在齊奏爆發後緊接豎琴輕柔的刮奏。能觀察到陳以琳之最大個人風格,是擅長處理複雜層次,引出織體豐富的音響。當小號組奏出堅定的動機時,卻需弦樂細細撥弦;在最後一次歡騰起來時,8部圓號璀璨齊響,更有恢宏的管風琴,但仍然清楚聽到小小鐵片琴的利落音色,從中可知陳以琳的調度功力和在幾天排練、演奏下來所費的心神。
與陳以琳素無私交,但六度相隔理論使然,輾轉終聯絡上,得她親談是次音樂會以至近10年與世界一流樂團和音樂家合作的種種,還透露正安排新樂季回港演出。之於當晚,她難擇特別一瞬,覺得在華格勒的音符中塑造聲音是一大樂事,見證樂團每日埋首和開展出史克里亞賓的音樂(當數那曲最振奮和強大的尾段,陳以琳言)亦是非常值得。而回憶年初她在母校美國麻省史密斯學院與年輕藝術愛好者見面交流,續問及想對香港青年音樂人說的話,她寄語:「To have the courage to pursue what makes your heart beat and gets you fired up! Embrace and hold on to who you are, write your story, and forge your own path.(勇於追求令你心動熾熱的事!擁抱並堅持做自己,寫你的故事,開拓屬於你自己的道路。)」
回想以英語進行的文字訪問,走筆到此,縱無蒙古族台灣作家席慕蓉詩中「雖然已經不能用母語來訴說」的無奈意,倒有歌舒詠《一個美國人在巴黎》的一絲鄉愁。
俄國作品算是陳以琳熟悉的曲目,2014年在倫敦弗里克國際指揮大賽,她即以「俄國五人組」成員林姆斯基—高沙可夫(Rimsky-Korsakov)的《天方夜譚》奪魁,從此蜚聲國際。可惜上次其原定在港與香港管弦樂團的實體演出因疫情而告吹,不然肯定會選奏3月和紐約愛樂演奏過的此曲。科隆的這場音樂會入座率極高,歐洲觀眾一如既往在完結時起立歡呼,如雷貫耳。不肯定她有否聽見我用廣東話大喊的「好嘢」,但毋庸置疑終有一天當她在港揮舞起其成名作《天方夜譚》和眾多憑其識見所帶來的音樂後,台下的廣東話喝彩聲會遠不止一個。
作者簡介:英國牛津大學音樂博士生,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碩士演奏課程導師,旅居倫敦,深信一筆在手可穿越時間和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