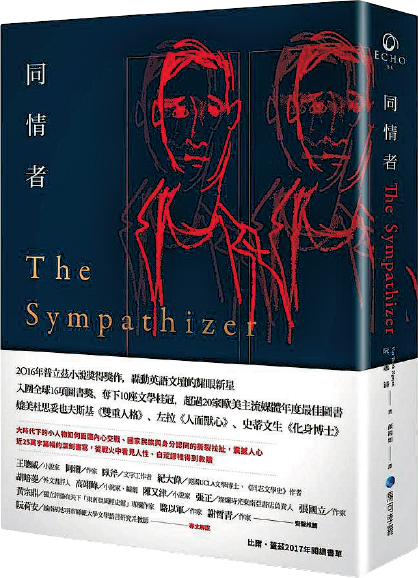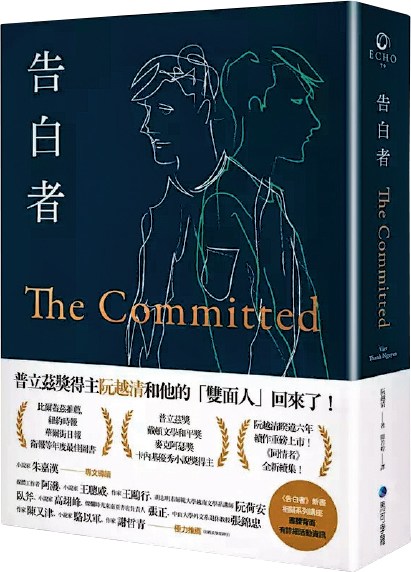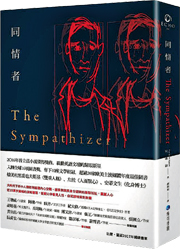【明報專訊】「在美國,這場戰爭被稱為越南戰爭;在越南,這被稱為美國戰爭。」由HBO及美國獨立電影公司A24聯合出品的文學改編電視劇《同情者》(上圖)4月於串流平台上架,開場文字已指向戰後敘事的二元性,如何記憶並敘述一場戰爭,取決人站立的位置。承接越裔作家阮越清2016年獲普立茲小說獎的同名原著小說,劇集同樣由潛入南越陣營的越共間諜的視角敘事,試圖讓觀者進入雙面人的曖昧世界,跳出主流越戰敘事的二元局面。
與曾改編薩拉馬戈小說《盲目》的編劇Don McKellar聯合執行製作電視劇《同情者》,韓國導演朴贊郁曾在HBO podcast節目提及初讀原著小說時感到莫大共鳴,因韓國人與越南人經驗有相通之處,而故事情節亦擺盪於東、西方,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陣營之間,因此他很快便決定參與製作。Don McKellar坦言本來對計劃有保留,尤其是改編暢銷得獎小說,但在得悉朴贊郁也參與其中後,他開始能想像影視改編的風格:就像朴的電影充滿黑色幽默。此前,朴也曾在2018年改編英國諜報小說家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女鼓手》,該劇風格相對沉實,不像《同情者》的改編幽默荒誕,與小說基調一脈相承,以黑色幽默包裹沉重故事。
朴贊郁在節目中提到該劇運用電視錄影機般的倒帶(flashback)設計,由於小說以主角於再教育營中書寫的自白構成,劇作也嘗試營造回述、時空跳接的效果,按需要擺盪在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在不同時空轉換間加入不過分解釋、且充滿玩味的畫外音自白(有時是對着鏡頭自白的畫內音),挑動觀者情緒。這些過渡有時則以跳接至類近情景構成,如點燃煙草對接曾經的戰爭火焰;主角幻想與相隔兩地的血盟兄弟「阿敏」一起聽曾在故土共享的音樂時轉接至當下已隨將軍流亡至美國後在家中彈結他的一個瞬間;主角接受美國記者訪問的情景跳接至過去審訊拷問越共成員的場景。一幕接另一幕,貼近小說中上尉自白時不斷閃回記憶片段的節奏,當下與過去緊纏,記憶延宕,逝去的像從未逝去。
游移的雙重視角
故事由歷史中1975年越戰結束、西貢淪陷(或越南解放)開展,潛伏南越秘密警察多年的主角上尉,本來想留在越南慶祝解放,卻不得不聽取指令繼續跟隨管領南越警察的將軍撤離,前往美國延續諜報工作,監視將軍一舉一動。作為越共成員潛伏於南越陣營、自稱為「出類拔萃的同情者」的上尉,能游刃有餘地游走兩邊並理解雙方:信奉共產主義同時熱愛美國流行音樂,把列寧斯大林等思潮論說倒背如流同時美式英語俚語信手拈來,支持越南解放同時同情南越「敵方」。這種雙面人的雙重視角,使身為間諜像演員般的上尉無可避免愈漸長得像敵方,像在小說中他自白:「大多數演員戴上面具比脫下面具的時間短,我卻是相反,也難怪有時候我幻想着扯下臉上的面具,竟發現那面具就是我的臉。」《同情者》出版後相隔6年面世的續作《告白者》,更是由兩張臉變成兩顆心,由間諜演變成巴黎難民的上尉,心也分裂成兩半。
越南出生、4歲隨父母坐難民船離越至美國成長、現為南加大教授的阮越清,在一個訪問中談及他從小亦有種當間諜的感覺,那時在家中會觀察越南父母,在外他會觀察美國人;而小時候在越裔男孩群體中也要選擇靠邊站,宛如越戰後的現實縮影。《同情者》出版後不久,阮身邊有越裔朋友告訴他,他們的父母很討厭他,因為小說主角是越共的人,美國越南難民群體更有人認為阮是叛徒;但與此同時,《同情者》也無法在越南境內出版,甚至電視劇也無法在境內拍攝,而要到泰國拍攝。形成這「兩面不是人」的局面,許是雙方只願己方版本的歷史被述說,但阮越清顯然對單向的敘事不感興趣,並認為那只會鼓吹戰爭,把別人化約為他者,化約為敵人,形成無限循環的暴力。
同時,阮也拒絕以美國主流視點書寫這場戰爭。像在他小說裏深埋的,也是個充滿矛盾充滿衝突、辯證不斷的世界。在《一切未曾逝去》中他引述索忍尼辛的詢問:「如果哪裏有邪惡之人在暗中作惡,只需將他們與我們其他人加以區分再摧毁就好了。但是善惡之間的那條線貫穿了每個人的心臟。而有誰願意摧毁自己的一小塊心臟?」由此提出一種更符合正義的「肯認的倫理」(an ethics of recognition),讓人看見並記憶非人性如何存在於人類身上,體認我們自身也有潛力傷害他人,或容許這些行為在我們的同謀或視而不見下發生。假若我們無法體認自身的加害能力,「就更容易自視為純粹的受害者,更有甚者,還讓我們有了理據,得以對我們認為傷害自己的人施行報復」。
後設角度的反思
只是,在過去的文學或影視作品中,被視為非人一方卻多是在國際上聲量較小的越南人。《同情者》面世前,以越南人視角講述越戰故事並能進入美國主流視野的作品,不論文學或影視皆長期缺席。阮越清一直記得還沒到13歲時看過著名的越戰電影《現代啟示錄》,自此便無從忘記那美國水手屠殺舢舨上所有平民的影像,最後一名上尉甚至處決了唯一倖存者,一名越南女性。每次他想起這些畫面就像再度經歷觀賞時的情緒,目睹如學者Sylvia Chong所稱的「東方惡畫面」(The Oriental Obscene),引發強烈的厭惡、驚駭、羞恥和憤怒,因為他看到的「自己」是一個他者、一個越南佬(Gooks)。阮認為那些死亡與屠殺的影像,對軍人來說也就是色情,可以撩起觀者淫邪的趣味,衍生戰爭欲望。在《一切未曾逝去》中阮更剖析了主宰電影生產及圖書出版等市場的美國,如何輸掉戰爭卻在「記憶戰爭」中獲勝,並提出荷李活作為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一環,如何控制記憶並滿足戰爭機器的需求。把越南人描繪成野蠻的威脅、未開化的人,可使人持續視他者為非人,製造法國思想家Guy Debord所說的奇觀(spectacle),令觀者變得麻木冷漠。
《同情者》其中一段重要情節,也是上尉參與拍攝由故事裏一位荷李活名導執導的越戰電影,名為《小村莊》。上尉最初不願為這自大狂妄的名導擔任越南顧問,但後來想到可為越南爭取更好的呈現而變得積極,望扭轉荷李活呈現亞裔時的刻板印象,像小說中名導助手輕視上尉時,他認為烙印在那助手視網膜上的「全是荷李活憑空揑造出來、盜取真正亞洲男人地位的閹人影像」,盡是傅滿洲、陳查禮等形象。小說中,上尉最終也無法扭轉局面,然而劇中的上尉某程度上算是成功了。這微妙的變化,使這個不乏後設電影(meta-cinematic)意味的電視劇,像落下一個「如今荷李活已不同往昔」的註腳,尤其不論在戲裏或戲外——戲裏《小村莊》的越裔或亞裔角色對拍攝者不無調侃與譏諷,如其中一名拍攝《小村莊》的臨時演員以廣東話讀出對白後,劇組人員竟說:雖然我明白那是兩種不同「口音」(accent),但你可否說得更像越南話?那臨演馬上挖苦地反問:「那你會不會說丹麥語?」;戲外,《同情者》電視劇除了能以越南人視角講述越戰,甚至搬演至(小說在批評的場域)荷李活,並由大量越裔演員飾演劇中角色,且越南語、英語對白各佔相當比重——也反過來映照如今荷李活的變遷。阮越清也曾坦言荷李活讓他感到驚喜,認為荷李活轉變了:「它跟小說和電視劇中所諷刺的1970年代並不完全相同。」
這場戲中戲還有一個更明顯的改動。劇中加入了蘭娜(南越將軍的女兒)到片場拍攝的情節,名導後來讓她加入《小村莊》、飾演一名被強暴的越南女子。相對小說輕略描寫名導在《小村莊》加入一段女性被4名越共強暴的情節,電視劇把這情節延伸改寫:一名以「方法演技」見稱的演員,突然某天向名導暗示想要得到蘭娜,然後接下來的畫面便是名導臨時加入的一場強暴戲。這場戲即便最終沒能完成(上尉試圖阻止),也不難讓人聯想到電影史上一段導演與演員即興設計、事前未經女演員同意的真實性侵情節,即《巴黎最後探戈》備受爭議的畫面。在運用後設電影(meta-cinematic)手法的劇中加入這段影射情節,指向的是否當今更具爭議性、在電影圈發生的各個#MeToo事件,引發觀眾反思?
被殖民與身分認同
令上尉被關進再教育營一年仍未能離開的一件事,也來自一段強暴情節:一名越共女特務被南越警察拷問並折磨輪姦時,作為越共間諜的上尉卻沒能保護她,甚至在自白中略去這段往事。當時,女特務被問及姓甚名誰時她答:「我姓越名南。」這段被放置影院內拍攝、後設式的情節於劇中反覆出現,迫使人思考審問的暴力、旁觀他人的痛苦如何形成「奇觀」,以及殖民背後的層層暴力。尤其當女子說出「姓越名南」時,更讓人想到這國度長年被殖民的歷史:「五四年我們國家被一群外國魔術師鋸成兩半,還有二戰期間被日本短暫佔據的過渡期,也要去適應前一個世紀有如慈愛長輩般的法國人的調戲。」(《同情者》)小說不時以戲謔口吻嘲諷,意識流地從上尉視野敘事,或呈現心迹。影視改編卻無法如此直白,當中的體制暴力與壓迫,便由羅拔唐尼(Robert Downey Jr.)一人化身五角擔演:中情局人員、東亞研究所教授、美國國會議員、荷李活名導、上尉的法國父親,無論哪個領域,全都是這一張臉,一張強化壓迫的臉。續作《告白者》後段更直接以劇本形式,諷喻終局發生的一切就如一齣「白色喜劇」,由白人殖民者投資的「史詩級大製作」。
母親是越南人、父親是法國人(作為神父從未承認兒子),上尉在那個尚未接納混血兒(更要是私生子)的時代,長年被罵雜種(bastard),自小被排除越南人外,幾乎所有親戚同學蔑視他,長大後成為間諜更使他陷入身分認同的窘境。除了上尉,殖民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也展現在離散者之中。南越將軍攜妻女到美國後,輾轉將軍夫人開了一家越南餐館,內有一個以越南國土形狀雕成、刻度環繞西貢時間的鐘,象徵着越裔在流離失所後被卡住的狀態:「我們都不只活在兩個文化中,這和偉大美國熔爐的頌揚者想像的不一樣。流離流所的人還活在兩個時區裏,這裏的和那裏的,現在的和過去的,就如同遲疑的時間旅人。」到續作《告白者》場景由美國遷移法國後,一個聚集所有越裔到場觀看的表演〈幻想曲〉,更把離散者領往舊西貢的歲月:「流亡人士聽的歌多半充滿濃濃的憂鬱、浪漫的失落感,自然而然讓他們想起失去城市的痛。」
小說裏的各人命運,似乎都被這特定歷史時空形塑。作為間諜的上尉,在將軍懷疑有內鬼時為明哲保身殺掉南越少校以及在美國報社當記者的左派小山,及後兩個鬼魂時常跟隨他,並在耳邊低聲叨絮。到《告白者》,情節逐漸落入與同被法國殖民的阿爾及利亞裔的衝突與殺戮中,讓讀者直視「盤根錯節的結構性暴力」(朱嘉漢語),更多的鬼魂縈繞。這「死人合唱團」既可視為上尉歇斯底里的心理狀態反映,亦可視為一種象徵,象徵悠長歷史上背負或蟄伏的鬼魂。如劇集終結前鏡頭帶我們從難民船移往海面的一幕,海中存在許多如鬼魂般的身影,呼應阮越清在《一切未曾逝去》中寫:「戰爭與記憶的並置,在20世紀的災難後至為常見,數千萬人似乎呼求着要被紀念、被供奉,甚至,若你相信鬼魂,要被安慰。」問題是,如何回憶與書寫過去,才是對被遺忘的鬼魂最正義的方式?
從《同情者》到《告白者》,上尉對自身與群體狀况的反思更為強烈,新舊角色言談間充滿辯證,法農、德希達等理論有效融入高潮迭起的情節,更不讓讀者從單方面看事情,也不讓讀者喘息。作為在美少數族裔的阮越清,沒有直寫以少數族裔在美國的經驗,反而選擇在大歷史中取材,回應美國及其戰爭歷史,如今回望,作品裏探討的殖民及戰爭議題在當下依舊迫切,其陰影縈繞未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