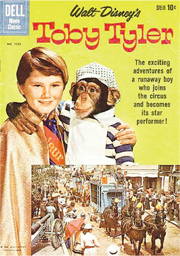【明報專訊】我們都知道,K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不知在哪一天(或,某天我們突然發現)離開這世界。
醫生推斷了一個日子作為限期,但,早在醫生作出這個宣判之前,K早已在十多年前的一個上午,對我們宣布:「我隨時都會死去。」癥結在肺部。姐姐提起了這件往事來安慰我。
其實,她忘記了,K也一定已經記不起,早在許多許多年前,K仍然年輕,我還未到上學的年紀,某個夜裏,K如常在工廠加班,直至深夜,《歡樂今宵》已經播完,還沒有回家,我開始擔心,漸漸感到一種恐懼,問姐姐:「她會不會,已經死了?」
另一天早上,K仍然在家裏。我感到很快樂。但她黑着臉問我昨天夜裏的事,而且說:「你是個惡毒的孩子,老是希望我會死。」
我不作聲,心往下沉。自此,我熟悉了心往下沉的感覺。當心的重量增加,我就把事情,或,某個人的影子,像一株花(連着根部)栽種在心的隱蔽角落。這花在心裏愈長愈大,漫山遍野,漸漸成了一片巨大的密林,使我每次碰上深愛的人或事物,都不由自主地聯想到,他們的死期,或我失去他們時的情狀,誤解是這之間的徵兆,而誤解,是一種人們無法自控的常態。
如果她一直都在,如同一種隨處可見而且觸手可及的日常,或許,就在習慣之中,我會慢慢忘掉了她。即使她就在我的眼前,身影也會在我眼睛裏消失。人們往往花掉大量的時間,注目在遠方的風光,想要接近能捏着自己目光的陌生人,卻無法真正認識身邊親近的人。
每隔幾天,我就會撥一個電話給她,告訴她,我有多麼喜歡她,聽她在電話的另一端大笑——並不是因為害怕她突然消失,而是,珍惜仍然擁有的當下,也只有在拚命珍惜的時候會再次發現,所有的珍惜終將徒勞,這一刻和下一刻以及上一刻一樣也會過去。時間像河水,一種遺忘的速度。
於是,我給她起了一個名字。並不是為了記住她,而是為了釋放她。
因為她已經很累很累。
K。
有別於她身份證上的名字,也不是,我們平日對她的稱呼,不是陌生人看到她時對她的稱謂。我要給她一個全新的名字,彷彿要把她從一個囚牢裏解放出來,但,很可能會被她拒絕,就像每一次,我表示要替她收拾髒亂的房子,她也會說:「你有潔癖。這是我家,人在混亂中,才會自在。」
她沒有給我任何名字,她可能不知道,名字是一份珍貴的禮物,卻不是每個人都會得到。
我從沒有告訴她,對於清潔的執着,其實是源於小時候,家裏總是沾滿灰塵和鞋印的黏黏滑滑的地板、很久也沒有人清洗的髒衣服,總是從缺的乾淨襪子,以及凌亂的桌子和衣櫥。我不可以說出這句話,因為這樣的坦陳太接近一種追究和控訴。
(我想用清潔作為結界,把自己和這個世界分割,就像從未出生那樣。)
(小時候,她常常用一種輕描淡寫的語氣告訴我:「其實我根本不想把你生下來。」)
因為這種坦陳的語氣中必然包含怨憤,那種怨憤或許不只是/真的是屬於我,而是這個社會加諸我們的對於一個母親應該如何持家的觀念——保持家裏窗明几淨、做出美味而營養豐富的食物,生產和照顧子女,而不必發展和忠於她自己。要是她聽到這樣的說話,也必定會內疚,對自己感到更生氣,因為,在她的意識裏,也有着一個模範的母親必須要達到的無數標準,雖然,在她之中也有一個愛護自我的反叛者,但反叛的聲音極微弱,只能以堅持不整理房子來表達對於母親這個角色的怠倦感。
無論我,還是她,甚至是城巿裏其他的人,在我們成為我們自己之前,必須先成為別人所期待我們會成為的那個角色,就像是一種義務,或責任。
血緣和家庭,帶給我們親密,以及,跟親密分量相若的殘忍,因為這種與生俱來的關係,以及日復日的共處,使我們習慣性地逼迫家人恰到好處地扮演他們的身份和角色,在他們可以安然自在地做作為他們自己之前。
因此,多年前,我遷出了跟她一起生活的那個居所,因為,人們需要距離,只有距離足以讓人重新記起對方是誰。於是,我可以留在潔淨的房子裏,盡情洗擦地板和洗手盆,放縱自己對於清潔的偏執,而她也可以留在物件胡亂放置的空間裏,在微髒中完全放鬆。偶爾,當我想念她做的菜,就到她的房子去吃飯,那時候,我要謹守當一個客人的禮儀,按捺着在借用洗手間時順便替她清洗座廁的衝動,因為,她的房子也是她內在的延伸,我可以走進去,放下禮物,但不可以任意以關懷為借口,以自己的意志改變或掌控她。
一位編劇朋友曾經在咖啡室對我說了一件事,最後,她下了一個結論:「所以,她的母親也妒忌她的美貌。即使親如母女,也會互相忌恨,親情也不是完全無垢的。」
我能感受到這句話之中的失望及懼意,但我看到的不是嫉妒或恨意,而是拘禁。一個社會,一個群體拘禁了女人,而女人也以相同的方法拘禁了自己和別的女人。在這個以陽性為主流價值的世界裏,女人有多美麗,就決定了她會得到多少愛。於是,比較就會出現,因為絕對的美麗是不存在的,有的比較美,有的不那麼美,但無論有多美,她們也不會永遠都美(就像,絕對的愛並不存在,有的得到多一點,有的沒有得到那麼多,而且,那種愛不會永遠都在)。女人一直被放於匱乏的位置,但同時,一旦她們成為了母親,卻要因為母親的身份被要求,源源不絕地為家庭和孩子供應,而且必須是無私、偉大的,不可以考慮個人的追求和慾望的,否則,她們就是自私的母親。
離開咖啡室之後,我想起一件事。K在我的青春期,曾經對我說過,她生下我以後,因為營養不良,臉上長出了黑色的蝴蝶斑。她走進藥房,打算購買可以褪斑的藥膏,但女店員盯着她的臉對她說:「無論塗什麼藥,你都是這麼醜。」K以逃難的姿態走出了藥店,但店員的話始終留在她心裏。
踏入暮年,K終於不再染髮。每次見面,我都會由衷地告訴她,她臉色紅潤、銀髮發亮,笑得像個少女。
「是這樣嗎。」她不願相信:「年輕時,從沒有人說我漂亮。」我沒有說,這只是因為,這個世界布滿了苛刻的眼睛,那種目光不止投射在K身上,也在每一個她之上。
當醫院裏的護士致電給我,告訴我,K的抽血化驗出現異常狀況,要我立刻到醫院替她取藥,並囑她準時服下,我即時致電K,問她關於吃藥的事。
那時,她正在追看一齣連續劇,並且氣定神閒地說:「不必理會他們。他們總是這樣,大驚小怪。」
「怎麼可以不理?」
「我只是因為去了旅行,忘記服藥而已。」她說:「你以為,吃了藥,就會痊癒嗎?」她對我描述這些年間在公立醫院長期病專科看到的病人:「他們就是服下太多藥物,愈吃愈虛弱。」她堅持,她的身體是她的,應該由她作主。
於是,我就知道,她所需要的,或許不是藥物或醫囑,而是更多的陪伴。
(在她不知道的角落,我便給她起名K,讓她在被書寫的過程裏,脫離母親或其他身份的指涉,還原成一個盡量接近本來的面目。)
K來我家看我,就像很久之前那樣,她再次對我訴說童年時期在馬來西亞的橡膠園度過的日子,那所房子,以及她所飼養的常常喜歡睡在灶頭的貓。當她跟着家人匆匆回到中國的時候,無法帶上牠。
「誰知道呢?」我說:「或許我就是那頭貓輪迴再回到你身邊。」
K便瞇着眼睛,出神地看着我,似乎已被我說服相信了我虛構的故事。我只好忍住笑意對她說,如果有來生,希望我們也會相遇,最好的情況是,她是主人我是貓。
「不﹗」她說:「今生我已把你養大,下一次,當然是我做貓。」
生命本來就是,由撕裂和痛苦地開始,一個人從另一個人的肚子,血肉模糊地被扯出來這個世界,而每個人終於都會,失去呼吸,歸於塵土。
下輩子再遇到K的時候,她可能是我的朋友、老師、寵物、上司、情人、敵人,或陌生人。但,也不必待到下輩子,現在,當我想起K,我會知道,是穿透了表相的那種覺察,在母親、妻子、女兒、病人,K,首先是一個女人,一個人,一個獨立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