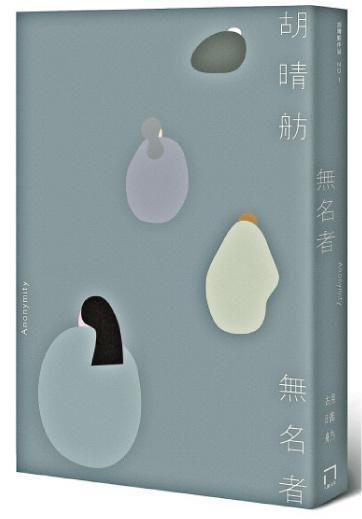【明報專訊】現代的移動是很普通、很簡單的,很多人從小就有移動的經驗,旅行、遊學、公幹或移民都是平常事。胡晴舫,台北出生,一九九九年移居香港,後來各地遊走,旅居過七個地方:美國威斯康辛州、香港、北京、上海、巴黎、紐約、東京。今回到香港,任光華文化中心主任,作兩地的文化橋樑。胡晴舫說:「我這麼普通的人,就在移動的話,流動這件事是當代人的共同命運。」
「以前移居就是移民,就是離開你的社會,但是現在的移居是轉換了一個環境,好像從一條街換到去另一條街去。」然而歷史上的移動是痛苦的,胡晴舫認為在二次大戰的時候,移動是因為戰爭,人們是被迫離開家園。到了冷戰時期,世界由柏林圍牆分隔,移動是為了要離開某個社會體制,是沉重的。她說:「柏林圍牆倒下時,我們這些人便開始亂走,是出於自由意志的遊走。」《無名者》其中一篇講到柏林圍牆這事情,是因為她理解自己是時代的產物。「其實時代還在定義你。身為一個作家,責任是觀察我的時代,用文學的角度跟我的時代對話。」胡晴舫更強調是華文文學,說:「因為我們有着自己對大時代的對話,風土人情不一樣,承載的歷史、包袱也不一樣。」她從時代的定義出發,遊走世界各地,令她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和責任。
領悟人類整體命運
「隨着歲月和旅途的加長、拉遠,我開始領悟到一些事情,才會有這本《無名者》,旅途對我的影響,就是我對時代的體悟,對人類整體命運的看法。」旅居各地加深了胡晴舫對人類集體性的透澈看法,年輕時她會想到自己跟世界的關係,處理「我是誰」的問題,經過很多地方以後令她有很大的改變。「我發現人類的共同性格,理解到人跟人的關聯在哪裏,明白個人的幸福似乎跟社會集體未必有關係,然後思考地球和人類的關係。」
胡晴舫居住在不同的城市,不光是住在那裏,還經歷了那個城市發生的重大事件。如住在香港時,發生了疫症;在東京,遇上三一一大地震和福島核電廠事故;去斯里蘭卡,碰到南亞海嘯;在波士頓,碰到波士頓馬拉松爆炸;在巴黎,也經歷了音樂廳恐怖襲擊。她說:「我去年搬回香港,也經歷了港鐵縱火案,發生時我也在過海途中,非常接近。移動的經歷使我觀察到,因為一些自然災難或人為襲擊,令我和很多不認識的人,一同捲入了面對死亡的命運。」他們大多都是最普通不過的人,大家一樣是從學校出來,找工作、戀愛、交朋友,一樣被放到社會上去求生存,在社會上不是最上層,也不是最底層,而是在中間,並且是最多數的。她說:「我們這種人最容易被忽略,比如日本的大地震,死了三萬多人,其實每一個人在他死前都非常認真地在生活、認真地在工作,他的人生也可能有很多的快樂和挫折,但他最後走入歷史的方法,是一堆死亡的數字。」
胡晴舫感嘆着這些被忽略的「無名者」,在時代的浪潮中載浮載沉,面對無法掌控的命運,她說:「人類的歷史是一條河,完全無辦法控制,你死的方式,死在誰旁邊也沒辦法控制。海嘯來的時候,不管膚色、語言、性別、年紀,全都被捲走,當然我們可以把海嘯視作是時代的浪潮,它來之前我們都很快樂在岸邊生活。」有時候,浪潮或許由浪潮中的人造成,胡晴舫指出:「所有偉大的宣言都是以人的名字發言,人為什麼要戰爭?很多事情都是『無名者』發起的,最後死難的數字也是『無名者』最多。巴塔克蘭劇院的恐怖分子渴望要改變歷史,他們殺的也是一大群『無名者』。」「無名者」跟「無名者」之間,為她帶來不同的思考,也讓她關注這一群每天努力地生活,經過挫折跟沮喪,用不同的方法活在世上,而又默默步向歷史的人。
語言的土壤
旅居各地除了令胡晴舫思考世界外,還提供了語言的養分,她說:「小時候的語感是台灣給我的,是一九七○年代社會土壤很貧瘠的台灣,在迎向世界時,我接受了香港、上海或英文、法文給我的感染,豐富了我的語言。」語言系統不可以封閉,寫作本身就是活化語言的過程,語言一直被不斷使用,不斷地變化。「我不斷的活化、創新語言,展現不同的樣貌,它絕對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並不是靠追求文字的純淨性為目標。」
香港的文字很獨特,受到廣東話和英文的影響。胡晴舫曾問董啟章思考時是用什麼語言,她說:「聽他說思考時使用粵語,我是蠻驚訝的,當變成文字時閱讀卻沒有障礙。我讀香港作家如劉以鬯、董啟章、西西的作品,覺得他們有獨特的語感。」她認為每個地區都有它使用語言的方法,以台灣為例,有國語、台語,然後加上日語形成獨特的文字。「這些都是作家的養分,所有作家都在尋找自己的表達方法,所以在文學裏每一個作家都是追求獨一無二的,我們身處的社會給予我們不同的養分,讓我們長出不同的花卉。」她形容香港文學的獨特性可能是其開放性,以國際大都市的姿態容納不同文化、不同的語言。
旅居者的「根」
這些年來,儘管我們的城市有着分崩離析的轉變,讓人無所適從,有人嚷着要離開,胡晴舫卻回到了香港。對於經常移動的人,「根」是重要的命題,胡晴舫曾經講過:「台灣是我的故鄉,香港是我的家鄉。」她來港時是二十七歲,這城市令她震驚:「那時我還年輕,香港一下子就影響到我,是因為那自由的感覺。」當年的台灣,對女性有一些期待和束縛,要符合傳統女性的形象,她憶述:「我離開時,台灣還在談女性主義,女權這件事情還是要再討論,到了香港這事情就解決了。香港是相信女性的工作能力,沒有人會期待你要溫婉,女性可以直爽,可以說出心裏話。」香港的法治和專業主義令她找到好的工作,胡晴舫說:「那時候的台灣社會是關係主義,很多人會說那個人是誰的兒子、那個人是誰的學生。在香港,他們看你的才能和熱誠,然後就給你機會。」
很多人說香港人很冷漠,但胡晴舫卻看到香港人的美:「他們嘴巴都很兇,但在緊要關頭都會提點我、幫我,其實香港人是非常慷慨。不要看他們每天都在匆匆忙忙,其實心裏是有不同的面向。」她認為所謂的「根」,就是人認同當下生活的社群,說:「你認同、你歸屬、你要守護的,『根』就是這個概念。」她因為看到香港人關心社會、參與社會運動而欣喜:「從台灣人的角度來說,你會發現香港人是非常純真,他們都充滿了希望,每一張臉都在發光。」這光芒是源於守護社群的心,也許這就是「根」的價值。
命運的安排,現在胡晴舫每天上班下班,都走在她很喜歡的灣仔港鐵站往會展的天橋上,她興奮地說:「天橋永遠是擁擠的,有各式各樣的宣傳,兩旁廣告招牌五顏六色,而且什麼氣味也有,但很奇怪,人走來走去卻不會碰到別人,非常有香港味道。」這番描述是親切、真摰、用心的,回到香港也是一個很自然的動作,生活過十一年的城市,對她來說的確是一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