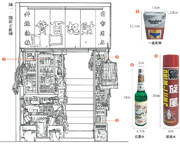【明報專訊】他給記者回電,爽快答應見面:「今天都可以!」
一小時裏約成訪問,快過小明上廣州。
我們唱盡他的兒歌──《何家小雞何家猜》、《十二隻恐龍去野餐》、《小明上廣州》各有千秋……卻未必知道他的名字。
小時候未有認真思考歌詞,只懂反覆吟唱,卻不知不覺一句句刻進記憶。
現在的外購卡通片主題曲沒改編成粵語,外語咕嚕咕嚕小朋友無法跟上,《兒歌金曲頒獎典禮》亦乾脆摺埋,「兒歌」彷彿成為幾代人的集體回憶。
「香港兒歌之父」韋然,作品陪伴無數小朋友成長,在我們都畢業多年後,他依然好學不倦,攻讀博士,為兒歌研究「做功課」。
從童謠舊曲尋靈感
在颱風玉兔徘徊不去的黃昏,我們乘坐子彈𨋢,登上韋然在工業大廈的辦公室,窗外紫紅的天色魔幻,我們像潛進密封的單位。韋然從閣樓步下,像一個躲在洞穴裏深耕細作的智者。他徐徐談起寫兒歌的因緣,彷彿已是更深遠的事。當年他加入麗的電視台當兒童節目《荔園小天地》編劇,由張堅庭主持,他本來只是負責為節目編「傻瓜笑話」,「但見隔籬台《跳飛機》有兒歌很紅,這邊說也要有歌,我就開始寫,但其實我唔識的」。
電視台工作人員遞來一本《協和幼稚園歌集》,任由他選取歌曲,按節目內容填上新詞。歌集中的歌曲至今一直在不同幼稚園裏廣泛流傳,「像『一耕天常思麵』、『鵝士一個歹拼過』、『禁田士稱天』。」記者皺皺眉,不明所以,他朗朗笑道﹕「即是『一更天想思眠』、『我是一個大蘋果』、『今天是晴天』,由不諳粵語的外國人填詞,所以全部唔啱音」。
第一次填詞被打回頭
第一次交給電視台的功課,他選了歌集裏一首關於郵差的歌,填成《紅花開黃花開》,結果給電視台音樂總監黎小田退回,「他笑笑口問我,這是什麼,我才知道粵語是一字一音」。當晚回家後拿出報紙副刊,將常用字整理歸類到不同的音階,「比如《明報》是so、do。我成晚就執藥咁執,第二日就懶醒地交給黎小田,他接受了」。無師自通,他說那個年代人人都是這樣子。
唸謠采風 二次創作
啱音是基本要求,在麗的工作年間,他每星期為節目填兩首歌,產量豐富但他並不滿意,「填了幾個月,覺得好悶,為什麼寫極都是人哋的歌?為什麼香港沒有創作兒歌呢?」一天讀了盧青雲在《明報》「自由談」寫的樂評,「她看完音樂會,很感觸,說外國對童謠很着重,外國童謠都經音樂家譜曲,比如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但中國完全沒人理,香港也一樣。我開始想,這個責任是不是應該由我來負呢?我就開始做童謠蒐集」。
他說的童謠,是唸謠。一如當年獅子山下許多「好打得」的香港仔,在麗的工作同時,他也在香港大學當旁聽生和圖書館助理員,在圖書館書櫃上如獲至寶地找到一本《美洲廣東華僑流傳歌謠彙編》,「晚清發生太平天國暴亂,太平天國的人要不投降,要不走到外國謀生,南美當時很需要人手發展,廣東人帶着自己的文化到當地,包括我太爺,也在那裏落地生根,文化卻保存得很好」。書中記錄了二百首兒童唸謠,他嘗試按詞譜曲,發覺很難聽,就大膽只擷取關鍵字,自己作曲再填詞,像《何家小雞何家猜》,原來是遊戲口令的童謠只有四句——「何家何家何家猜/何家公雞何家猜/何家小雞何家猜/何家母雞何家猜」,「我就將它故事化,『真怪誕呀又有趣/你望望公園裏』,用入心的擬人法帶小朋友玩,說有『黃狗爸爸羊媽媽』,又有『松鼠妹妹牛叔叔』,加強童趣,發現好work,小朋友很喜歡」。
「小明」唱足四十載
韋然被譽為「香港兒歌之父」,因他史無前例地創作大量粵語兒歌。他認為兒歌內容必須與時代緊密扣連,說自己什麼都不懂才敢將固有統統打破,重新建立,「那批晚清的童謠題材,比如《光陰好》、《椰子夾酸薑》, too far away,但內容可以modify,比如《豆腐蒸蝦米》,原本是『雞公仔/洗落米/唔見阿婆買餸歸/芥菜煮苗西/豆腐蒸蝦米』,如果換成現代情境,比如『媽媽話啲餸好貴』,小朋友就很喜歡」。許多兒歌都由兒童遊戲口令入詞,「以前小朋友玩『狐狸先生幾多點』、『木頭公仔唔准郁』、『See See Madam砰澎猜』,現在他們玩『龍蝦屎屎』,你聽過嗎?」看見記者再陷入迷惘,他拍拍雙手,再拍拍大腿,唸起口令,得意地示範起來。
當年香港沒有原創兒歌,他用短時間寫成了三百首,將傳統童謠改頭換面,到唱片公司敲門,「很快就答應了,條件是沒有人工,不過我們可以用他們的錄音室,好開心,每個人可以得到五盒盒帶作為報酬」。他邀請港大合唱團認識的好朋友一起錄音,當中有前資訊科技及廣播局長尤曾家麗。雖然盒帶大賣,卻引起了改編的爭議,「比如『雞公仔/尾彎彎/做人新抱甚艱難』我改成『做人點可以怕艱難』,由灰沉沉變成了很勵志,有人認為不應該」。面對抨擊,他卻十分自信,「但這首歌證明改編是work的,這個版本幾乎取代了舊的,舊的大家基本上都不會唸了」。
跳出香港的小明
說到兒歌內容也要與時並進,不得不提韋然的小明系列。小明自從出現於一九七六年的《小明小小明》,至今已經四十二歲,是韋然作品中最長壽的角色,小明是個怎樣的人?「是一個很naive、純真的小朋友,永遠長不大的,喜歡周圍去。」
一九七六年的《小明小小明》,今天網上仍能聽到,編曲相對簡單,夾唸夾唱,歌詞只是遊戲「小明捐山窿」的口令。韋然在二○○六年將歌曲重新改編,雖然說是「加強版」,聽起來卻徹頭徹尾是一首新曲,「我覺得香港的小朋友不認識自己國家,想靠這首歌帶大家遊覽中國。小明坐火車,坐火車去邊度?坐火車去新會,坐火車到洛陽,去北京探祖父,去西京探外婆」。小明喜歡旅遊,除了大家耳熟能詳的《小明上廣州》,韋然筆下還有《小明去東莞》、《小明遊深圳》,像是特別喜歡到內地玩,韋然說他的兒歌不帶政治意識,卻指另一首《小明探阿爺》有「最多話想說」,「但這首不是兒歌,是成人的兒歌,寫給長大了的小朋友」。
「爺爺讚佢好聽話/識得冇亂玩嘢」,《小明探阿爺》的歌詞似有中港關係的隱喻,「青蛙叫/水滾了/精人蠢人正亂跳」也似乎在寫溫水煮蛙的操作,韋然說歌詞內容開放給聽眾自行詮釋,但不多不少表達了自己對國家的感受,「我從小很崇拜『阿爺』,但又好憎佢,他令中國有很多悲劇產生,是魔王和救世主的混合體」。副歌以三字一組,從孫中山立國、日本侵華、大躍進、文革、四人幫,講到近年的貪腐醜聞、黑心食品事件,「很多事情我感到無奈,左右很難分,正義很難分,綠藍很難分,甚麼才是對呢,世界很大,很多事情我看不清」。
透過兒歌,他也帶小明乘上了高鐵。《小明搭高鐵》寫有「一地兩檢/靈活措施利市民 」、「高鐵開路/連繫各方搞好經濟」,韋然坦言自己沒有政治任務,「如果放民生在大前提,是真的很方便,但主權方面,好像有少少not appropriate」,但他認為可以靈活處理,思考一件事情是不是好事,要從「離苦得樂」的宗旨考慮,讓小明坐高鐵旅行,只是從方便與否的民生角度出發。
欠傳播平台 兒歌盛况不再
兒歌不再流行,韋然認為在商業社會無可避免,但一再強調香港並不是沒有新的兒歌生產,他指每天本地都有音樂劇上演,當中兒童音樂劇為數不少,每年至少增添百多首原創兒歌,「我今年寫了幾套,有王司馬與牛仔的《飛行棋》,去年寫了《孟子與虎媽》,但表演完了放在YouTube,最多有五六百個click rate,五六百個都是自己看、親朋戚友看」。他認為問題在於缺乏流傳的大型平台,「電視台為什麼不播兒歌呢?因為兒童節目沒有人賣廣告,做一隻兒歌,要拍一個MV,要錢的。以前電視台賺錢時當津貼一下兒歌,做branding,但現在電視台蝕錢,節目cut得就cut,外購的日本卡通片,歌都不再改成中文了,找人填詞也要錢嘛」。電台方面,他指自己從前的兒歌能夠流傳到外國,因為兒童節目例如《聽聽唱唱學英文》、《漫步唐詩路》都放在主流頻道的黃金時段播放,現在電台只為了滿足政府要求,將兒童節目敷衍放在冷門頻道和時段。而大人和小朋友都不愛買唱片,亦令兒歌流傳變得困難,「以前做兒歌,可以賺錢,就算不賺錢,能夠平衡收支,我都做。現在做一隻就蝕一隻,做一隻兒歌碟都要二十萬,以往賣到三幾千,可以收回成本,現在這些錢賺不回來的,大家都是自己掏錢包去做」。
有卡拉OK集團近日被控侵權,須將相關唱片公司的作品悉數下架。韋然的作品多年來也一直被侵犯版權,在許多唱片中曲詞創作的一欄被刪去名字,「香港的華資唱片公司從來都不喜歡計版稅給作者,唱片公司如果寫我是作曲、填詞人,要我授權才可以印碟,要是刪掉名字,寫『傳統』就不會有人去考究了。」商業用途上的擅自取用,雖然不公平,但作為獨立創作人,不像大集團,往往未能靠自己爭取,「寫一封律師信最少要五千元,按歌的收益,我可能分到五千元版稅,但打官司隨時要二十萬」。雖然如此,他認為創作亦不應被版權制度綁得太緊,只要不是商業用途,放寬有助歌曲的流傳。
好兒歌帶給小朋友歡樂
如何讓兒歌重新連上聽眾,也在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範圍,他認為作為教材在學校裏傳播曾經十分奏效,《何家小雞何家猜》曾被納入課本內容,希望日後可以將更多好的兒歌推介給學校。什麼是好的兒歌?「兒歌只要帶給小朋友歡樂就足夠了。如果能happy learning就是bonus。最重要是歡樂感,小朋友要開開心心,才能學到更多,整天暴躁就什麼都學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