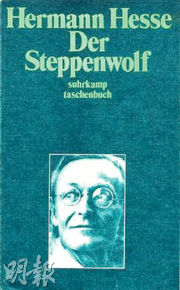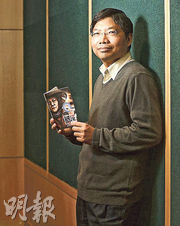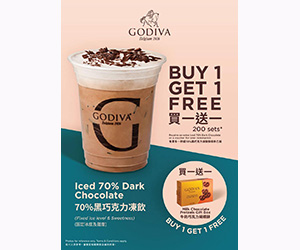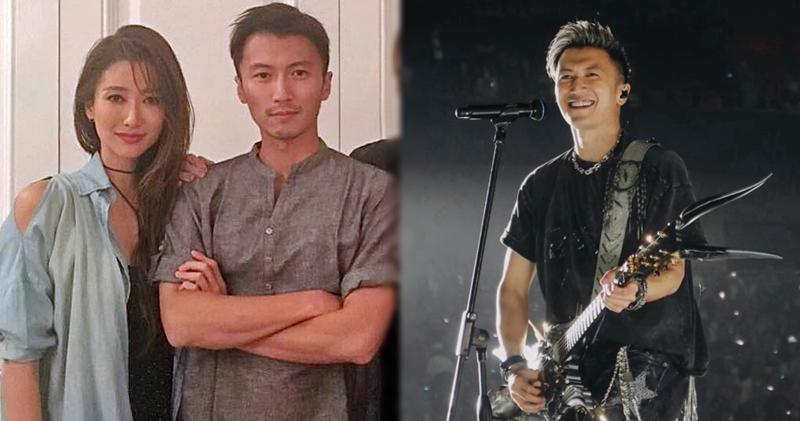【明報專訊】也斯,原名梁秉鈞(一九四九—二〇一三),香港戰後第一代本土作家的代表人物。我得知忘年好友也斯身罹肺癌,便為他開展這個文學家紀錄片的拍攝工作。我一方面希望為朋友與香港文化做一個紀錄;另一方面,我嘗試為香港文學尋求一種與世界對話的語言。
紀錄片是以記錄真實為主。不過文學家的真實生命,除了表面的生活記錄,創作的世界才是文學家最重要的真實生命。如何透過電影影像呈現作家的想像世界?相信是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文學家紀錄片導演所不能迴避的問題。
也斯的文學,崇尚自然,反戲劇化。也斯見到我拍攝《劉以鬯:一九一八》選角挑演員時,他很鄭重地跟我說:「你不要找演員在我的紀錄片內出現,更千萬不可以找演員飾演我。」我記得平日跟他聊天,那種中學詩歌朗誦比賽所推崇的抑揚頓挫模式,也斯最為反對,認為很造作。他喜歡的是一種平易近人的、隨和內斂的語氣。這是一種輕的表現方式,追求一種清淡的美學。
他眼中最美好的詩,是一種跟生活息息相關的狀態。可以看、可以食、可以穿、可以游、可以歌、可以舞的。也斯的文字可以跟不同藝術家交流和越界,讓文字轉化成不同的載體。文學可以化成了照片(李家昇、王禾璧、又一山人等攝影師的合作);可以化成了食物(劉健威、蕭欣浩等的食評人做菜);可以化成了時裝(黃惠霞、鄧達智等時裝設計師以衣服布疋與也斯作品對話);可以化成了旅行(也斯周遊列國筆下的東歐、美國等世界不同的城市);可以化成了歌聲(香港音樂家龔志成與瑞士的表演樂隊「聲場書法」的音樂),當然,也可以變成舞蹈,香港舞蹈家梅卓燕的現代舞,可以說是其中極大的挑戰之一。
梅卓燕設計的舞蹈,改編自也斯的《戀葉》,原來是在室內表演的。我想,電影具有放大的能力,能夠展現無窮想像力。如果能打破空間的阻礙,穿梭於戶內戶外,讓具象與想像兩種元素不斷更替,具象中看到抽象,在抽象中看到具象,便能將也斯二元對立的詩作風格,更具體呈現出來。我嘗試用電影語言,重新構思梅卓燕的舞蹈。這一段舞蹈大概只有八分鐘,卻要用影像呈現文字的內涵,整體呈現也斯整首詩的風格和美感,絕非易事。
這個片段本身是具挑戰性的,甚至溢出一般人心目中的所謂紀錄片的「標準」。不過,我堅持這個舞蹈放在電影中,就是尋求這種標準以外的驚喜,拍攝一部非一般的文學家紀錄片。結果台灣公映後,我很高興聽到很多觀眾對這段演繹十分喜歡,香港首映的觀眾對這個片段亦十分難忘。兵行險着,亦是值得的。
混雜、拼湊與反結構
《東西》電影其中一個要解決的難題是結構,也斯的朋友實在太多了。他跟我訂定受訪嘉賓,他們來自不同藝術界別,甚至來自南北東西,語言不一,幾乎世界各地都有他的朋友。也斯還打趣地說:「我的朋友都有我性格的一面,你見到他們,合併起來,那個就是我了。」我於是斗膽用後現代的拼湊觀念,讓他的朋友在電影中互相拼湊。最後受訪者竟然超過四十人,我要為每一位受訪者度身設計一種方法,把他們的性格準確地表現出來,無疑是一大考驗。例如鄧達智的出場,是在元朗一邊食盆菜,一邊談也斯。日本的世界文化研究學者四方田犬彥教授,以前常跟也斯比較日本與香港文化差異。我邀請他在北角街市的擠擁人流中穿梭,然後與他一邊乘坐電車,一邊談香港文化。德國以硬朗馳名的學者顧彬教授,我邀請他身穿西裝漫步雨中。諸如此類,無一相同。每位受訪者各自精采,卻在他們眼中呈現不一樣的也斯。
我想起讀也斯的小說,表面看似沒有結構,評論者難以找一套西方理論簡單套進去分析。其實他是用詩人的思維來寫小說,他追求一種自然、蕪雜、包容的境界。我發現他不是用理去整理各種關係,而是通過情來組織結構。我想也斯的電影應該走這種風格,充滿現代抒情的風格(詳見拙文《中西抒情:也斯〈剪紙〉中七十年代殖民香港的都市情感》,收於陳素怡編:《也斯作品評論集(小說部分)》,二○一一年)。因此,我要把也斯生前片段,與他的朋友不時互相照應,用情拼湊出一個也斯與朋友互動的世界,打破生死的隔閡。
觀眾觀賞這部電影會面對一個挑戰,看完電影後,你要在腦海中重新拼湊也斯的形象出來。為什麼要這樣處理?因為我一直思考一個問題——
紀錄片究竟可不可以情通生死,叩問靈魂呢?
(作者是小說家、電影編劇、電影導演。)
(本版「特輯」黃勁輝導演文章為節錄,全文刊於《明報月刊》文化附冊《明月》三月號,更多精彩文章見《明月》三月專題「他們在島嶼寫作」。)
●黃勁輝
■《明藝》前期內容可瀏覽:
《明報月刊》網站:www.mingpaomonthly.com/cfm/main.cfm
《明報》網站:www.mingpao.com>搜尋>輸入「明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