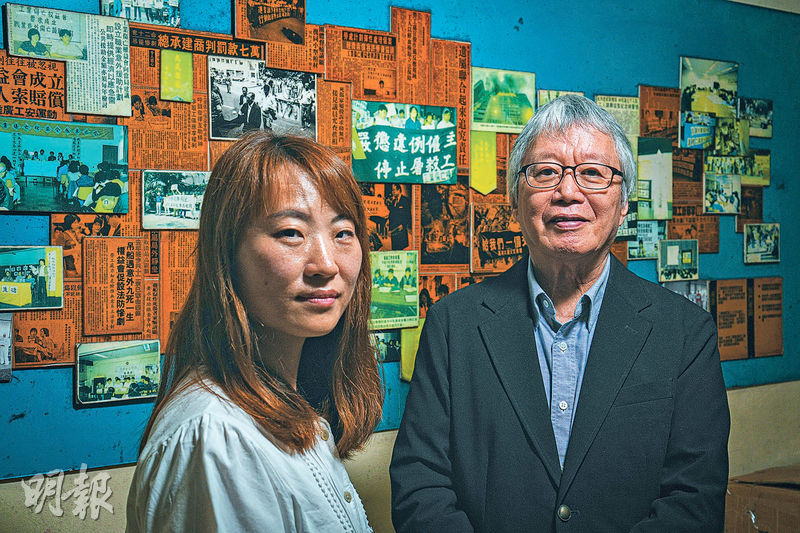【明報專訊】以香港為故事背景的《高凶浩劫》去年上映,男主角是聯邦調查局前人質拯救隊長,一次任務令他失去左腳,自此需穿戴義肢。故事講述退休十年後,他來到香港擔任摩天大樓「明珠塔」的安全顧問,其間發生恐怖襲擊。救人過程中,他在高樓外沿繩攀爬,場面驚險。銀幕下他即使穿著長褲,跨步間仍不時露出充滿機械感的腳踝。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汪春春的論文以義肢為題,她發現,大部分西方文化社會並不會「包裝」義肢,而內地義肢製作則預設要「包裝」。她說的「包裝」,是指將鋼管部分用肉色泡沫材料套上,再打磨修飾的工序,為求讓義肢觀感更接近真腳。「『包裝』在中國是統一化的流程,我就想,為什麼大家會對義肢的肢體形狀有執念?」
小腿義肢 如何做?
汪春春花了一年多在四川一家康復中心考察,近距離觀察中心技師如何製作義肢。因每個人的腳粗幼、形態有別,為保證舒適和安全、防止突然鬆脫,所有義肢都要度身訂做,而且步驟繁複。
技師先按使用者的腿形做一個模具,灌入石膏。取出這段實心的仿製腿後,必須稍微修整形狀,並削小約3%至5%。「截肢後長期沒有運動的部位,會因血液不循環而腫脹。以後會因穿戴義肢壓縮,肉會因再次運動而略為萎縮,肌肉會變小一些。」她說。剛穿上義肢的人通常覺得很緊很痛,也不如外人想像可重拾步伐如獲新生般輕鬆,「很多時候痛感是沒辦法處理的,要待使用者自行克服,努力去接受它」。為了減少皮膚與「接受腔」的摩擦,在石膏削小後,會用軟物料製成「內襯套」貼在石膏表面。「內襯套」外加上八至十層纖維材料,並以碳纖加固。最後以液體樹脂填充空隙,成形後取出石膏棄掉,餘下的部分加以打磨,除淨石膏粉末就完成。
義肢的這個部分稱為「接受腔」。汪春春解釋,更關鍵地影響功能的,其實是「接受腔」以下的連接鋼管與腳掌零件,由廠商製造,性能因價格而異。我們偶爾在電視上看到刀片跑手刻苦練習的勵志故事,田徑場上,他們腳上的彎弧每一下踏步,都顯得非常有力。「平常走路毋須這種彈跳力,用來走路變相像跳起來。」汪春春指出,最普通的款式腳踝關節不能動,走起來感覺沒那麼靈活,更好但價錢相對較高的,除了踝關節可以動,腳掌亦參考「刀片」設計, 「但弧度要小很多很多」,可「儲能」。香港截肢者協會回覆說,香港公立醫院有提供義肢製作服務,坊間亦有私營義肢中心,由於政府只會資助最基本的義肢型號,截肢者會按經濟能力和身體狀况選擇。
愛靚有罪?
「『包裝』其實就是修飾,變成看起來更像真腳那樣。」汪春春掃掃平板屏幕,展示一張「包裝」前後的對照圖,圖中經過「包裝」的義肢,鋼管被肉色材料隱藏,姿態稍為僵直。她說「包裝」用的材料質感軟,柔韌度很強,「嘗試做得跟皮膚顏色有點像,可是跟大多數人的膚色都不太像,比較深色。」
香港普遍截肢者的義肢都不經「包裝」修飾;相反,在內地,「包裝」卻是義肢產業統一化的流程,也是製作的最後一個工序。汪春春形容,很多技師甚至將此視作專業程度的表現,做得愈像真代表愈專業。她說「包裝」工序的潛藏邏輯,「為什麼要像真?因為它是假的,要看起來真,為了隱藏殘障,讓這個人變成健全的人」。她稱這種知識的形成其實由技師累積經驗,轉化寫成行內通用的教材,「當經驗變成了知識,就變得權威了,反過來影響自己日後做義肢的過程,也影響後來的技師如何做,變成對這個職業的專業要求」。但她亦指出,知識並不是技師平白無故地發明,使用者也參與貢獻,「我看見大多數人其實也希望有『包裝』,很多人拿着義肢的第一反應是『啊,是這樣的?我不會就這樣離開吧?你們會稍微弄一弄嗎?』」問題在於,這種牢固的意識形態會怎樣影響社會觀念,又如何回應不想「包裝」和對「包裝」效果不滿意的人。她研究時接觸的截肢者中,就有人不滿腳眼凹凸感不夠分明,有人覺得截肢與斷肢的接駁過於凸出,弧度不夠自然。
殘障者 這身分
汪春春說起讀過一本書Beyond Surgery,書中敘述埃塞俄比亞地區醫療資源有限,孕婦難產過程組織壞死,使產道出現漏口,引致日後大小便失禁,而且會通過產道流出,當地人嘗試施予手術。「手術普遍被認為是修復,等於是奇蹟,有一個suffering(受苦的),給患者做手術,就達成了『救贖』。」她說穿義肢的人狀况也相似,「有人殘障,給他們提供義肢時,就像說這個人的生活可以被重建。但之後是不是真的就可以恢復原狀呢?那是『超越穿戴義肢』這件事。」據她觀察,安裝義肢前後需要在生活不同層面不斷磨合,成為殘障者更是一種進程,「有身體的缺失和要不要希望自己是屬於殘障者這個群體不同,怎樣面對自己殘障,有很多種選擇。」
汪接觸的截肢者中,其中一個叫謝仁慈,她自四歲一次車禍被奪去右腳,因經濟問題到大學才安裝義肢,近年常在媒體上曝光,形象樂觀積極。「她不包裝義肢,露出來的,而且是基於一種很強的自我意識,覺得露出來是認識到自己作為殘障者的身分。」謝仁慈並非一開始已有這種意識,穿戴義肢三年後才有這決定。大學修讀法律系的她,讀書時發現法律有很多針對殘障者不太公平的地方,對條文描述身體狀態的用詞也感到不舒服,就跟教授討論,「教授跟她說,那你應該去為自己的群體、為自己奮鬥,因為你是個殘障者。她一下子意識到自己正是個殘障者,應該珍惜這個身分,要為自己努力」。汪春春說,事情的轉捩點發生在謝仁慈一次買衣服的經驗,因為義肢總是把褲管撐得鼓脹,她每次出外都意識到途人的側目,有一次終於受不了,自行把義肢「包裝」撕掉,露出鋼管,「撕掉後,她說覺得新世界的大門打開了,以前作為殘障者,想坐關愛座、使用殘障衛生間,別人會因為她年紀輕不理解,以後就可以光明正大」。汪春春形容謝仁慈當時是「準備好」迎接不同的回應,想要挑戰其他人對於身體「應該是什麼樣子」的觀念。
重建身體希望的工具
汪春春接觸的另一截肢者廖女士,取向卻是另一極端,她為了使義肢接駁口的弧度更平順,自行壓扁調整,反令小腿義肢跟大腿、脊柱的重力線偏移。另一方面,她也沒有為自己辦殘疾證,不去領取每個月的經濟補助。汪春春說,對仁慈來說,義肢是建構自我身分認同的一部分;對廖女士來說,就可能是她重建身體希望的工具,「可能希望總有一天恢復到原來狀態」。雖然兩人的想法不同,汪春春認為任何人都可以選擇面對身體的方式,即使沒有跳出健全身體觀的框架審視自己,每種方式都應該被尊重。
形象正面 或簡化實際困難
「但仁慈另一方面……表現出來的形象非常積極樂觀。」汪春春解釋她的憂慮,覺得謝仁慈呈現的自我形象有時過於正面,並不總在反映真實的生活狀態,「她有時呈現自己也做不到的事情,例如跳舞。她說她其實跳不到舞,是為了拍攝不得不做,因對方給她提供更好的義肢」。為了挑戰大眾的認知,她經常突顯自信,汪春春擔心當撕掉「包裝」被看作一種絕對的自我解放、一種過於美好的事情,會簡化截肢者須面對的困難。「仁慈的形象是大多數人沒法做到的,她受高等教育,有她的文化和社會資本,其他人到底有沒有能不能,我不太清楚。」
汪春春說,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小腿義肢,在最好的身體狀態下,能恢復的功能也只有60%至70%,大腿約40%。在康復中心考察時,她觀察到身體狀况對使用義肢的表現影響很大,「如果不能保持平衡,或者擔心用義肢很痛,他們會把大部分功能交給身體健康的那一邊,所以可能一踏出去,義肢那一邊只輕輕作支撐,另一邊腳馬上踏前,會出現很顛簸的走路狀態。」而安裝義肢前後,截肢者須做一段時間的物理治療,包括訓練肌力和平衡力運動,「訓練過程其實很累,須消耗體力去尋找和適應與義肢的配合,還要忍受疼痛」。她說,大多數人首次穿戴義肢都感到「很痛」,「因義肢按比例壓縮,感覺很緊,加上痛感幾乎是無法處理的。技師只能視乎部位微調,稍微放開一點點」。
接納身體 改變與限制
要持續訓練體能,學習與義肢協調,生活上的困難,不僅如此。汪春春說除了義肢本身的功能和公共設施配套,社會對殘障者的評價往往對截肢者外出造成更大的限制。她另一主要研究對象是個二十五歲年輕人,遇上車禍,截肢手術後回家休養,「有人給他介紹對象,對方是個有嚴重精神疾病的女生,旁人勸說,認為女生有病可能會拖累他」。汪春春藉此指出截肢者面對狀况的複雜性:他們有時會遭受歧視,即使被接受和理解,善意對待卻可能依然不公平,叫人難受,「會針對他的身體,評價他的人生,例如假設他須依賴另一半,也因其身體判斷他應該跟有精神疾病的人一起才匹配,這對雙方都不公平」。
「我覺得要看到穿戴義肢可給他們帶來的改變,是積極的,以及不可帶來的改變,可能是一些功能上的限制,在他們需要幫助時提供合理的幫助,在看待他們時不要以身體作為看待的標準。身體只是身體,身體殘疾只是身體給他帶來一些不便,不代表他的能力低下。」說回研究初衷,汪春春希望通過身體重新反思文化的邏輯,呈現殘障者生活的狀態,以及這些「超越穿戴義肢」的狀態在社會層面如何產生,「希望大家明白,並接納身體的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