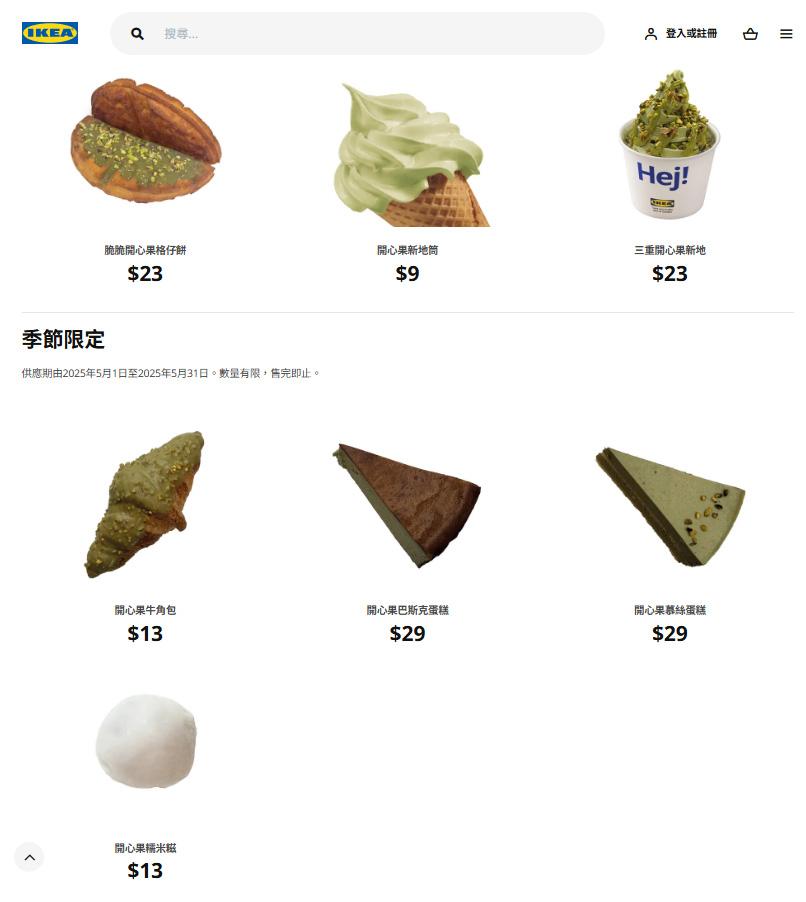【明報專訊】去年七月底,一個尋常午飯時間,記者在銅鑼灣港鐵站月台上親睹一名OL突然受驚抱頭蹲下,原來是有個男生為趕上列車而在她面前跑過,這一反射動作,令人不禁猜想她曾經遭遇過什麼,畢竟連串研究調查發現原來有精神創傷的香港人,比例不少。
港大醫學院精神醫學系早前發表調查結果,發現在社會運動和疫情雙重影響下,約36%受訪者同時出現中度至高度抑鬱症和創傷後壓力症(PTSD)症狀,即每三人便有一人。究竟疫情之後,精神治療制度可以如何改變,社區又可以如何自救和互救?
反修例創傷:
林婆婆•元朗創傷後遺需輔導
六十五歲的林婆婆很愛美,耳垂戴着三隻精緻花耳環,衣領掛有紫色太陽眼鏡,用透明花紋化妝袋裝着防疫小物,大概是因為昔日經營美容院,習慣了對衣著細節一絲不苟。性格開朗的她說,這一年無法露齒大笑,因為去年7.21元朗事件中,她為躲避白衣人襲擊,在元朗站樓梯摔倒,膝蓋跪地,也撞到嘴巴,下排沒了兩隻牙。原先預約好整牙,又因疫情關係要延期。
雖然在訪問時,她不時輕鬆談論家常,但其實在7.21後連續兩星期,她無法進睡,也無胃口進食,只要靜下來就會落淚,其後確診患上PTSD,需要每天服用精神科藥物。現在憶起當日畫面,她仍然會哭:「我行樓梯落去,見到有好多人、好恐怖、好密集,他們兇神惡煞地拿長棍打人和跑上來,我想折返月台,又行得不夠快,我記得有幾個年輕人在我後面想扶一扶我,豈料就是為了幫我而被打,我覺得我連累了他們……」
現在情緒好點嗎?她說今年六月開始逐漸不再需要以輪椅代步,減輕了對腳傷的擔憂;現時會持續到公立醫院覆診取藥,亦會見私家心理輔導,正慢慢康復。但始終社會發生太多不開心事件,她說難以心安。
譚蕙芸•「病識感是救命草」
予人感覺幹練的自由身記者譚蕙芸說,在採訪反修例運動期間亦自覺受情緒困擾,尤其在理大衝突後,她發現有段時間無辦法和沒去過現場的人聊天,「覺得好忟憎,只能夠和經歷過的人傾偈,否則會覺得不被理解,又覺得無能力解釋」。加上她最近要照顧患病家人,令情緒跌入低谷,需要尋求心理輔導協助。
空談叫人有希望無用
但她亦自覺幸運,在反修例運動時精神健康儲備足夠。她回溯起十年前,曾因左耳突然失聰和耳鳴,致失眠數月,萌生自殺念頭,幸而當刻意識到要找朋友幫忙,「病識感真的是救命草,平時要有留意精神健康資料,打好底」。吃一年藥治療抑鬱症,再花上三四年時間靠做瑜伽、靜觀和寫作才真正脫離。「精神健康其實都是要先搞好機器,回到基本,睡好、食好,做運動都好緊要。」
人們總說要心懷希望,但香港的前景如何令年輕人看見希望?她說幸而自己在雨傘運動後港人消沉的數年裏,看過不同國家的抗爭歷史,知道台灣、韓國等地無不以數十年抗爭,才令她不至於被無力感壓倒。「空談叫人有希望是無用的,都無希望。為什麼現在創傷會更加傷?因為現在已經幾乎見不到明刀明槍的對峙,但社會不讓你表達感受,連掀開傷口找水清洗的機會都沒有,無人能肯定是刀傷、瘀傷還是無傷。創傷最大未必是受傷這件事,而是沒有面對這件事。現在怎會談希望?跳得太快了。」
但看歷史、做靜觀都需要靠平日累積,如今要如何急救?她呼籲「為自己做一些事情吧」,即使是再渺小的行為,下樓買份報紙也好,總好過坐在家中覺得做什麼都無用。「去(法庭)旁聽啦,我認識OL太太告假去旁聽。這些小故事,會令人發現還有人在堅持,不可以被想摧毁我們行動念頭的人得逞。」
研究:逾三成人同時抑鬱+PTSD
臨牀心理學家、「良心理政」召集人葉劍青表示,因為反修例運動而求助的病人主要分成兩類,第一類是有抑鬱症狀,第二類是有PTSD症狀,PTSD常見的症狀包括長期處於戒備狀態,和出現入侵性記憶情况,即和創傷事件有關的記憶、噩夢不請自來地持續出現等。
精神科專科醫生黃宗顯說好多反修例運動病人,因為等官司過程漫長,聆訊日期一拖再拖,無了期等待令他們常常擔心自己會復發,亦不敢作長遠打算。「尤其有PTSD的人,通常是社運參與者,目睹的衝擊會大些,看電視都會有困擾,或者是家人有參與。雖然社會每一個階層都有,但年輕人居多,因為熱愛這個地方。」
港大醫學院精神醫學系在今年二至七月,用電話和問卷訪問11,493名香港市民,近半是25歲以下,73.7%受訪者出現中度至嚴重抑鬱症狀,40.9%出現中至高度PTSD症狀;當中約36%同時出現兩種症狀。和港大醫學院在一月發表的「港人精神狀况觀察性研究」比較,當時有31.6%受訪者有PTSD症狀,是次研究則達40.9%,有明顯升幅,或反映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香港人情緒問題。
疫情創傷:
隔離 標籤 不信任充斥
原來因為疫情而衍生的精神問題相當普遍,近日意大利聖拉斐爾醫院研究發現,42%新冠肺炎康復者患焦慮症、31%患抑鬱症、28%患上創傷後壓力症。根據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自1981年有紀錄以來,至2018年間,本地自殺率於2003年爆發SARS時是最高的。
SARS患者情緒恢復需數年
中大醫院行政總裁馮康曾在2003年感染SARS,其後成為「沙士互助會」創會會長。他知道當時好多SARS病人都出現情緒困擾,尤其是在疫情早期染病的淘大花園患者心理壓力特別大,因為當時染病是突如其來,毫無準備,因此很多病人一提起染病就會哭。「最初一兩年我們辦活動時都見到好多人有情緒問題,要去到第四年左右,明顯感覺到大家普遍情緒恢復得幾好。」
他自言由於當時擔任醫管局新界東醫院聯網總監,是抗疫一分子,曾親身見證過醫療團隊治癒病情最差的SARS病人,因此對於自己染病沒有太大不安。不過,他記得初時需要檢查數次才真正確診,入院後數天病情惡化得很快,連簡單落牀都感到氣促,而且治療過程反覆,最後應該亦是靠着康復者血漿治好。雖然只是三星期就出院,但康復過程仍要面對種種不確定,始終SARS是新病症,當時沒有人知道病毒會否長時間影響肺功能,或是有不少病人因為接受過高劑量類固醇治療,而出現骨枯和其他副作用。
他說雖然都是傳染病,但今次疫情有一些不同,好多精神健康問題還包括公共衛生層面,例如感染人數較多,居住在疫廈要如何清潔家居,亦擔心確診後被隔離、被標籤,鄰居疏離、排擠、不信任。而且疫情時間長,要保持身體距離、要在家工作,是一種生活上和經濟上的破壞。而中大醫務中心亦發現疫情第三波出現的社區問題比之前多,「因為第一、二波好明顯是由外地輸入的個案,第三波好像在社區擴散,要做好多企業支援,有些公司打來說,員工的家人樓上確診要怎麼辦」。馮康說其實注重個人衛生、勤洗手就不用太過擔心。
拯救方法:
建立信任 察覺身邊人
面對四成人有PTSD症狀,疫情過後到底在精神治療制度上要如何拯救港人情緒健康?受訪者都表示,香港精神治療制度必須走向社區模式,馮康說人們總將公立醫院精神科輪候時間長,視為精神治療制度好大問題,其實是將問題向精神科專科傾斜,但絕大部分病人只需要見心理學專家即可紓緩病情,「大部分有情緒問題的人看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應該是集中去看金字塔頂端、有嚴重精神病的人,用藥物介入」。此外,屋邨私家醫生接受的全科醫學訓練其實都包括精神健康,可處方簡單藥物、醫治失眠等。而企業和學校亦需要關注員工和學生的精神情緒健康。
可先看心理專家 勿傾斜精神科
黃宗顯指出,澳洲模式是慢慢將住院服務轉移到社區照顧,但需要好多人手和專家資源支援,他在公立醫院任職十七年精神科醫生期間,院方亦曾嘗試發展家訪形式,但後來同事都說工作量愈來愈重,變成每次家訪亦流於形式。他希望醫管局思考公私營精神科服務合作,而私家醫生亦可以多走一步,主動和學校或社工接觸,例如反修例運動中不少病人都是由學校轉介過來,或是社工帶來,不少學生好怕接觸外人,而社工往往花在他們的時間最多,亦最先掌握到病人用藥狀况,「所以要建立一個信任,中間人角色都好重要,好多時都是一個被捕人認識另一個在看醫生的被捕人介紹,自己會比較相信同行人,多過純粹在醫生名單中隨便找一個,他們不會的」。
葉劍青則表示,公立醫院精神科輪候時間長,私家醫生收費貴是不爭的事實,因此他們都在尋求轉型的方法,主要從社區層面出發,包括現在和地區組織討論開班傳授自己照顧自己心理的方法、將「心靈照顧站」遍地開花等,「簡單來說就是自救與互救,平時在網上看多一些照顧自己的資訊,不要將自己認知那套強行硬套在別人身上,還有餘力的就幫忙察覺身邊人的情况」。
最後葉劍青強調,任何治療的第一步都是聆聽,好希望大家可以好好聽身邊人說話。黃宗顯亦說:「人們現在都了解到精神健康和社會是密不可分,希望有機會可以重建和年輕人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