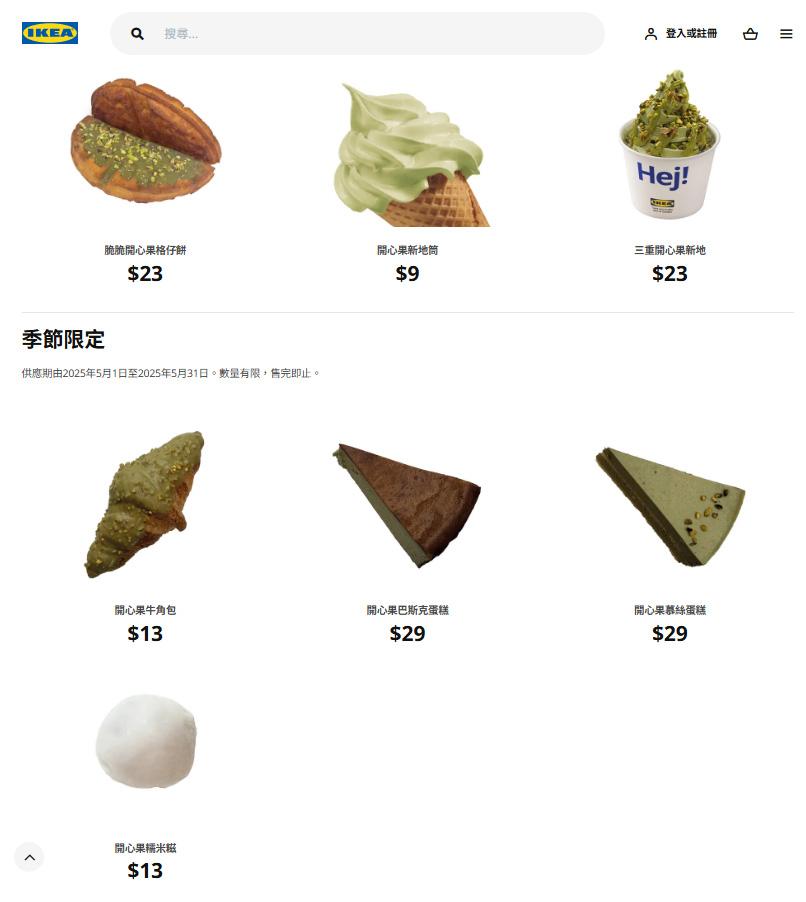【明報專訊】二○○五年一次訪問中邱剛健說過,「我認為(電影)劇本可以獨立存在,變成小說、話劇一樣讓人們獨立欣賞的東西。……電影劇本怎麼變成讓人獨自欣賞的東西,實際上有人做到了,《廣島之戀》做到了,同時是很好的電影,也是很好的文學作品」。想像他聲色厲言──電影劇本可含文學底蘊,足見分量。涉獵中西文化深邃廣袤的邱剛健二○一三年辭世後,他的劇本陸續出版,除早期作品、八十年代前後新浪潮時期的作品外,剛於本月出版的《再寫經典──邱剛健晚年劇本集》,便收錄他晚期二○○三年至二○一三年病榻牀上仍不怠創作的手稿原樣。有別於上部收錄他在港較為人熟知的新浪潮作品:《地下情》、《胭脂扣》、《人在紐約》和《阮玲玉》,此次展露的大都是他從未曝光、未拍成電影的劇本。我們請來此書策劃人之一羅卡及主編喬奕思,細說這位風格別樹多樣的編劇家、詩人的晚年創作及此書出版緣起。
六十年代在台灣創立前衛雜誌《劇場》引介各種西方思潮與戲劇、於各文藝場域發表先鋒作品的邱剛健,受邀到邵氏擔任編劇工作,至他最火紅熾盛的八十年代,多部作品皆以筆名「邱戴安平」面世,「故後來知道這是『邱剛健』的人不多」,羅卡等人在他逝世後,跟其遺孀趙向陽女士商談,發現留下手稿眾多,認為邱剛健「最具創作性的其實是手稿、未被改動的原貌」,尤其劇本於他迹近「文學創作」,「需逐字逐字、逐場逐場的斟酌,全不喜歡別人改動」,故認為「手稿才是他的遺願,最合他心意」,自六十年代相識邱剛健的羅卡如是說。遂出版《美與狂:邱剛健的戲劇‧詩‧電影》、《異色經典:邱剛健電影劇本選集》後,這部包含晚年未被拍成電影的劇本集——改編自托爾斯泰小說的《復活》、背景設於香港的類型片《罪人》、回望早年經典《胭脂扣》寫成的遺作《胭脂雙扣》,及改編自莎劇《王子復仇記》、拍成《夜宴》卻被大幅修改的《寶劍太子》,尤具價值。
邱剛健一生創作豐饒,除影視劇本逾百部,也有詩歌和戲劇,綜合看始能完整呈現一個「作者」(author)的藝術世界。邱剛健在世時紙本出版卻只一部於晚年二○一一年出版的詩集《亡妻,Z,和雜念》,逝後友好於二○一四年為他出版第二部詩集《再淫蕩出發的時候》。接連參與出版此劇本書系的喬奕思說,自二○一八年出版劇本集《異色經典》,「那年在台灣大家開始很關注邱剛健的創作,發現了他的獨特性,台灣清華大學舉辦了特展,討論他的詩歌和電影劇本創作」,其時不少詩人及評論人對他的詩作亦有高度評價。在他出版第一本詩集時,也「表現得非常高興」,其時雖未有出版個人劇本集,卻見他「看待出版創作的態度極為認真」,後來在讀《寶劍太子》手稿時更「發現他寫得非常精細,一個字都不用改,他對待創作的認真程度,是達到直接出版的水平」。
隱居細研古籍 晚年反芻中西
經過八十年代創作巔峰,完成自編自導的前衛電影《阿嬰》後,九十年代邱剛健與家人移居紐約,尤在一九九五年愛妻蔡淑卿病逝後步入漫長低潮期,十年間創作一度停滯。一九九五年後更搬到紐約鄉郊隱居研讀中國古籍、古詩詞,「當時他家中只一個皮箱、一張牀墊,非常簡陋」,似乎頗不得志,喬續說,在二千年初他從紐約移居北京,「如卡叔(羅卡)所講,只是我們沒想到,他晚年創作力其實依然勃發,未有枯竭,即使在北京未能找到知音,仍不懈創作」。新書挑選的四個劇本,可說是他晚年最完整、「最能表現其『作者』特點」的電影劇本,「當然他晚年創作不限於此,也做劇本顧問、寫下不少電視劇本,但以完整性、藝術性而論,這四個劇本當之無愧」,惜有一部因版權未能收入——改編自《聊齋誌異》的劇本《倩女一千年》,「精彩程度跟《寶劍太子》相若」。
「《寶劍太子》是他晚年力作」,羅卡直道,也是他生平最後一個獨力創作完成的全劇本,《復活》、《罪人》、《胭脂雙扣》皆由邱剛健及其晚年伴侶趙向陽合力完成,四部劇本無論在文字或題材上均見風格多樣,「邱剛健多次談到,一個編劇應該任何風格的劇本皆能駕馭」,喬奕思舉例說《寶劍太子》古意較濃,從中也可見他在紐約隱居「沉澱後迸發出來的創作激情」,「當中有中西交匯、現代古代的交匯」;《罪人》則是警匪片,初由陳翹英寫故事大綱,設給周潤發去演,情節與節奏不屬文藝,「不是那種能慢慢細味、講究詩意的」,羅卡接道,雖然風格不同、是二人合力執筆,「但依舊嚴謹」,逐字修改完稿。
在晚年創作高峰(約二○○三至二○一三年)與較早年之間,相距約十載,若談晚年風格與以往之區別,羅卡會說,譬如八十年代多與邱合作的導演關錦鵬,多喜愛「文質彬彬的節奏,男女之間柔情悲情那種」,「是文藝、接近歐陸藝術片,在文藝之中提升格調,而普通人也能接受」,直至邱晚年,或與個人修養、曾隱居研讀古籍有關,「他對中國西方內涵經過反芻、反省,相對比較成熟,很熟練淡定,也講究咬文嚼字,是不論拍成電影與否亦可刊登的文學作品」,有異於新浪潮時期,那時「劇本沒那麼講究文學性,較多即興元素,較多所謂『美與狂』」。
沉思人之將死 逝前創作不倦
所以說劇本是否拍成電影已非如此重要,「邱剛健曾言寫好劇本後,就如腦海裏拍了一次電影」,喬奕思續指,他很懂得調整自我、與人合作,遺作《胭脂雙扣》「基於個人的創作,呈現許多內心世界,亟需尋到知音,而這個知音到底是電影製作上的,抑或作為文學作品的知音,也許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有人看到他的藝術世界」。《胭脂雙扣》固然跟他與關錦鵬的經典舊作有緊密聯繫,暗地重扣梅艷芳與張國榮的故事。其中《胭脂一扣》故事發生在邱剛健的出生地:鼓浪嶼。八歲才跟家人移居台灣的他,晚年多次回到鼓浪嶼,「在與趙向陽的訪問中,她談到邱剛健當時希望找回童年居住的老宅,似乎把晚年尋根的感覺,置放在這故事裏」。當中女角李夷,亦被投放許多邱剛健對太太的感受,「這種人之將死的感覺,例如在《地下情》周潤發的角色亦可窺見,但沒有《一扣》寫得殘忍,李夷半身不遂,要她愛人照顧,趙向陽提到邱剛健特地寫這場戲,因他認為愛不止是浪漫式,而是你要在生命不同階段,面對那種痛苦與複雜」,據說李夷這角色便灌注了當時邱剛健在紐約照顧病重妻子的情感。
《胭脂雙扣》是邱剛健病榻時仍孜孜創作的劇本。二○一三年入院、十一月病逝以前,羅卡及喬奕思與邱剛健一直有聯繫,其間更商討籌備他七月來港參加的座談會,當時無論在電話或碰面期間,邱剛健也都精神煥發,「全無死亡預兆」,及至五月收到他信中寫到身體現毛病,座談會方取消,羅卡說,「這段時間他仍一直寫作,看《美與狂》收錄他與劉大任的通信可見,他並不是說很痛苦、急救後又救回、要曬太陽坐輪椅那種,而是一有活動能力便去寫作」,那時年逾古稀的邱剛健或有所打算,「但他不以養病或恐懼來迎接死亡,而是寫詩、寫劇本,持續深化他的創作,作為生命的最後意義,他是有意識如此與病魔鬥爭,具有作家本色,以寫作完成生命」。
死亡,也是他創作的重要母題,孳生自早年作品。回看他早期的詩、戲劇或電影劇本,「他對生命的激情、怪誕的美、極端之對立與穿插,其實一直存在,譬如他的詩作《洗手》,把宗教、性、血以一個簡單的動作『洗手』貫穿,他向難度挑戰──如何在一個場景中讓人同時感受死亡、生的喜悅,那種高潮?他渴望將那複雜情感,高密度地集中在一個場景」,這是在讀他的詩和劇本時,予喬奕思的感受。
早上劇下午詩 詩劇互為表裏
關於他晚年生活及創作節奏,大概除了書中收錄與晚年摯友畫家楊識宏的訪談,及與趙向陽的訪談外,現時或難了解更多,而趙向陽本人於本月初剛辭別人世。當中講到,邱剛健有個創作宗旨,就是「他每天必定要寫字」。晚年在北京時,「他每天早上必然坐着寫劇本,即使不順遂也要坐着寫,到吃過午飯後,下午開始聽古典音樂,寫詩」。他晚年留下各種文字,詩歌、劇本及日記。日記雖是純粹記下每天所作,「但這習慣非常驚人,趙向陽那邊所收的,包含他從九十年代至逝世時,天天寫的多本日記,從沒停頓」。除了天天必定寫字這習慣,喬續指他相當注重要從不同藝術領域汲取養分,「在紐約那段日子沒留下創作,但楊識宏常帶他到處看畫展,他對畫作和當代藝術也深感興趣」,例如楊識宏提到他喜歡的存在主義雕塑家Giacometti。在劇本當中,「亦見他構想的畫面充滿構圖」。
邱剛健在生時出版的詩集,封面亦指定用楊識宏的畫作。近日新出版的晚年劇本集也在封面及內頁用到楊識宏的畫,「首先是邱剛健喜歡,其次是他的劇本風格與楊識宏的畫有某種神交之處,事實上他曾多次以楊識宏的畫作入詩」。封面畫作題為《存在的痕迹》,「那意象和氣息都非常之邱剛健」,喬奕思續釋,選畫過程除了由趙向陽幫忙,跟楊識宏習畫、邱剛健的兒子邱宗智亦有參與挑選。
所以,邱剛健的藝術世界需要更整全地觀看,除了畫作與音樂對他的影響,他創作的詩和劇本也存在互為表裏之關係。「他的詩作你會看見突然一個點子,突然一個意象,那作法非常電影,想像力具體,有聲有畫,直頭是噴血般『劈』一聲腦漿塗地的」,殘忍至美的程度,羅卡說,他詩中「也富節奏與速度,那是受電影的影響」。若說電影中的詩意,羅卡認為電影較難拍成詩的模樣,最接近的他認為是《地下情》的「心隨意轉」,「即非理性地根據大綱發展」,有些場面如詩,忽地去到某種情緒,「沒有鋪展,這在詩中是成立的,就是在生命中所發生的突然爆發」,也是跳躍即興,「卻跟情緒很配合,如意識流,是近乎文學實驗」。其他例如《唐朝綺麗男》及《阿嬰》等,也有類近詩的嘗試。「一個是上午寫劇本的邱剛健,一個是下午寫詩的邱剛健」,也都「忠於自己的『作者』風格」,喬補充說。
自我超越 追求創新
無論參與什麼片種製作,邱剛健也是別具個性的編劇家,忠於自身創作同時,也要突破求新。在《寶劍太子》中喬奕思略見早期創作《唐朝綺麗男》《唐朝豪放女》的淡迹,可是,她感覺這跟他八十年代所取的唐朝有別,《寶》「取的是五代十國,盛唐以後,跟他早年的盛唐氣象有所不同,而在《倩女一千年》他寫及許多朝代,卻避去唐朝,包括那營造的意象、視覺上的風格,迥異於唐朝那豐腴、性感和奔放的感覺」,她認為晚年的《寶》帶有蕭索之感。羅卡續釋,邱剛健慣於規避固有事物,「他情願聽音樂、看畫,也很少看別人的電影作品,尤其是當下流行的」,他追求創作的是內心所想,根據幾位與他關係密切的人透露,他寫完一場戲後,若有人跟他說劇中情形猶如某部外國片,「雖然他或未看過(那部戲),但這場戲他會撕爛重寫,即是他不希望受任何片影響,甚或移植過來,他要的是獨創」。喬奕思由此延想到邱剛健的詩作《伊人》,其中寫到:「好像年紀愈大,愈覺得自己的一切都是二手的,借來的。/像剛才我忍不住叫起來的時候,我清楚地聽到/我的叫聲裏面也有我看過的好萊塢電影」,喬認為這表達了邱剛健內心鬥爭,而她認為,他享受這掙扎,「對他來說,這就如他寫的詩,帶給他複雜情感,有痛苦,但這痛苦通向的是創作的滿足」。
打破俗見 女性自主
雖說在形式、表現手法、意念或內容上求超越自我,一些創作母題往往讓人念茲在茲,反覆揣琢。從早年至晚年,邱剛健持續寫到死亡、性、情慾、殺戮。談到劇本中表現的性與赤身,喬奕思說這是「意淫」,「是意識上那種性,非粗俗的,在在挑戰我們對性的普遍認知」。如他早期探討女性形象與性的經典作品《愛奴》,至晚年創作,性亦與精神相通,喬舉例指《復活》的主角林海燕與陸誠,在他們經歷悲戚複雜的情感後,劇末他們在雪地脫衣,赤身於雪中為對方擦洗,「這場戲的確是裸體,但你看到的不止肉體本身,而甚至讓人感到神聖」。她續談《罪人》的破俗處理,其中男主角羅白和女友秀娟,與十一年前被羅白誤殺其母的Mika,三人最後睡在一起,「這讓人感到曖昧,似乎難以界定三人關係」,喬認為他要打破我們日常對性的俗見,澆以精神內涵。
談到女性形象,羅卡說到他們當年一代影評人揣思如何評價《地下情》女主角阮貝兒(溫碧霞飾)的趣事,由青春迷惘到勇敢灑脫,及至晚年的女性形象,似乎始終如一。喬奕思接指邱剛健寫的女性精神內核,「皆是現代的,非傳統道德——女性要害羞忸怩那種」,而是不論朝代氛圍或服飾形態,由《愛奴》、《地下情》、《阿嬰》至《寶劍太子》,皆充滿現代感。《寶》中母后這角色流露「她對性的開放,對亡夫的觀念,可說是絕情,又可說是自私,以至她對欲望的迷戀,便異於莎劇原著的母后」,對亡夫不在乎的態度,打破了讀者對當時女性的既定形象。在《復活》當中亦然,邱剛健在托爾斯泰的基礎上增添「舒懿」這女記者角色,此人物以自身交換愛人所願,「但她沒有自怨自艾,因這是她自主決定」,除卻一般受害者心態。在《胭脂雙扣》中,也有個讓喬奕思留下深刻印象的女角色崔穎,當中「甚至可見邱剛健前期作品中許多影子」,對於性、愛、情絕非從屬者──這種現代女性的形象,始終貫穿他作品。
隨遇而安 與己戰鬥
〈後記〉中趙向陽寫及邱剛健與她合寫《罪人》時極為用心,非常希望為香港電影注入一絲活力,並「一直企盼香港的電影能夠像新浪潮時期一樣」。《罪人》背景設於香港,當中的地景建築與香港密不可分,喬奕思舉例說有「電車、斜坡和天台各種元素」。而書寫《罪人》,於早期在香港創作豐盛的邱剛健而言,「也特別難得,他非常高興又可以寫一個香港的故事」。
從鼓浪嶼、台灣、香港、紐約,至晚年北京,每個地方居住十年或以上的邱剛健,從他的作品以至交談中推算,羅卡說,「他不太重視身分,反而不願被環境、身分綑綁」,但不等於他喜歡旅遊式的探索追尋,「而是隨遇而安,有什麼困擾壓迫的事,便走往別處」,每個地方定居一段長時間,「他生活規律,有他個人的小世界」。喬奕思想到一首他晚年寫過的詩《歸人》,用以詮釋:「他回頭,想繞過自己/走入東西南北的胡同」──他,始終是繞過自己,「與自己交流,與自己戰鬥,用文字去打造自己的藝術世界」,這路徑於他,也許最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