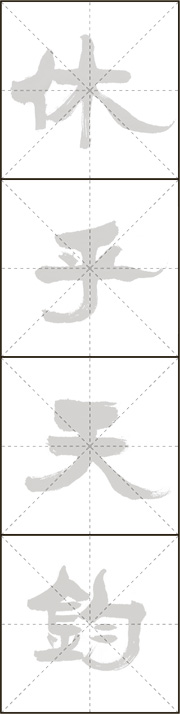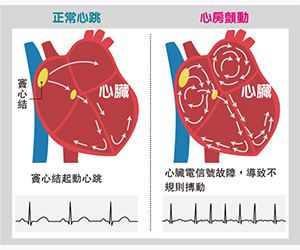【明報專訊】近來阿甘發夢離不開3大類,「一類探監啦,一類是跟家屬傾偈啦,另一類就是坐監」。他在過去幾星期特別忙,先為47人上庭籌措還押的緊急物資包;庭內保釋申請搞足1星期,又要天天朝8晚11守候着隨時提供支援;理大事件被告陸續上庭,也要做足準備。「石牆花」自去年年底邵家臻失去立法會議員身分後正式運作,全職員工只有3人,甘鎧仲(阿甘)是其中一個,也是唯一不是社工的一個。一入石牆花在荔枝角的辦公室,猶如一個雜貨店的倉庫,6個貨架上疊起一大堆「祝君早安」毛巾、一排排黑人牙膏、一條條Tempo組裝紙巾……他熟練地介紹,毛巾呢,「祝君安好」唔得,標籤不是「AA0008BY」這種厚度都唔得,他現在用手一摸就知道;魷魚絲呢,7g先得,平時多買到的是14g、21g,「你都唔知時興隆點解要出咁多隻,哈。」紙巾易買喇卦,看上去跟在超市見到的沒兩樣,他說這是長條形的,不是我們常見短身那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