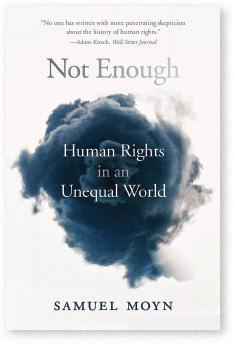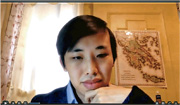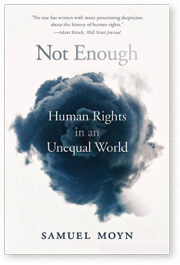【明報專訊】各式各樣的社會議題當中,權利的講法總是出現在不同的政治立場裏,似乎不同主張的人都有各自的權利自由需要社會尊重和保障,即使彼此的權利可能互相衝突。
例如在美國,人身安全是基本權利,但同時許多人又高舉持槍自衛的權利;疫症下人民的生存權是權利,但同時一些人會認為拒絕戴口罩都是權利。人人心目中都有自己一套權利,且得提防着其他人的侵害。這便是奉人權為圭臬的理想世界嗎?抑或人權作為道德政治的想像並非只限於此?人權還可以是什麼?
為此,筆者特地訪問耶魯大學法學院和歷史學系教授Samuel Moyn,看看他在新書《不足夠:在不平等世界的人權》(Not Enough: Human Rights in an Unequal World),如何覺察到人權論述在當代的不足。
人權不應只是維持人的最低生活水平,確保生命能存活下去,更應該回到思想史中,看看人權如何在很長時間作為人類政治的理想追求,又如何在歷史的跌宕中化成今天的模樣。
人權史的書寫淵源
早在十多年前,Samuel Moyn已經開始書寫人權思想史和政治發展史,且不同於一些主流觀點把現代歐美歷史的民主化看成人權勝利的發展史,他更着眼於人權發展的不同層次、不同地區的差異。但到底有何原因驅使他書寫人權史呢?「其實早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攻讀博士學位時,我已經對人權的議題很感興趣。當時是九十年代,冷戰剛剛結束,當時全世界的氣氛都是一片歡騰,覺得是民主化或者人權發展的里程碑,我也是順着大時代的氛圍,開始對人權這個議題產生興趣。」
不過相比起一些典型的人權史論述著作,Samuel Moyn似乎另闢蹊徑,走上另一種不太尋常的左翼方式書寫人權史。「那時我還在法學院讀書時,因着當時的興趣而上了些關於人權的課程。但當時我已經感覺到那種對人權的論述缺乏批判性,所以我暗下決心,有朝一日在大學教授歷史時,會嘗試通過著書的方法,以了解為何學界會對人權發展的想像如此狹隘。」因此,從2010年出版的《最後的烏托邦》(The Last Utopia)、2014年出版的《人權與歷史的運用》(Human Rights and the Uses of History)一直至今,他不斷書寫人權在歷史的發展是如何敘述出來,同時忽視了什麼,帶來了什麼假象。
法國革命的人權理想
在《不足夠》中,Moyn提到早在十八世紀的時候,作為激進思想的人權觀,可不是只要求有投票權或者言論集會權利,思想家爭取的可是「飽足」(sufficiency/ sufficientia)的權利。「飽足這個概念是現代才出現的政治概念,跟一神論的耶教信念有關。」Moyn斬釘截鐵地說。舊約聖經《箴言》有句說話,「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使我也不貧窮、也不富足,賜給我需用的飲食」(30:8),一神論的教導是上帝會供應飽足,飽足才是真正的幸福,而非富有。而英國傳統的議會立憲,甚至是獨立後的共和美國,都是奉行古典的政治信念,即確保社會上不會有太多極端貧窮或者富有的人,從而使社會趨向穩定,但平等的飽足作為政治理想是不存在的。這得待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才出現這種現代新式的政治想像。儘管雅各賓派主導革命的時間並不長,且往後也隨着恐怖統治而盪回帝制的一方,但當時掀起的有關社會公義的討論和實踐,對於公民如何在社會享有平等的飽足權利,其指向的福利國家甚至福利世界的管治模樣,在革命後持續以不同面貌再現。
雅各賓式的福利社會可理解為「資產擁有者的民主」(property-owning democracy),但不同於英式的地主階級議會制,雅各賓黨追求的是確保在社會中所有人都擁有一定數量的土地,以及參與經濟活動的能力,並提供公平的收入作為支援,確保所有人都能得到相應的公共利益。因此,他們的民主是把所有人都提升為資產擁有者,從而實質地體現政治和經濟的自主。畢竟如英國社會主義者拉斯基(Harold Laski)所言,雅各賓黨揭露了貧富分明的世界是基於制度的安排,因此人同樣能以平等的原則重新安排制度。「社會主義對人權的理解,在二戰前一直以不同方式追求飽足的政治理想。」只是雅各賓黨的激進結果平等主義,漸漸被福利世界所取代。
四種自由
19世紀是社會主義發展的高峰,在英、法、德、奧、意、美等地方都承繼着法國大革命的未竟之志,各自走上批判現代化和資本主義、提出不同政治經濟新可能的年代。如法國在1830年代,路易-菲利普一世剛剛在位之時,有個「人權俱樂部」(Société des droits de l'homme)乘勢而起,其宗旨也是呼應1793年的《人權宣言》,追求一個平等分配的社會,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最大的幸福,而不是單純半死不活的生存。後來高舉社會權利的著名社會主義者如傅立葉(Charles Fourier)、路易.布朗(Louis Blanc)或聖西門(Henri de Saint-Simon),更別說是馬克思及其後的左翼發展,也是呼應着相近的權利想像。
而對於Moyn來說,這種人權思想發展的分水嶺之一,是美國羅斯福總統的新政及其「四種自由」(Four Freedoms)的宏願。人所共知,1929的經濟大蕭條把美國逼入前所未見的寒冬,也因此迫使美國開始進行財富再分配,擺脫持守逾百年的經濟放任原則。不僅提供福利,更加通過「睦鄰政策」支援拉美國家,促進雙邊經濟發展。因此羅斯福新政不是單純國內政策的改變,更是一種跨國的福利世界模式。而他1941年於聯合國上發表的「四個自由」演說,是作為美國第二波權利法案的先聲。其中「免於匱乏」之自由,更成為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納入條文所保障的最低生活保障權,將權利由基本政治自由擴至社會權利。這對Moyn來說也是雅各賓式政治理想在當代的體現。
如今.從飽足降至最低保障
今人常把《世界人權宣言》作為人權發展的巔峰,作為戰後國際社會重建的基本原則。「在我過去的閱讀中,發現書寫人權史的較少注意到戰後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解殖運動,但明明那裏才是真正把人權化為政治行動和動員的口號,從而在戰後美蘇主導的冷戰秩序中,爭取政治和經濟自主性。」戰後的眾多亞非國家領袖,同樣意識到政治自主不能缺少經濟自主,而資本主義秩序下的經濟自主,只能通過在全球推動社會主義改革,讓社會福利成為全球管治的方式也有可能實現。因此由萬隆會議到非洲統一組織,前殖民地國家紛紛組織協調,以便跟跨國企業和帝國秩序競爭。只恨這波人權革命只能維持至1970年代,因着各種原因而慢慢消弭。「國際經濟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在1974年的聯合國大會上通過認可,試圖取代「布雷頓森林體系」成為更平等的戰後經濟秩序,結果40年後我們見證到的只是新自由主義的勝利,社會權利倒退到保障窮人存活的最低保障,以確保市場利潤的最大化。
例如近40年間的中美之間,各自以不同方式演繹人權,為其國家發展背書,打着人權之名為市場自由化大開勝利之門。Moyn認為中國自毛澤東死後的經濟改革,把政體蛻變成新自由主義式的後期社會主義國家,以國家主導的經濟政策推動市場自由化,從而產生巨額財富,但代價是國內的貧富差距迅速拉開。政府所強調的往往是民眾的生存權,先顧及溫飽才能兼顧更多權利,以此來忽視新自由主義下帶來的極大貧富懸殊,且因而觸發的社會矛盾和生活困難,更不用說威權政治力量如何大力打擊公民社會與各樣政治社會權利。另一方面,美國民間組織和左翼政團過於強調身分政治的重要,忽視了小眾身分權益和國家財富分配的巨大關係,面對社會不同面向市場化的巨大壓力時,人權組織和運動更是前所未見的薄弱,因此我們看見一幅戰後的奇異現象,當社會主義論述在公共空間不斷減少時,人權論述卻以倍數增加,伴隨着的是市場自由化和福利稀有化的狀况(假定當中無必然關係)。更不用說,美國軍事帝國主義如何借民主化和人權之名,在冷戰後不斷發動新的戰爭,戰場遍及黎巴嫩、格瑞那達、巴拿馬、伊拉克、索馬里、阿富汗之類,以人權之名的血腥味久久不散。
進步還是退步?
我很好奇,對比起典型的人權民主進步觀,這是Moyn的人權發展倒退史觀嗎?特別是被他視為最後一個雅各賓代表的美國當代思想家羅爾斯(John Rawls),也把社會權利框限在一個國家之內的分配,以至於在《正義論》中容許某種階段論,即國家可以在優先保障公民基本政治自由的過程中,犧牲其他較不重要的自由,以逐步走向公義社會。這似乎是從福利世界走回福利國家,且放棄了對福利世界的國際管治的想像。「我不會稱之為倒退,至少不是單純的進步或者倒退,而是兩者都有。人權思想和新自由主義也不是並行不悖的邏輯,只是在『國際經濟新秩序』後退回國家主義的框架。著史令我相信,不管是在疫症時期還是在經濟衰退的時代,人權運動還是可以創造新的可能的。」
■問:李宇森。留學紐約兩年,在BLM(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和疫情下見識到不少權利論述的在地衝突,人人都覺得自己有權,唔通人人都有權咩。
■答:Samuel Moyn。耶魯大學法學院和歷史學系教授,專門研究人權思想史及其歷史上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