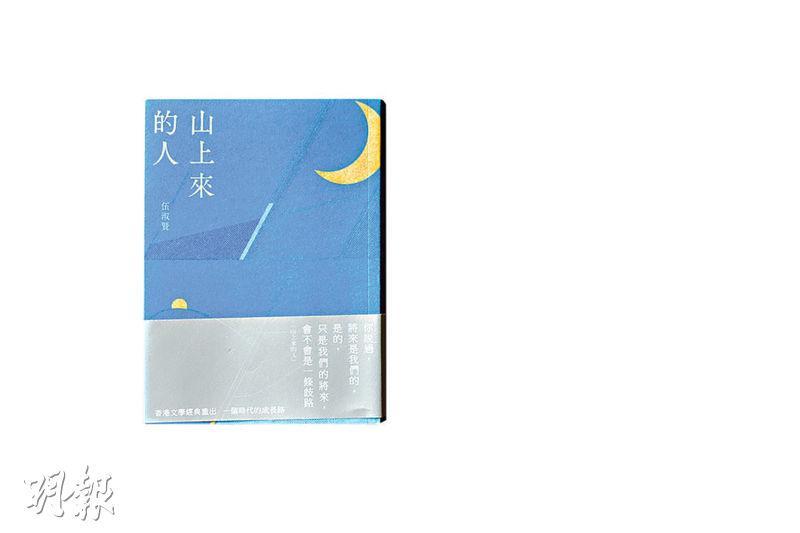【明報專訊】ViuTV的綜藝節目《ERROR自肥企画》,引來不少人討論為什麼要娛樂,以及在碎片化的時代如何提高人的專注力。記者倒是聯想到,自己有多久沒專注去閱讀一本書呢?在《山上來的人》作者伍淑賢眼中,寫作就是她娛樂自己的方法,也希望文字能娛樂讀者,而小說是一種娛樂,最重要是有生命力,能夠打動自己,打動別人;不需要用力帶出什麼信息,只是描寫世間眾生相,已經可以很有趣。
本地小說家伍淑賢由1970年代開始筆耕,直到2014年出版首本小說合集《山上來的人》,也是素葉出版社的壓卷之作,本來讀者只能在報章、雜誌等讀到她的文章,看結集更能看到她一路走來寫作的風格與關注的題材。2015年《山》在香港文學生活館首辦的「香港文學季」,與作家陳浩基的推理小說《13.67》同獲文學季推薦獎,當時館方說《山》是「骨灰級文青必讀」作品,多了人認識伍淑賢的小說,然而書籍數量不多,早已斷市。
今年4月《山》推出新版,書中分為3章,第一章收錄了3篇新作品,分別是Say Shirley、〈浣紗〉及〈戰旗〉,舊作就有〈古古〉和與書本同名的中篇小說〈山上來的人〉。第二章多是篇幅較短的文章,時間由1978年橫跨到2011年,由她在文學雜誌《青年文學》、《素葉文學》和《文化新潮》,到報章《文匯報》發表的散文皆有。至於最後一章,是〈父親〉三部曲,此系列曾被香港電台改編為電視作品。
如果人變成植物……
未提到新作〈戰旗〉時,伍淑賢已提到她家有個兼職家傭,總是樂此不疲地訴說人生經歷,諸如自己攀山偷渡失敗後懷疑撞邪等。記者聯想起〈戰〉中家傭對躺在牀上動彈不能的東主見死不救的一幕,伍淑賢說寫此文不是因為家傭開始,家傭是「寫吓寫吓突然走出來,一種結構上的方便」。〈戰旗〉原名是〈為什麼戰旗美如畫〉,句子摘自《英雄贊歌》紅歌副歌部分,也出現在故事中,這是一名唱歌老師介紹給她的歌曲。由此可見,她寫作愛用生活中信手拈來有趣的片段,她覺得每個作家都是如此。
這個故事她真正想寫的命題,是她害怕人會變成植物。一棵樹,一生都站在同一個位置,不能移動。〈戰〉的開首,伍淑賢這樣寫女主角思俊的狀態︰「她打自早上五點多醒來,發現全身動不了聲音又發不了之後,心神經歷有世紀般長。」從那刻開始,思俊只能聽家傭群姐打掃,隔籬鄰舍打開鐵閘上班,窗外斜坡上的女工高談闊論,來抄表的媒氣公司職員的聲音……像卡夫卡的《變形記》,不過換了伍淑賢口中更傳統的形式,如果用佛教的角度看,可以說是寫女主角在不能動彈的日子如何觀照自己。伍淑賢的體悟是︰「我開始老,老去最大的影響是你會覺得自己行動沒以前好,沒以前跑得快,幾千米遠的地方你不敢去,移動、行動能力是生命力的表現。」這篇文章不是約稿,在此新版合集以外不曾發表,是伍淑賢忽發奇想之作,沒有字數限制之下的創作,讀者更能從中見到她對生命的思考。
寫作娛己 才能娛人
其實伍淑賢的正職是做公關和傳訊工作。她業餘時寫作多年,對她而言寫作是為了什麼?寫作是為了自娛,而很重要的是,要能「娛己」,才能「娛人」。她形容自己寫作過程,是先有一個「策略性部署」,未靠上寫字枱,就會在腦袋裏構思,決定選材角度,從什麼人的視點出發,那時思緒像千軍萬馬,有個大概,當她下筆時「最大的戰場在那支筆」,「每次寫作都是在那個瞬間,或那段期間,你選擇什麼,或者想建構什麼」。每個當下決定都成就最後的作品。
記者像追問其他藝術家一樣,問她創作有沒有什麼目的,有沒有什麼事情想說,她說這些作品在完成的那刻開始便有了自己的生命,她跟時下有很多話想說的創作人不同,但又能明白新創作人的想法︰「年輕人,特別經過這幾年,當然是有很多信息想說,因為是一種戰鬥,或者是要爭取某些事情的狀態,我覺得是合理的,但我自己對文藝的觀點從來都不是這樣。」她以社會主義的工農兵作品為例,在那個時代,文藝是思想鬥爭的一部分,她覺得現在香港社會很多人這樣想卻不敢宣之於口。「如果你是立志這樣做,我覺得有少少是將創作工具化……我要自己的作品娛樂到自己,也要娛樂到人,如果有一個框架在,我覺得是做不到這兩點的」,框架令作品變得索然無味,也失去其影響力。
性格明快 作品「輕逸」
所以相比時下總是很沉重的讀物與藝術創作,《山》可說是個異類。數年前,作家梁莉姿形容伍淑賢的作品「輕逸」,此詞出自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的書《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輕逸」作為文學概念,可以淡化沉重的現實主題,而「輕」是精準、確定的,而不是模糊、隨興的。許迪鏘在新版《山》的序中,延伸此討論,說伍淑賢的作品有一種「簡潔亮麗」的風格,他寫道簡潔是情節鋪排的鬆緊相濟,亮麗是文字的爽朗明快。問伍淑賢是否同意自己的作品「輕逸」,她覺得自己沒有特別思考要寫得輕還是重,她倒是提起許迪鏘常說她愛用白描的手法寫作,但當然寫作時不會刻意決定這個位要用白描,「可能我性格本身如此,我比較喜歡明快的東西。當然我也會欣賞像音樂家華格納的作品,那種精心鋪陳、五色目眩的結構,我會欣賞但寫不到,因為我不是那種人」。她的寫作方法,也許與她如何觀察世態人事有關。
伍淑賢喜愛留意人的生命狀態,這點可說是貫穿其作品。在另外兩篇新故事,她也有參考身邊有趣的人物。Say Shirley是由伍淑賢欣賞的歌手關淑怡開始,講到一對母女在度假時溺斃,後者原來真有其事,伍淑賢參考並寫出這部她覺得好多生命可以同時存在又有關連、生生不息永無止境的作品。至於〈浣紗〉本來是一篇關於社區和街道的邀稿,她卻借此文寫地產經紀,因她覺得在前線的銷售員,他們的生命總是很豐富的,特別是做樓宇買賣,經紀和客人來回商量對答的時間,動輒就是數月,會有很多特別的經歷。
如果說「輕逸」、「簡潔」、「亮麗」成為伍淑賢作品的關鍵詞,記者覺得那是因為在伍淑賢眼中眾生百態都充滿生命力,讀者能在作品中見到她的澄明睿智。伍淑賢說在她的腦海裏,有一個以生活所見所聞組成的資料庫,那些事件像一個個「火頭」,而對她特別吸引的事件和觀察,就會成為她的命題,當有機會寫作,適合的時機,就會燃起這個火頭,所以什麼時候寫什麼小說,可以是很順理成章的決定。
在這本小說集,中篇小說〈山上來的人〉一向是評論人的重點,當時伍淑賢獲《文匯報》邀請寫連載小說,她就當是一個練習的園地,「那有什麼更容易的題材?當然是講中學生活,因為這是一個集體回憶,我想每個人的中學生活都很有趣的,只不過普通的中學生活以外,敝校也有些特別有趣的事情,就提供了一個好好的背景去書寫」。所謂特別有趣,是伍淑賢來自修女學校,學校急於成名,所以當時很「激進」,要求學生參加很多比賽,那就是故事中主角和朋友的遭遇,由此寫到教師學生罷課,被認為是影射1970年代修女與進步教師衝突,引發全港學潮的金禧事件。她說︰「學校是平台,真正想寫的都是其中的人,他們成長的過程。」對她而言〈山上來的人〉加入了很多價值想法和質疑,而文學是要提出疑問,為現實給出新的選擇。
「絕對本土,絕對邊緣」
文學館頒獎予2014年版的《山》時說,其作品「絕對本土,絕對邊緣」。此書的舊版買不到也不易借,伍淑賢的朋友說公共圖書館有十多人在輪候借此書,現時再版後由600減至400多頁,編輯刪去一些伍淑賢也覺得太「文藝腔」的舊文章。她寫得本土,是因為愛觀察身邊的人和生活;會寫得邊緣,是相信文學是要提出疑問;觀察、疑問,理應都是人重要的娛樂,難怪伍淑賢的作品,總有很多離奇人物片段湊在一起,讀者在其作品中穿梭,拐個彎就會遇到新鮮事,記者也實在難忘伍淑賢談起寫作,笑到雙眼瞇起一條線的樣子。她說︰「有空想想這個火,又想想那個火,我覺得很開心。」找到熱愛的創作形式,全心投入,享受其中樂趣,大概就是這樣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