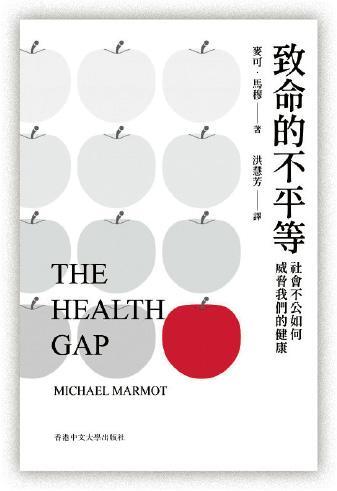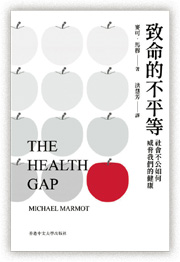【明報專訊】扶貧委員會日前發表《2020年香港貧窮情况報告》,分析計入政府在疫情下向全民派1萬元等「非恆常現金項目」,得出政策介入後貧窮率減至7.9%的結果。另一邊廂,倫敦大學學院流行病學教授、中大健康公平研究所聯席所長Michael Marmot(馬穆)著作推出中文版《致命的不平等:社會不公如何威脅我們的健康》,中大研究所亦即將發表最新報告,馬穆在專訪中談及為何他對香港情况深感興趣,而研究所的香港學者鍾一諾指出「這本書是有某程度的革命性」,因為相比起一刀切劃線扶貧的概念,馬穆強調的是社會梯度(social gradient),「從社會頂層往社會底層走,地位愈低的人,健康愈差」,除非你是最頂層1%的人,否則都關你事。社會不公平,就會帶來健康不公平,馬穆在書中說,「我們希望為健康公平性創造一個社會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