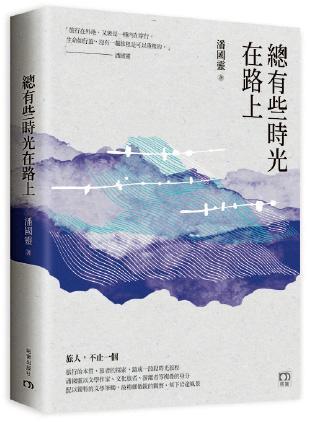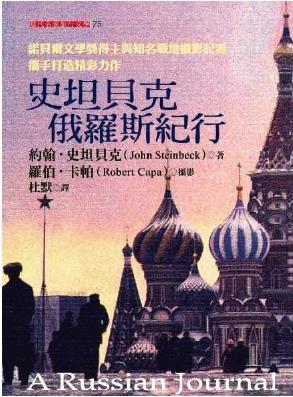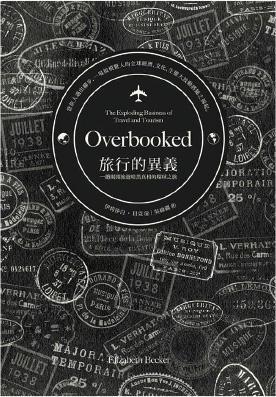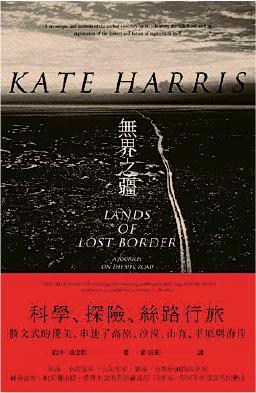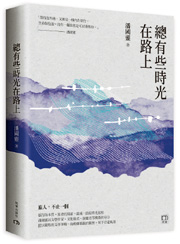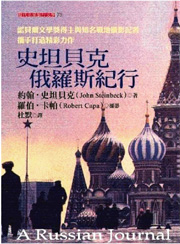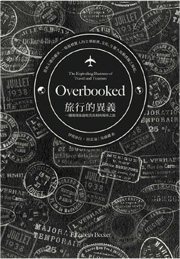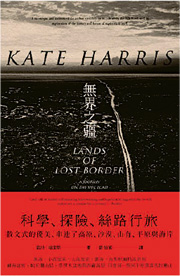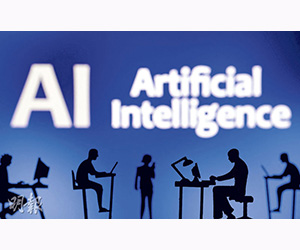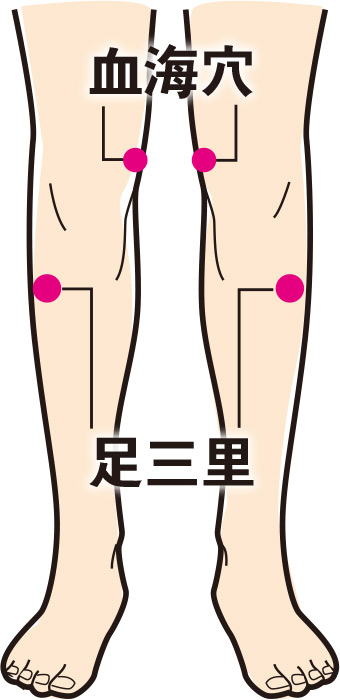【明報專訊】每個作家都有其特有的性格,這個性格可以在文字中摸索出來,也可以嘗試以hashtag一錘定音,要為潘國靈加一個hashtag,那必定是「#游走」,因為旅行就是潘國靈其中一個出口。他笑指自己是雙棲動物,需要在香港和異地之間擺盪,要自製一段距離才能繼續書寫下去。潘國靈指自己十分享受成為沒有人認識的「異鄉人」,「可以放下在香港的身分,走入異地,沒有人在意你」。現時受疫情所限,很多人無法輕易離境,往返兩地的旅行更不用說。踏足異域的自由受限,也許是很多人從未想過的景况,潘國靈也感嘆:「原來出境,你能夠選擇一個地方,以往你很容易就能做到,但是背後是牽涉一種流動的自由。」
新書《總有些時光在路上》結集了潘國靈多年來有關旅行、遊歷的文章,記錄了潘作為旅者身分的轉變,以及在異地旅途上的人生時光。全書一共八章,配以潘國靈行旅時所拍攝的照片,帶讀者一同回溯潘國靈的人生旅行。
旅者和作者之間的身分重疊
潘國靈每次離港的原因各有不同,有留學、旅區、公幹、駐校等等,「這個要累積很多才能將旅人的狀態呈現,每種狀態下的書寫都各有不同,希望可以書寫旅人的多重身分」。有時候,我們會是普通的旅客,想去當地的旅遊景點觀光,而潘國靈也有很多曾經到訪卻沒有留下筆墨的地方。每次旅行,潘國靈都會帶一本簿,記下旅行的所思所想。即使過了十多年,這些旅行記憶仍然保存完好,這些文字有的是讀書筆記、詩句、片段式的書寫。潘國靈認為寫或不寫的分別關乎旅行書寫的狀態,有時候在路上會有心血來潮想寫,就像是書中收錄的〈流浪的意義,及其不可能〉。這篇文章是潘國靈在紐約旅行途中的即興之作,寫的時候沒有想過日後會出版成書。「寫作的狀態很自然,寫字的人,想記錄或是想抒發的東西,不會滿足於拍個照留念,雖然我很喜歡拍照。」潘國靈說,他的旅行遊記很多都在路上寫的,若然留待日後再寫的話,就無法進入當時的狀態。
在新書《總有些時光在路上》裏的後半部分,收錄了較長的文章。潘國靈指這些文章需要仔細編織,召喚出很多旅行的痕迹和經歷。「我覺得寫作人有一個很幸福的地方,就是他可以活於任何時態,你的筆尖可以往返許多年前、穿梭時光。」
雖然作家可以書寫不同時空,但是潘國靈直言旅行的記憶是具有揮發性,「即使要回憶過往,也不能太遲寫」。此外,潘國靈補充還有一種旅行寫作狀態是為了寫作而前往一個地方,「香港太多教學、日常工作、答應下來的工作,寫短篇的文章時,是能完成的,但書寫長篇的文章時,會常常中斷」。他為了投入寫作,而特意前往北京而閉關,也寫成了《寫托邦與消失咒》。
重回紐約
紐約這個城市對於潘國靈而言意義非凡,在二○○七年,潘國靈獲資助前往紐約,在紐約居住一年。時間的長度為這次的旅程添上更重的意義,「我常常覺得如果去一個城市,能夠經歷四季是非常美好的事」。有些人會覺得香港和紐約相似,但其實不然,「有時候相似性是流於表面的,在身體裏會覺得分別很大」。
居住在紐約的族群非常多,或許國族的疆界在紐約不再那麼明顯和重要,潘國靈也很快便融入了當地的生活。其中,潘國靈很喜歡紐約的地下鐵路,形容它是一個非常強盛的生命體,指它和香港地鐵非常不同,卡廂沒有信號,乘客會看書解悶。紐約的博物館、畫廊、劇院、戲院繁多,即使小眾藝術也有一定的觀眾群,藝術發展非常蓬勃,潘國靈形容自己當時就像一塊海綿般,在紐約這個藝術城市享受着多樣的文化和知識。在二○一一年,潘國靈短暫地重返紐約一個月,原本他對某些紐約的記憶已漸漸消失,可是當他重新踏足舊地時,能夠召喚到被遺忘的記憶,他形容就像和舊友打個照面。他重訪了世貿遺址,眼見原來的斷石頹垣的模樣變成了世貿中心一號,巍然矗立,令他不免懷念起以往的廢墟。他在書中寫道:「在長達十年的時間,『歸零地』以廢墟之姿示人,沒有刻意隱藏現場的頹垣敗瓦,世界各地旅人來到災難也是廢墟現場,看着眼前敗壞的鋼筋泥石,不無沉靜下來,從缺失中反思生命。」
紹興魯迅故居之旅
潘國靈在二○一一年左右到訪中國不同的城市,好像是上海、中山、廣州等等。他指當年中國會出版一些香港本地作家的書籍,對香港文學的接納程度比較高,所以他在那幾年間有不少機會受邀到內地擔任講座嘉賓,或者作文化交流。
潘國靈作為魯迅書迷,也曾到訪過上海的魯迅博物館。他第一次乘高鐵,便是去探訪魯迅的故居、出生之地。他一直都很想去看魯迅筆下的魯鎮、烏篷船,身處紹興水鄉的時候,更體驗了搭烏篷船的滋味。「旅行除了是吸收文化、親臨實地,你都會不停思考,事物是否都變得後現代了?比如出自孔乙己的咸亨酒店,現在已經變成五星級酒店。基本上整個紹興都用魯迅作招牌,變成旅遊盛事。」這次的紹興之行令潘國靈感到衝擊,令他思疑什麼是真實性。他回憶當時參觀北京的四合院,隨着導遊走進去參觀,當時仍有平民在四合院居住,也不知道是參觀者在觀察,還是被住在裏面的人觀察,「這種景况十分有趣,後台(backstage)已經成為一種前台(frontstage)」。他感嘆:「已經沒有所謂『原來』,『原來』已變了另一個異况。」
潘國靈坦言自己也探訪過不同作家的故居,雖然有些作家的故居會被重新包裝為書迷朝聖之地,但也有不少作家故居保有原貌。他曾經尋訪《在路上》的作者傑克.凱魯亞克的住處,住處並沒有刻意粉飾、翻新,非常低調,「只是想讓人知道,這裏曾經有文人的足迹」。
旅行的意義在於……
不少遊客到往他方時,着重消費購物、觀光享樂,哪裏好玩哪裏好吃才是他們最關心的地方。也有些打工人,會為了去旅行而拚命工作,消費完便會回港繼續工作。潘國靈對於有些人說的「旅行是對自由的嚮往」很是疑惑,因為旅行早就是資本主義的其中一環。和這種遊客相反的是背包客,追求流浪、冒險的旅行,目的便是為了和自身的地方產生距離感。這兩種相反的旅行者,背後都有一個「家」的地方等待自己,他在書中寫道:「旅行的本質就是人為地與家園保持距離,從而獲取經驗和樂趣。」
書中其中一個章節名為「渡劫之行」,潘國靈將生命裏的難關帶到旅程之中,「我不想說旅行是一個救贖,但某程度上它能讓你走出自困、鬱結的狀態」。潘國靈說起年輕的時候自己會想「走遠一些」,去東歐、西歐。但近年,他便覺得「遠近不是單單以時差、里程去計算,其實是關乎心境。突然間會覺得越南、緬甸好吸引——原來這麼近的地方,歷史會這麼複雜」。其中一篇〈伴離之旅〉便是記錄潘國靈第一次踏足緬甸仰光,在大歷史背景面前,潘國靈帶着沉重的心事一邊遊探一邊理解緬甸的歷史痕迹,在旅程中慢慢走出鬱結,療癒自身。
旅行除了是對異地的探索,對於潘國靈而言,旅行也像一個個不同景致的窗口,在這些窗口中可以突破以往的視野、觀點。在異地他亦不忘本土,他指書寫本土有一種開放性,可以和世界不同的文學有交集,「我常常覺得香港作家,其實都不妨寫其他地方。因為世界太大,每到一個地方,你不同的人生階段你得到的經歷……要出一出去,才能更加明白自己的城市。常常在自己的城市,會有一種局限」。他在不同城市旅行時,偶爾會看到香港的影子,在澳門旅行時,比對香港的意味更濃。澳門和香港有着不少相似的地方,大家都會認為香港的發展比澳門更為蓬勃。在潘國靈眼中,澳門可作為香港的對照,當各個城市「力爭上游」、過度發展的時候,澳門仍然保有矮樓房、舊式茶樓以及特有的南歐風情,反思香港因發展步伐而失去了不少可貴的文化特色。
以一個陌生人的身分,走進新的地方,離開熟悉的景致,這種新的衝擊和新鮮感也是旅行的魅力所在。正正因為只在書上、熒幕上、網絡上了解過那些地方,才充滿了想像。潘國靈筆下的一個個異地,都予讀者另一種閱讀城市的方法,不是那些告訴你好玩好吃的資訊,而是從地方的歷史、他的親身經驗作為異國度的嚮導。
文學info‧一些經典遊記
《史坦貝克俄羅斯紀行》約翰.史坦貝克
這本書可以說是強強聯手的一本旅遊文學,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史坦貝克書寫,二十世紀享負盛名的戰地攝影師羅伯.卡帕拍照!他們深入極權國家俄羅斯四十天,為大家帶來俄羅斯真實的一面,圖文並茂地道出俄羅斯不同階級的生活實景。史坦貝克不加批判地書寫,並在最後添上諷刺的一筆。雖然他們兩位來自西方民主社會,但書中也盡見其對俄羅斯勞動階層的諒解。
《在自己房間裏的旅行》薩米耶.德梅斯特
作者因為一場決鬥被罰軟禁在家,其間以玩票性質寫了這本他也意想不到的暢銷書,引起極大迴響。當時的作者只有二十七歲,被處罰在家中房間後,才開始真正觀察這個生活的地方,慢慢地超脫身體的禁錮,以活潑的想像力思想旅行,探討哲學、歷史。當中亦有和小狗和僕人細膩的互動,也從他們的對話得出人生哲理。全書字數不多,作者卻能在短短四十二天和一本小冊裏反省自身,尋找自我,在疫情看也別有風味。
《旅行的異義》伊莉莎白.貝克
在全球化下,有賴科技的發展,旅行觀光成為某些城市的主要收入來源。這種旅行觀光包裝甚好,人們只看到光鮮亮麗的一面,而忽略了這個龐大的產業對於自然、社會的破壞性。此書出版前,一直鮮有人討論旅遊業的問題,當時的旅遊寫作大多集中在吹捧旅遊、認識異國之好,於是作者決定以記者身分走訪十個國家、四大洲,觀察、記錄旅遊業對國家經濟、文化、生態等等的影響,帶來不一樣的旅行論調,藉此令人反思旅行的意義。
《無界之疆》凱特.哈里斯
凱特.哈里斯是一名生物科學家,但心底藏有一個探險家之夢。本來可以在實驗室攻讀博士的她,毅然放棄並踏上單車展開冒險,也藉此研究人類如何打破荒原,建立自己的邊界。旅程可說是困難重重,除了是地區疾病的憂慮,亦有和不同族群相處上的文化衝突。作者書寫一個外國人在擁有神秘色彩之地,如死海、西藏、烏茲別克等的遭遇和景致,當中亦有抒發和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