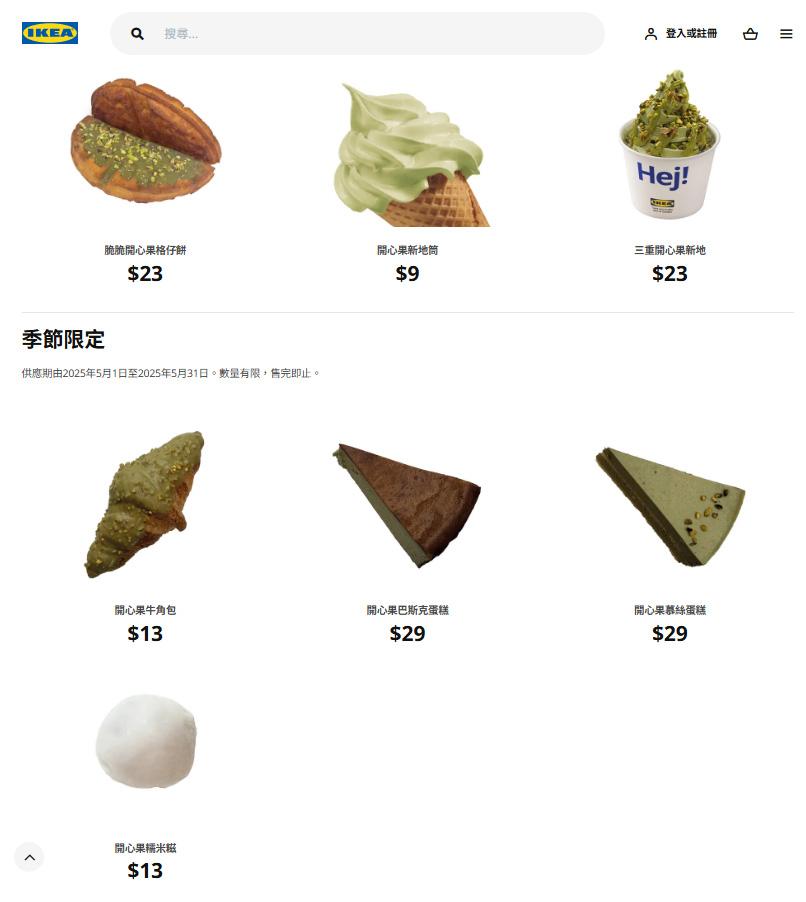【明報專訊】頑抗者,必勝利——此句出自十九世紀烏克蘭民族詩人謝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又譯舒夫真高)手筆的一句口號,八年前響徹獨立廣場,如今又成為烏克蘭國人的誓師之詞:儘管俄烏軍力懸殊,民調表示近七成烏克蘭人自信終將擊敗侵略者。抵抗沙皇可謂烏克蘭的悠久傳統——篇首詩句即針對帝俄(「各族人民之牢」)而發,謝甫琴科並非第一人,但絕對是最著名一人,從謝氏頭銜之多——烏克蘭文學之父、民族詩人、畫家、琴手、烈士、先知、聖人,可見其地位之高。究竟十九世紀的詩作對烏克蘭人意義為何,對今日世人又有何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