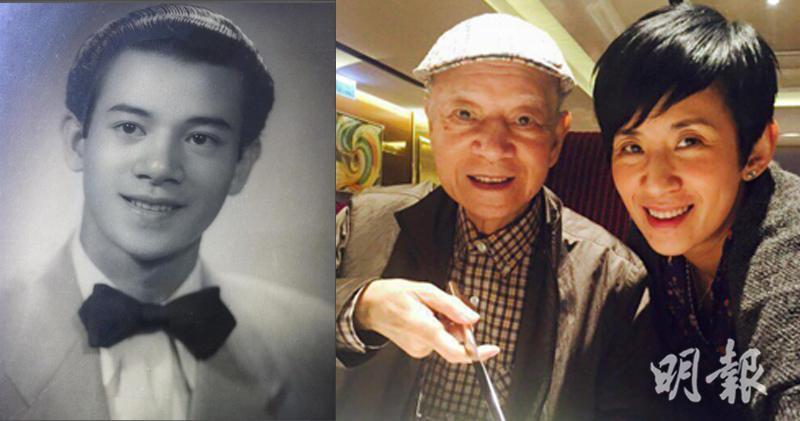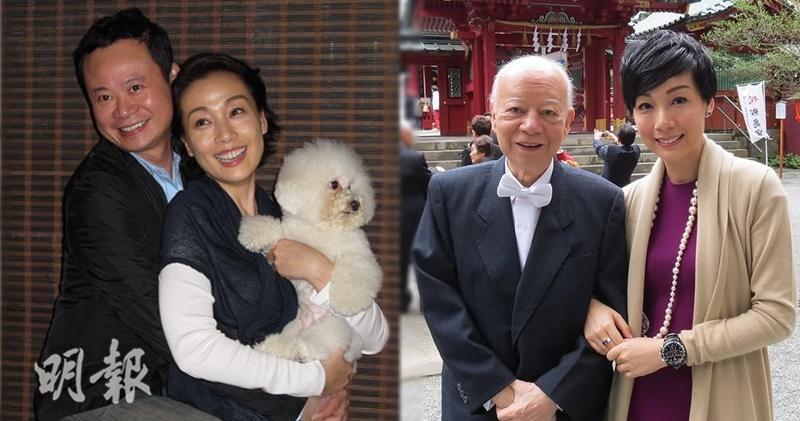【明報專訊】4月21日是防疫措施放寬的一天,可是也沒誰夠膽高興歡呼,誰知暫時安穩又能維持多久呢?大館展覽「圓缺俱樂部」策展人李伊寧(Erin)捕捉如此時代下,她在香港感受到這樣一股脆弱情緒,集合7名藝術家的作品,展覽英文名字是emo gym,觀眾進入場館當作做個小練習,即管「emo」一下,為情緒舒展筋骨。
「Emo」從一種音樂風格演變為潮語,指很情緒化的時刻、個性,有些人也會用來自嘲當刻的多愁善感,尤其在社交平台上更要事先「聲明」,免得被視為放負、矯情。Erin說展覽原本在去年開放,因疫情延到今年1月,再延至4月,計起來由籌備到展出,已差不多兩年,開初她想過以迷茫為題,因為當時感覺到2019年後,「大家不知怎樣走下去,但後來以為疫情好快完,卻總未完,好似大家都要move on,就發現面對很多脆弱」。策展人介紹文的頭一句是,「這是一個即使走在街上都可能隨時落淚的時代」,一看好似說得太誇張,想想竟也貼切。
而在世界逐漸重新打開的時候,展覽用上頗直接的語言來接通觀眾,Erin說在尋找第三條路,「我一直想做個展覽跟香港觀眾有共鳴,有時會在展場聽到觀眾說,唉藝術呢啲嘢,我哋唔識㗎喇,所以我想觸摸那種時代精神也好、大家在想些什麼也好,這兩三年香港經歷很多,大家都有種脆弱,又覺得未必可以很安全地說出來,或跟身邊的人說,所以這個展覽就是一個安全、親密的空間,練習他們的情緒」。
客廳 看別人在街上的模樣
推開展廳的門,進入有電視、有魚缸的「客廳」。嚴瑞芳2019年的作品《逆踏》包括一組街頭錄像,是她用手機拍下在街上觀察到的一些小動作,如有人在商店門外的排隊膠帶旁徘徊,要排又不排的模樣;地鐵車廂裏有個女人像沉醉在自己的世界裏自言自語;巴士車窗外有昆蟲用腳重複摩擦;男子在馬路旁跳舞,瑞芳說看在她眼中這些行為都「好爽」,「他們在公共空間很自由地表達自己,我們可否透過參考其他人,如行路時不斷改變動作,不被監控辨識到?行路都可以是一種抵抗」。於是她又請舞者以此作參考,用違反慣性動作的姿勢舞動。另一邊曾家偉的一組作品,將吸啜水缸玻璃的琵琶魚放得巨大,看牠一呼一吸,觀眾或可聯繫起留守家中依附屏幕生存的狀態。
隧道 訓練親密感
展廳中間有一條外形帶點夢幻的「隧道」,是朱凱婷的《inti-gym》,一間訓練親密感的「健身室」,當兩個陌生人分別從隧道兩頭入內,脫鞋踏上地氈,坐上椅子,二人隔着一層彈力布,可「觸摸」到對方,然後會按指示傾真心話,如「你(真的)過得好嗎?」,最後掀開一小格的布對望。
我說這讓人想起大熱配對節目Love is Blind,她笑說見到時也驚訝與自己的畢業作相似,不過節目要求不見面談心事的男女最後需選定對象「盲婚」才可見面,而藝術家則一直以各式各樣的小實驗探討人與人產生親密感的過程。她在外國曾站餐廳玻璃窗外舉牌與食客互動;又試過將聖誕節愛人要在槲寄生下親吻的西方傳統,化為由她手持植物,放二人頭頂看他們會不會吻起來。在香港,她去年曾於街頭以餐廳所用的「限聚膠板」作為阻隔再互動,發現在海邊的人比鬧市更願意參與,但還是有不少人懷疑她的意圖,「會問我係咪傳教?」
從實驗和理論得知,建立親密感有幾個元素,「第一是triangulation,兩個人之間存在第三件事,例如在街上看到BB、狗,然後說好得意,會令兩個人更親密。第二是一些阻隔,(人類學家)Edward Hall提出不同類型的關係會保持不同距離,陌生人與情侶是不一樣的,我做完餐廳舉牌的實驗,就發覺中間有阻隔,令人感覺安全。第三是燈光顏色、光暗,要舒適又不可太暗製造不安,太光又太暴露;第四是(心理學家)Arthur Aron說的4分鐘眼神接觸可增加親密感」。她的設計中,如絲襪般的布料重疊幾層,愈往內愈不透明的效果,策展人Erin說也花了一番工夫,搭建人員曾認為沒可能把布拉成現時的漂亮弧度,藝術家去做1:5的模型說服師傅,結果由10個人合力拉出滿意模樣才釘好,這個形狀與柔軟布料,也想營造被擁抱的感覺。
卧室 記憶與未來的脆弱
從客廳進睡房,作品也從更私密個人的角度出發。李卓媛兩組作品,《末日方長》與《憶》,分別呈現面對過去與想像未來的脆弱。《末日方長》是她邀請父母、弟弟和兩名朋友一起創作的作品,請他們提供一件與自身過往有關的重要物件,改裝為針孔相機,再讓他們談未來,「原理是倒轉攝影的關係,好多時是由攝影師主導,我就想被拍攝的人作主導,以溝通、信任去做這影像,用對話作為曝光時間,佢講幾耐我就影幾耐,每次拍攝都以一條問題how are you tomorrow?開始」。她如此看脆弱,「我一直以來創作的切入點是已消失或快將消失的人事物,就似城市變更的速度,很多事像是永恆,亦可短暫。會感受到脆弱,是因為跟這個地方的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為很多事可重複再現,但上一次或已是最後一次」。
「末日方長」是來自她一次從簡體字幕出現的誤讀,「這與我們身處的環境都有共鳴,來日方長是指未來有很多時間,但都是離別前夕才說的,這拍攝就像一個說再見的練習」。另一個作品《憶》與她的婆婆有關,有一次婆婆在家中說要執行李回家,家人才發現她的記憶開始從腦海消退,「有時她也忘記了我的名字,所以我們就給她一本相簿」,婆婆看到一張全家福,「她會說『是一家人呀』,我覺得很感動。記憶很『化學』,也是流動的,有時記得多些細節,有時記得對一件事的感覺,就似倒影,風在水面吹過,倒影就會模糊」。婆婆昔日從事製衣,在大合照所穿的長衫還保存至今,「我嘗試用陶瓷這種堅固又脆弱的物料,將衣服用壓印的方法做瓷板,再用瓷板曬相,做出不同深淺變化」。在每幅相下面,寫着歪歪斜斜的日子,是給婆婆的小習作,「你能看出她寫得辛苦和很用力,寫數字是一個訓練去幫腦退化的病人,撇開作為一種治療,我亦好奇記憶模糊或失憶的人,對時間的概念是怎樣?」
她希望觀眾能慢慢看,甚至能在瓷板上看到長衫的花紋。策展的Erin則透露與藝術家構思過許多展出版本,如用木框將相及瓷板放在一起,最終決定這個比較空靈的裝置形式。展覽也想讓年輕藝術家有更多摸索空間,「很多藝術空間的展覽時間很緊湊,三四個月前發現有空檔,就會找藝術家問可否做個show,這種節奏好難做到大型作品,又如對於會雕琢物質的藝術家就不適合,像她冲這一輯相,在黑房可能兩星期,發展這個概念都需時半年、一年,沒可能4個月去做」。經過卓思穎、劉清華、鄭虹的作品,Erin帶我回到入口拿個掛在牆上的大聲公,走出場館,給我介紹這次合作的另一個新發現。
後樓梯 發聲、告別
我們帶着大聲公循「賽馬會藝方」出口對面的石階下去,轉入另一場地「賽馬會立方」的後樓梯,中間經過電梯口外的大電視,播着一段錄像,原本這是水牌,他們拆掉才知內有電線,能放屏幕改裝為展覽延伸部分。推門進後樓梯,裏面迴盪着『咿咿唔唔』的聲音,抬頭一看,幾個與大聲公形狀相似的巨型喇叭安裝在中央。
這是嚴瑞芳為展覽創作的新作《梯間回聲》,邀請已移民的人唱出彌撒歌The Last Supper。瑞芳是基督徒,不過她找到這首歌,並沒有傳教的意味,「歌詞說耶穌走的時候囑用這個餅、那個杯紀念我。我由細到大唱好多詩歌,發覺這首歌有點怪,並沒說我為你死,你一定要信我這類的話,而是展現出人性,告別就是這般純粹」。場地是她選的,「我想找一個大館內不被監控的地方,後樓梯就是這裏最自由的公共空間」。
因移民面對離散,她說與面對死亡有點相似,「分開了不知會否再見,不知怎麼處理,說不出口。既然用語言處理不到,我這兩年都會用更多比較抽象的聲音,能傳遞一種直觀的情感」。她想像,只需隨身帶個大聲公,找一道後樓梯,就可自行製造出一個超越宗教的神聖場所,可以紀念,可以發聲,也可留下聲音給之後來到這裏的人。除了移民的人,她邀請無伴奏人聲樂團以世界語合唱這首歌,「合唱時,你的聲音會被聽見,同時也在聽別人的聲音,合唱就係咁簡單,這就是公共,有你有我」。咿唔之聲是唱的人在練聲,亦以此引觀眾自然地隨之加入自己的聲音。
Erin以「honest」(坦誠)形容這次展覽的作品,「我收回作品時再將當中的脆弱性收窄少少,發現講社會機制的脆弱性,在香港很難找到這種作品」。她以李卓媛從親友關係出發創作為例,「反而這種作品是很honest的,她的世界就是在想這些,然後跟你分享」。關於記憶的脆弱、親密感的脆弱、私隱的脆弱……嚴瑞芳說,她的脆弱,是在創作中發覺怕把想說的,說得太清楚,「莫非抽象是一個包裝,掩蓋我不敢直接講?」她害怕自己在不經意中已改變了。承認Emo,好像不易啟齒,或人人都慣了手勢戴幾重頭盔,才敢訴說所感,她沒用太抽象的方式,簡單釋放一點點鼓勵與力量,脆弱或許有時是傷感,有時不好過,但有時也是誠實面對自我的難得時刻。
「圓缺俱樂部」展覽
日期:4月21日至6月19日(周二至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