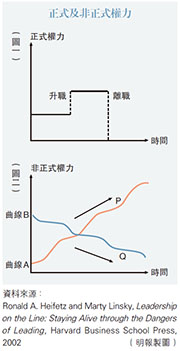【明報專訊】藝術家Ernest Chang天生紅綠色盲,偏偏熱愛fine art,沉迷繪畫、攝影。近年專注pop art發展,作品用色鮮艷,因為繽紛鮮艷的顏色他才容易看得到。作品中不難發現大家眼熟的動漫人物,構圖卻帶文藝復興時期的名畫影子。「我就是用顏色先吸引你目光,再跟你談更多深層意義。」
Ernest Chang(張子言)擁有多重身分,既是攝影師,也是藝術家。Ernest說話中英夾雜,他在美國出生,因着父親的工作,8歲來香港,讀了幾年本地學校,之後在德瑞國際學校繼續學業,後回到美國升讀高中,曾在Ringling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讀Fine Arts,再來港又在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短暫學習攝影。前途應該一帆風順?他卻坦承學攝影未畢業就停學,因當時受毒品問題困擾。他說20多歲時來香港做時裝攝影,部分圈內人有吸毒陋習,他也隨波逐流。後用了3年時間徹底戒除惡習,攝影題材也由喧鬧的娛樂、時裝,轉為以家庭、企業為對象。眼前的Ernest有美國人的坦率作風,談起過去毫不忸怩掩飾。
科技助打開創作之門
他於2014年在灣仔藍屋附近開設藝廊The Stallery。起初他把這裏當作攝影studio,順便展出自己的作品,開業2、3年後,開始舉辦與藝術相關的展覽。「我7歲就知道自己有色盲,喜歡繪畫,那時候常常畫素描,畫黑白的東西,我不會有問題,因為黑白對比強烈。」到10幾歲涉足攝影,當時心想「影相不需要自己混色,只需按下按鈕,就可以把世界的色彩capture下來」。但他傾向黑白攝影,即使後來成為專業攝影師,客戶都比較喜歡他的黑白作品。「拍攝彩色人像作品,客戶有時候會反映問題,如色調太青、太橙等,但我自己不會察覺。」後來從攝影回歸繪畫,「我覺得我腦袋裏的東西,多過我用相機capture得到的。所以我想創作多些我心目中的東西,而不是靠capture現有的」。
「Pop art很多時有很粗線條,顏色亦好sharp,我可以分辨得到。」Ernest無意間接觸到絲網印刷這種技巧,透過multiple layers製作彩色圖像,發現這種方式不會因為色盲而影響創作,簡直是「perfect for colour blind的人」,而科技亦為他打開方便之門:「我創作時習慣用iPad,再配合一個叫Cone的App,非常方便。例如我畫了個digital draft,只要把這個draft傳送到App,點一下任何位置,我就會知道那顏色的代碼,只要把顏色儲存,我之後隨時可以找得到。我習慣用iPad畫好初稿,再傳送到電腦加細節。」
紅綠色盲如加藍色濾鏡
紅綠色盲下的世界,到底是如何的?Ernest 形容他眼下的世界,就像加了一層藍色濾鏡的Instagram。「我看到的紅與綠,沒有你們看到的那麼sharp,太相近的顏色會mix up,看不到漸變色的分別。我只看得到很sharp的紅色,粉紅色在我眼中可能成了灰色;橙色或看成啡色,事物就好像被混進了一點黑般。」他笑言「自小就覺得色盲好煩」,例如當年考地理,他要教師協助在地圖做標記,一涉及顏色,單靠自己就做不來,「不能說是很大的障礙,但因為每天都要面對,就會覺得好麻煩」。他的pop art作品大都用色繽紛而鮮艷,Ernest笑言:「就是要弄得如此colourful,我自己才可以看到嘛!」不過他也接受意見,例如有朋友着他「用色不要那麼濫」,在2021年面世的Bling Dynasty系列,他便糅合了西方和中國藝術的美學意念,以刺繡工藝等手法表現,構圖用色相對淺。「我需要很多feedback才可以進步,對顏色有更多了解。」色盲既是無法改變,他就想方法共存,轉化為創作動力。
仿效三聯畫 3木板拼接巨型作品
喜歡藝術又曾修讀藝術相關課程,不難發現Ernest的作品,很多時會以文藝復興時期名畫為靈感,構圖相近,人物卻換上香港、日本、美國家喻戶曉的動漫角色。「這些動漫人物伴隨我們這一代長大。我在美國時,任天堂遊戲都有英文版,日常生活如產品包裝也有動漫。上代人的明星是真人,是瑪麗蓮夢露、貓王;我們這一代的明星就是虛構的動漫人物,我們的成長與這些pop culture緊密聯繫。可以說這些動漫都代表一部分的我。」
2019年Ernest的Famous by Proxy(《代.名.畫》)系列中的The Entombment of Mario,是他最喜歡的作品。「最特別之處是我仿效文藝復興時期的方式,那時因為沒有大木板,會以3塊木板拼接成巨型作品。」Triptych(三聯畫)常見於文藝復興時期的油畫,易於分拆運輸。「我這幅畫有19種顏色,1種色1個絲網,但由於用上3塊木板,即是說我要製作19×3那麼多的絲網」,光聽已感到複雜。為什麼着眼於文藝復興時代?「那時作品包含很多virtues(美德),是後來modern art(現代藝術)、postmodern art(後現代藝術)喪失了。」他解釋:「Modernism是做art就是做art,例如法國藝術家杜尚(Marcel Duchamp)的尿兜作品,他說藝術就是藝術,不需要其他meaning。Postmodern也是art for art's sake,但加入了現代的struggle,加入了諷刺元素。我覺得現在已進入metamodernism(元現代主義)時代,我想把文藝復興時期那些教人要做好人之類的教誨,融入這個時代。」那即是把舊的、已有的,用新的方式呈現?「現代很多東西都沿於舊時。即使畫油畫,技巧都是承襲舊時。但藝術家把舊的概念或技巧,加入自己的思考、新思維,這個『合成』就是新的。」
「現在跟小朋友、年輕人,說大道理、聖經故事或希臘神話,他們可能不感興趣。我的畫The Incredulity of Master Roshi用上《龍珠》角色,吸引年輕世代去了解。」至於較年長的,則可能一眼認出跟名畫The Incredulity of Saint Thomas相似之處,畫的是關於不相信基督復活的聖經故事。似曾相識的名畫換了角色,便成為跨世代連結。「Metamodernism就是要利用跟社會有聯繫的地方,加進舊有觀念而又是現代社會需要的,像是那些關於美德的教育,想方法不要淹沒於社交媒體的巨大漩渦……這一個generation很容易接受pop art,文藝復興年代的大師級創作,構圖各樣都已經很完美,我用pop art的形式把經典帶給現今世代。」
認為毋須神化NFT
NFT是近年大熱課題,Ernest表示他不反對,因為那是個保護數碼藝術品的好方法,正如實體藝術品可以用房子保護一樣,不過毋須太神化NFT。「暫時來說,NFT不是一個art concept,而是一個platform、一個tool。」他認為藝術也應該注意對環境的影響,「NFT未fully sustainable(完全可持續)的一天,我認為也不算是真正的art form」,所以他的創作仍以實體為主。他創作中的新系列以中美的太空競賽為靈感,侃侃而談政府與私人企業間的關係,又認為即使人類覓得第二個地球,也仍然會一如過往,重複破壞地球的行為。對人性悲觀,卻用上色彩繽紛的顏色去作畫,Ernest笑言:「我就是用顏色先吸引你目光,再跟你談更多深層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