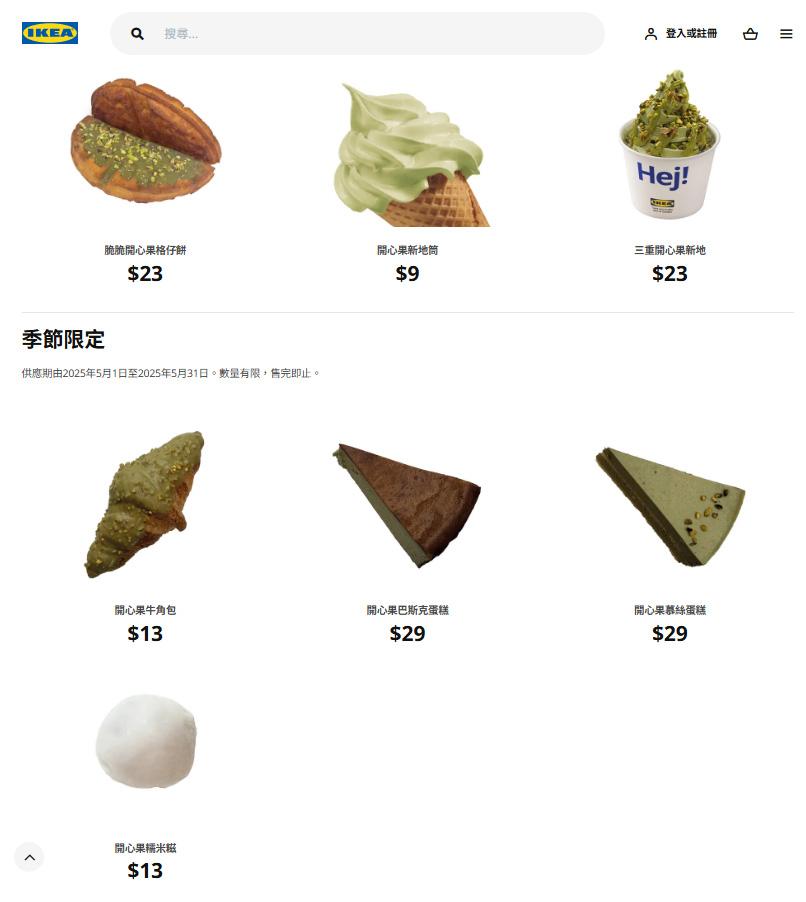【明報專訊】讀者認識曾詠聰大多都是看他的詩,出道作《戒和同修》受到不少人關注,也是難得銷量較好的詩集。事隔三年,曾詠聰以散文集《千鳥足》回歸讀者眼前。曾詠聰對生命的際遇有種獨特的見解,而這本散文集的名稱正好解釋。「千鳥足」是日本語,意為醉酒後腳步虛浮的狀態,他認為生命會有「斷了片而不清醒」的狀態,未弄清發生的事情前便跌入接踵而來的意外。他上一本作品《戒和同修》強調「包含了規律、和諧,以及共同修行的意味」,是回應了生命的挫折,那麼《千鳥足》便是刻劃了生命在交錯之間所產生的不確定性,一種迷惘的狀態。
這次的散文集結集了曾詠聰過往的作品,包括專欄文章,及六年之間的散文。一般的散文集以時序排列,或是以主題劃分,曾詠聰卻將《千鳥足》文章的編排次序打亂,只是根據作者的「感覺」編排,是名副其實的「散文集」。曾詠聰這個小小實驗,是想看看在如此零散的狀態下,一睹讀者的反應,「希望讀者可以在這種狀態下仍找到自己的排序方式、閱讀節奏」。這種忽發奇想的背後,是曾詠聰認為讀者都有和他相似的成長經歷,只是時序不同,他更指所有事情未必理所當然地按某個時序發生,人生充滿着萬變。
不只是編輯書的方式,曾詠聰連三位幫忙作推薦序的朋友也不放過,朱少璋、吳其謙和嚴瀚欽只能收到書的部分書稿,以此作序。他說:「我要求三位寫序時要裝作看完整本書,看三位寫出來的序,無獨有偶地會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虛假的,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實驗。」
不誠實的散文集
相對上一本詩集,曾詠聰說在身分上有所轉換,他在《戒和同修》裏是觀察者,與讀者分享對世界的觀察和想法,而在《千鳥足》裏是參與者,以第一身的感受出發,包括他的選擇和當下別人的反應。雖說《千鳥足》是一本散文集,但是在文裏行間都會看到詩的存在,在文章加入詩作。曾詠聰顯然對寫詩比較有自信,他也自言較為得心應手,加入在散文中往往是為了留個念想、起個引子,他認為寫詩就像猜謎,讀者可以多個角度作解讀,同時埋下未被言說的感受。一方面強調散文能夠完整交代整件事的曾詠聰,一方面卻在文章裏打下啞謎,如此矛盾的作法,其實也對應了他對自身的不誠實。
人前是中學老師、文學獎得主的曾詠聰,能夠有安穩的生活之餘,也帶來不少有話題的作品,第一本詩集亦有亮眼成績。光鮮如他,才是最害怕失敗的人,一句「我很抗拒軟弱如此顯露」,注定了他不誠實的個性。即使有野心、有怯懦這種人性固有的元素,曾詠聰也不希望顯露人前,「還是要笑,嬉皮笑臉地說其實不要緊,志在參與」,這種退後的保護色成為他多年的生存伎倆。
「即使直到現在,我對自己或其他人仍然有不誠實。其實每個人都有對自己不誠實的地方,只是比例上多與少的分別。巧合的是,我是從小到大,不誠實佔的比例比較多。」曾詠聰道。可是書寫散文貴乎真誠、真實,不誠實如他,也直認自己寫散文相當矛盾,「可是我都坦露給大家,我就是不誠實的」。曾詠聰的不誠實,在《千鳥足》裏作出了讓步,或許未能徹底地承認自己的慾望、陰暗,但所寫的事亦非利害推動,是發乎自身的情感流露,不完美,但可接受。
曾詠聰在寫作不誠實之處,可以看出其自身的幽默感,這些搞笑淡化了事情的嚴重,轉移了焦點。就如其中一篇〈末日如斯〉寫從前和現在疫症時期的上課經驗,表達出疫情時期教學雙方的無力,結尾一句:「感覺到心儀女生一直偷偷看我,我打算依仗侷促的安全感表白,她才認真告訴我,你的鼻水把口罩沾濕成兩個小圈,有點嘔心,送你一個替換。」他指疫情是一個循環,重複地上映,現在看來不勝唏噓。童年時或會因為這種不需面授、猶如停課的學習日子感到快樂,可是成人以後,有了兒時的對比便愈覺沉重。曾詠聰說自己並非刻意搞笑,這些都是真切發生過的事情,而且在記憶中留下深刻印象。能在悲傷裏尋得一點惹人發笑的幽默感,曾詠聰也直言會令事情的嚴肅程度減弱,他不時希望自己修正缺點,學會放下搞笑去認真看待事情,隨即便笑自己「次次都不成功」。他續說:「每一次認真的事情,我都以搞笑的行為處理它,是嘻皮笑臉地面對事情,就像太宰治的《人間失格》,他愈不開心,他就愈搞笑。」
以輕鬆的方法迴避痛苦,是每個人都有的經驗,大概是直面痛苦需要太多心力,令人無法承受。曾詠聰也以此作為安慰自身的方式,說服自己在面對重大難關時,可以輕鬆、容易應對,或是平衡得失心。在書寫上,幽默也是一個容易吸引讀者的優勢,只是讀懂曾詠聰的幽默感,就會了解是作者的不誠實與失意。
詩人轉行寫散文
就前文所提及,曾詠聰較善於寫詩,寫散文則相對困難。他解釋,自己是一個思想跳躍的人,也沒耐性,所以寫散文所花的心力和時間比較長。他說:「要完整地交代一件事,又不會很唚氣,同時讓人覺得有追看性,比起寫詩會更吃力。」儘管如此,曾詠聰都希望成為一個既能寫詩,也能寫散文的作家。
曾詠聰坦言詩集的讀者較少,而散文的門檻較低,可以包容更多的讀者,於是他希望以書寫散文來讓讀者了解他更多作品。他續道:「我希望拉近和讀者的距離,書寫平易近人的散文。」的而且確,曾詠聰可以曲高和寡,繼續寫詩,選擇寫一些更易理解的文章是為了實踐自己的文學觀,「我不認為文學是企高一級的。我更重視文學可以和更多人分享感受,其他人參與不到是非常可惜的事」。他進一步說,解讀詩所花費的心神比其他文體多,詩的讀者難求,甚至如詩人呂永佳所言,詩的讀者比作者更少,散文則更易解讀、更易得到共鳴,在讀者眼中,更加傾向去閱讀散文或小說。
他觀察坊間有不少散文集,各有各派的作風,可是能夠討論的散文集卻非常少,這是因為散文集太強調個人。加上在市場上,平白易明以及報紙專欄結集成書的散文集比較多。他尤其喜好麥樹堅的散文,《絢光細瀧》便是當中最愛的一本,他認為麥樹堅對熱愛的事情了解透徹,轉化為散文時又不失觀看性。
我的生命只示範一次
在曾詠聰的成長過程中,周邊的人對他影響甚大,一言一行都有他人的影子。而在《千鳥居》的文章裏,不難看到曾詠聰對於與身邊人相處的思考,人際關係是一條重大的線索。他由小到大都處於被動的位置,別人主動示好,才會回應,「我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感到很疏離,甚至在中學畢業之前,我是不懂得如何和人相處」。經過多年的適應和蛻變,曾詠聰開始改變對關係的想法,更嘗試珍惜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這些轉變卻是由於見證太多人離開而得來。他感嘆:「在這個世界,很多人會無常地突然離去、消逝,在離開以後,他才發現這些人值得珍惜和重視。」
有人視寫作是救贖、療癒的過程,曾詠聰書寫人無法再重遇的遺憾,卻未必能療癒自身。他直言發生的事情很多都是解決不到,相比尋求解脫,他以書寫作為生命的紀錄,「或許將來有幸給別人看到,那些人又發生相近的處境時,我希望我的選擇、感受是一個參考」。他續指書寫有趣的地方,在於不同時空的我們能夠在文字重遇,打破了時序和界限,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並非唯一的,而是具有公共性。
書寫散文另一個關注點是,公共性與私密性之間的拉鋸,曾詠聰的題材無疑是私密的,圍繞自身發生的事情。曾詠聰形容寫散文是危險的,他擔心暴露自己的弱點,以及暴露後別人的批評,所以他將一些私密過頭、無病呻吟的文章從《千鳥足》剔除。他說:「我希望別人是在閱讀,看到一些有用的文字、一些有用的文章。」可以看得出,曾詠聰要求「散文有用」,釐定的標準雖說是自己決定,卻也有跡可尋——重大的、共同的人生經歷。他認為散文最重要的作用是「有信息給別人提取」,令別人有得着或者對世態有所批判的散文才能稱得上好,反而文句用詞並非首要考慮的條件。
文學書的資助惡境
近年來,文學書為了提高銷量,會以進入學校為目標,接觸學生讀者。進入學校售書可以保證銷量之外,也為岌岌可危的文學書爭多一份保障。這次出版《千鳥足》,曾詠聰和出版社希望將市場瞄準學校。儘管《千鳥足》已獲得藝發局資助,可以不理會市場反應,但是曾詠聰仍希望接觸更多學生讀者。他作為中學老師去審視作品時,也認為自己的散文並不難讀,學生都能夠理解。
藝發局的文藝資助向來幫助不少本地文學作家出版,在書業市場萎縮的狀態下更見重要。藝發局也審批曾詠聰上一部詩集,可是因為藝發局當季度的資助額度已用畢,發配了更大的機構作文藝活動,導致他的作品即使獲得藝發局評審青睞,也不能獲發資助。他指一些不屬於任何機構的作者申請資助,面對審批的難度愈大,加上審批撥款的標準並不清晰、透明,令他覺得「很隨意」。曾詠聰續批評,現時出版獲資助的金額非常少,一般不會全數資助,只會佔全書的一半,甚至四分之一,在文學書銷路一直不明朗的市場,資助金額逐漸見少,對於出版社和作者而言是非常大的壓力,「他們拿了資助,當然希望出版,若然沒有人投資的話,他們要拿一大筆錢自資出版,風險甚大」。
曾詠聰認為藝發局並非有意壓縮文藝創作,一些有志之士不取資助仍會出版,可是在大筆撥款和獨立作者申請之間需要取得平衡。庫房金額有限,一些大筆的資助自然淘汰了個別或金額較少的申請,曾詠聰說:「單獨一個人是無法與大的文藝機構爭那個資助,我覺得可以分成兩條隊,將文藝活動及文藝出版分開,對他人都更公平。」雖然藝發局審批資助的結果未盡人意,但是曾詠聰亦提出不少文學獎的獎金可讓作者一圓出書夢想,亦有出版社投資書籍,出版文學作品的情况其實並非太惡劣。
即使文學讀者少,也無礙有熱誠的作者出版,將自己的聲音帶到大家面前,介入、回應世界,繼續為香港讀者帶來好的作品。闊別三年的曾詠聰書寫成長的經驗,以過來人身分回看過去,寫出了男孩蛻變成男人的複雜、感傷、成熟。或許他不是一個十分誠實的作者,卻是以自己的筆尖,用生命作為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