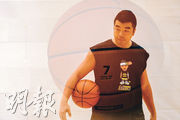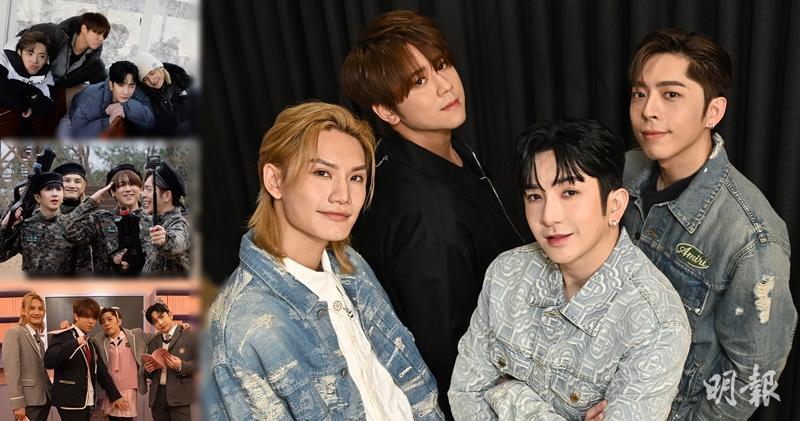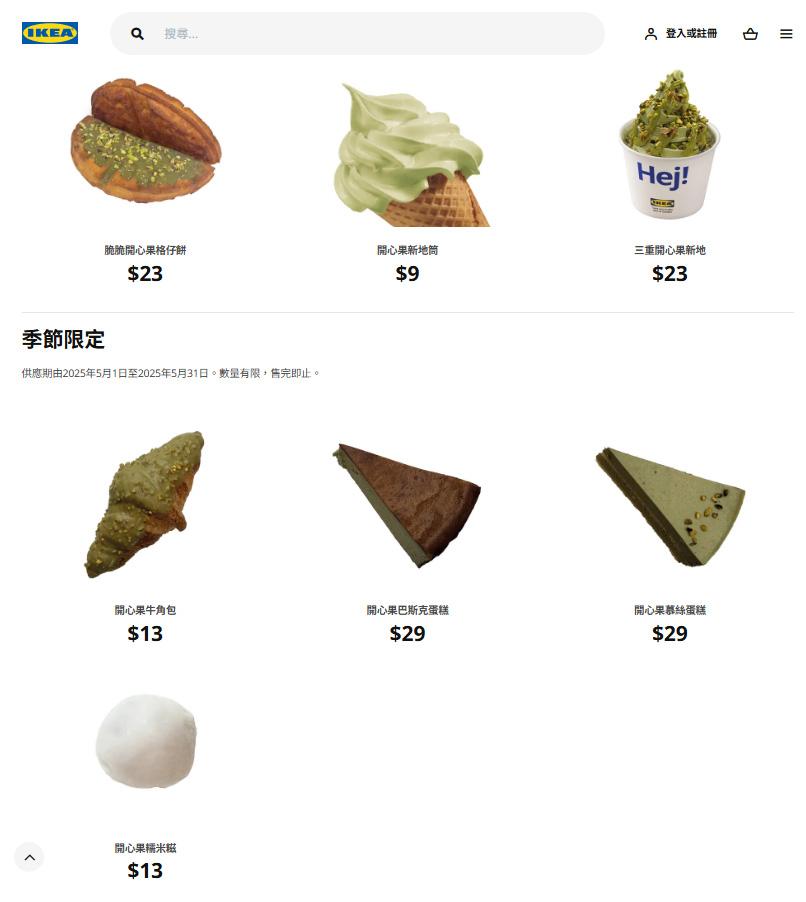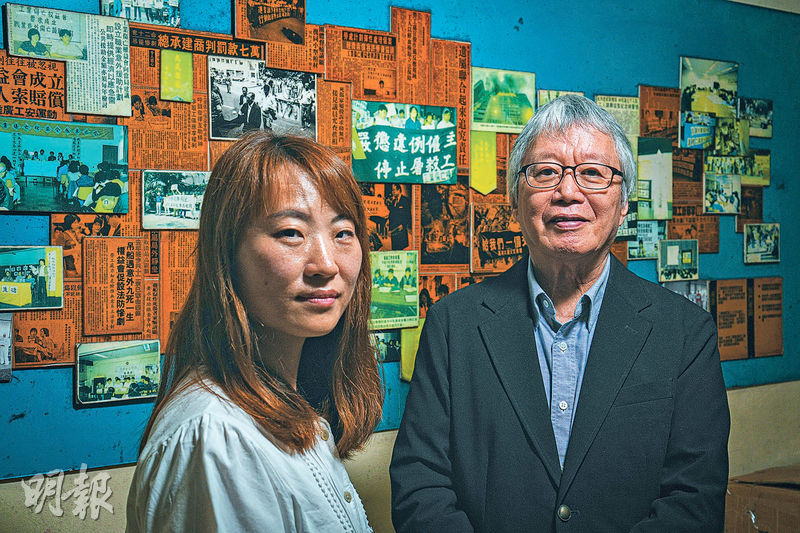【明報專訊】早前寫過有關古典音樂廳,以及有關維也納愛樂演出曲目的文章,這篇通識程度的文章是介紹粵劇。自知這方面的認識及浸淫,一不及專家,二不及戲迷,但我這一年多,從擔心「唔識睇」,看到津津有味,期待下一場演出。藉此機會向有興趣看大戲,但不得其門而入的朋友,分享一些個人體會。跟我寫了十幾年的古典樂評及影評不同,粵劇是我在疫情期間,海外古典音樂家無法來港,我又不能飛出去觀看一流演出而培養的喜好,殊不知愈看愈起勁,入戲院的頻密程度,及得上疫情前在香港入音樂廳,這個新興趣又反過來令我對古典音樂,尤其是相關場地有更深入想法。